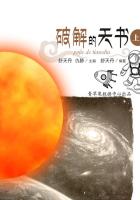好不容易血液循环了,身体有了知觉了,老大感到一阵压抑不住的恶心,那恶心如同往日杀猪时掏猪的大肠一般腥臭至极让老大一阵胃痉挛。
老大把着墙角伴随着那对男女肆无忌惮的叫唤声狂吐了起来。胃汁吐得差不多了老大才冲进门去,对这两人玩命地抡了一通王八拳。媳妇被揍掉了两颗门牙,村长的腿被打折了。老大本想学武松一下子结果了这两个狗男女,看着村长那吓得尿了炕不停哀号的样儿,老大下不去手了,觉得眼前比自己高了一头的汉子裤裆里是白长了个把儿。他揪着两人的头发把他们赤条条从炕上拽出屋子,一把火把队部的房子给点着了。
熊熊的火光映亮了半个山谷。
老大这次学乖了,他知道再当武松没什么好处,他躲到山上的山洞里想忍两天等风声小点就一走了之。
这山洞是他和嘎斯两人小时候上山玩耍时发现的,除了嘎斯没第二个人知道。老大信得过嘎斯,两人光屁股的友情那绝不是一般的。他躲进山洞,让嘎斯给自己弄点吃的,再拜托他照顾老娘,嘎斯拍着胸脯答应了说:“你放心走吧,你娘就是我娘。”
临进山洞老大还没忘记带上大学生送给他的VCD放映机。
村里的人敲锣打鼓找了两天没有找到。老大吃着嘎斯送来的大饼想着,这张半瞎子的书没白听,嘎斯够义气。
队部被烧了在乡里成了大案要案,乡派出所准备悬赏捉拿老大。
晚上村里的几个干部为商量这事又凑到一起,喝了一顿老白干也没谈出个所以然,都说这片山那么大哪里能找出个人。酒喝多了,干部们一时消化不了就不停地跑茅房。正好嘎斯给老大送完大饼也在解手,拉屎的时候听到醉醺醺的干部说举报老大有奖金两百块钱,屁股上的屎没擦干净嘎斯就把老大给举报了,他想这两百块钱能给他生病的老爹多买两服药。
警察们五花大绑地把老大从山洞里捉了出来。老大的惨样就像村民打猎时被活捉的野猪,大学生送的VCD放映机在警察的行动中被彻底地报销了,看着无数只脚在大学生的VCD上肆意地踩踏,里面的电子元件犹如《星球大战》里被摧毁的战舰一样四分五裂,老大心如刀割甚至忘了手臂被拧得脱了臼,绳索勒得自己脚踝生疼。
老大在村民们的围观下被押上了囚车。
嘎斯看着老大被警察揪着头发、踩着脑袋、反绑着手的样儿后悔了。他跟在后面跑,边跑边哭着说:“别怪我,别怪我,俺也没办法。俺爹生病实在没钱抓药。”
老大什么也没说一口浓痰吐到了嘎斯脸上,嘎斯还在追着囚车跑。看着嘎斯的可怜相老大觉得怎么好像被抓的人是他,又一想这叫他妈什么哥们儿义气,俺要是林冲,这嘎斯说什么也不配当那个鲁智深。
老大被判了三年。
这次不是在县里的劳教所,是更远的省城监狱。戴着大铐,被装在囚车里翻更多山,越更多岭,老大觉得以往二十多年的日子如同放电影一般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白被面上一幅幅巨大的画面塞满了老大的脑子。
虽然清晰,但老大觉得自己脑子里的这电影是那么让人闹心,村长、媳妇、嘎斯每个人都是那么虚伪、恶心。自己脑子里的电影根本没有自己以前看到的电影好看。
想着想着老大的眼角流下了眼泪,他在自己的生活和电影之间彻底地迷糊了,他认定现实里面的人和事都是假的,什么友情、爱情都他妈是狗屁。他更加喜爱也更加渴望电影里的世界,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才应该是真的生活。
老大在路上颠簸的闷罐囚车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当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世界观这个词的意思。
终于到了省里的监狱,这里和县城的劳教所完全不一样,墙更高,墙上的铁丝网也更厚,岗楼上还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操场上的狼狗也更加虎视眈眈。几个月后,老大和同号的各样犯人都混熟了,小偷、老千、做假药的、卖假证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老大的憨劲儿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好勇斗狠。
只有一个时候例外,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每每看到电影他就会想起那个大学生的话,他的眼神会柔和一点,露出他心底的憨直,恢复了当年和嘎斯在水塘里游泳洗澡然后拉屎那样纯朴的本色。
就这么过了两年,老大算是在监狱里吃香的喝辣的了,他又看了一个老电影《小街》。电影内容倒没什么,城里年轻人在特殊时期的胡腻老大看不懂,不过里面的插曲让老大不但眼神变了还流下眼泪。歌词是这样的:
啦……啦……啦……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没有哀愁
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
啊……啊……
每当我唱起它
心中充满欢乐 ……
听到这歌老大想起了自己的老娘,算算日子自己离家三年多了,老娘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越想越着急,老大只觉得一天也等不了了,便狠了狠心挖地道想越狱跑出来。
似乎挖地道是从古到今最成功的越狱方式,老大挖了两年多地道终于挖好了。在钻进地道的那一刻开始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头了。
老大再次翻山越岭地回到家,发现几年的光阴物是人非,家已经不存在了。几间瓦房残破不堪,老娘已经病死,媳妇早就改嫁他乡。村长因为贪污也被撤了职,现在人嫌狗不待见,连村西头王寡妇家都进不去了。
老大千辛万苦地想回家,可家没了。老大在老娘的坟上待了一夜,想起这几年的离奇生活想哭却哭不出来。
早上嘎斯来给老大的老娘上坟,在晨雾中嘎斯看到一个犹如匕首一样的身影消失在林中。嘎斯认出了老大,他想叫又没叫出声来,那个如刃一样的眼神让嘎斯知道那个当年和自己一起光着腚在田里玩泥巴长大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
嘎斯怅然之余再报官的想法在他心里转了一圈,马上他就把这念头随着自己肚子里的屁给放了。
既然老大这次能逃出来,下次要再逃出来可就不是吐自己一脸唾沫那么简单了。
之后,老大云游四方,混入了进城打工的民工大军,虽然四处都贴有通缉他的照片,可老大的面貌变化太大,没人能认出他。和监狱里造假证的犯人的学习让他知道去哪儿找什么人可以怎么做一个以假乱真的身份证,老大改头换面开始了新生。
老大做过了各样的工作,泥瓦匠、搬运工,最后在码头上扛大包。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和牢里一样都是弱肉强食,他利用在号里学到的生存能力带着几个扛包的苦力拎着扁担揍扁了码头上的地痞成了码头上苦力们的老大,逐渐垄断了码头的人力运输事业。
老大逐渐变得有钱了,不再自己扛包,闲暇之余就去录像厅看电影,多亏了当时充斥在大陆录像厅里的香港黑帮电影起到了对老大继续教育的作用。从《英雄本色》到《古惑仔》系列,老大想起了大学生对他说的至理名言,不明白的时候多看电影。
他时刻学习黑帮片里老大们的手段占领了当地的舞厅歌厅。老大更有钱了以后就放高利贷,控制了几个搞建筑的包工头,用同样的道理,他从小城市进军到了大城市,老大的事业急速地发展起来。
随着生意的扩大,他对自己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学着城里人一样要体现品味档次。以前是坐出租穿大背心裤衩喝白酒抽卷烟,现在他坐奔驰穿西服喝红酒抽雪茄。当然这些改变还是要归功于电影。到了大城市他的电影片目也随之进行了文化品位的升级,从香港的黑帮片过渡到了美国黑帮电影,《赌城风云》《教父》,还有《美国往事》。
老大自己总结了一句话,是电影改变了他的命运。
生活改变了,人必然也随之变化,学着电影里穿衣吃饭越来越讲究的老大,皮肤开始变细变白,肌肉开始松弛,身体开始发福,脑袋开始有点谢顶。他向一个标准商人的造型发展,他身边的女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个个都比当年乡下的媳妇年轻漂亮得多。
唯一一点没变的是他对读书人的好感,当年那个大学生对他的影响太深了,没有大学生跟他说的那句话他哪有今天?
只可惜他身边读过书的人太少,最多不过是初中毕业。这一点让他头疼不已,他开始让自己的手下上学,物色能发展有潜力的知识型人才。手下人写个东西就算不能像电影台词一样也起码能成段成句吧?所以老大看中了大头,大头也迅速地成为老大的左膀右臂。
还有一点就是老大什么生意都做,赌场、夜总会、高利贷、建筑公司,但就是毒品的生意不干,连后来的摇头丸都不卖。原因很简单,因为电影里那些正面的黑帮人物总会说一句话:毒品的事情不能干!而反派的黑帮人物则往往会干毒品这龌龊的勾当最后被正面的黑帮人物剿灭。
电影中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走向居然成了我们这位老大从事黑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这恐怕是所有电影工作者都没想到的。
老大算是什么都有了,没有他买不来的,没有他得不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女人。可老大知道自己从没在乎过现在身边的那些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女人们,在他心里总是隐隐地惦记着当年那个害他入狱的“潘金莲”,那个皮肤白里透红、脸上总是挂着两块“村里红”、笑起来还有两个大酒窝的乡下女人。虽然就是这个风骚的娘儿们毁灭了老大做一个淳朴忠厚老实巴交的农民的人生,但是老大就是忘不了她。
这女人已经在老大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每次想到她,老大似乎就能闻到那个健康而结实的身体里散发出的带着春播时肥沃泥土味道的芳香气息,但同时老大的脑海中又会出现村队部里那黄黄白白的两坨肉相互纠缠的上下折腾,使老大又闻到了那类似猪大肠的味道而一阵阵地恶心。
两股味道交织着出现让老大饱受折磨,他想意志坚定地把那女人的形象从自己的脑子里连根拔去,可就是做不到。
“这样的娘们儿自己都忘不了,人就是贱!”老大总结出了人生真谛。
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人一定会开始精神上的追求。老大又开始不满足了,他太喜欢电影了,当年在囚车里确定的世界观让他到现在都固执地认为只有电影才是最美好的、最真实的。
他开始投资电影,一次又一次,虽然每次都被不靠谱的制作人员蒙了,拍出来的东西让他自己都觉得差劲,但是老大还是大把大把地往电影里扔钱。
他把电影看成他的梦想,也是他寻找真实的唯一机会。
最终老大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