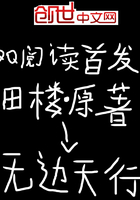有句话说得好,你可以像猪一样懒,但没办法像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可祁月似乎能做到这一点。她原先只是容光焕发,对学业不太专注,几周之后,情况越发坏了。她上学开始迟到早退,作业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就一抄了事。考试成绩自然不佳,但她似乎也不在意,照样喜笑颜开。此外,向来不修边幅的她,最近越来越注意仪表,穿戴也时尚光鲜了许多。有一天她走进教室,脸上的痘印也不见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擦了粉,但手段不太高明,粉擦多了,脸就显得惨白惨白。
杨略就坐在祁月的身后,自然发现了异样,趁着祁月中午不在,就召集了几个哥们儿。他特意也叫上了葛怡。毕竟,关注共同的朋友,的确是接近葛怡的最佳机会啊。
“我说各位,大家发现了没有,祁月最近很不对劲啊。”
“是有点反常。”葛怡把上课时祁月的种种表现说了一遍。这次,她出于关心,似乎把自己与杨略间的芥蒂忘记了。
曾泉咧着大嘴,坐在那儿,腿是一抖一抖的。
“担心个头啊!这叫十八少女芳心动嘛……嘿嘿……”
“就她?哈哈……”陶坷坷一屁股坐在杨略的桌子上,双手插兜,摇摇头,一脸的戏谑。话是没往下说,但大伙儿分明都听见了:嘿嘿,就她那体型,那满脸的痘印……哪个小子这么不开眼啊。
葛怡抬起手,作势要打他:“坷坷,你就积点口德吧。”
陶坷坷一脸的无辜和惶恐。
“我,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是没说,心里可全说了。”
“哟,葛大小姐会读心术,”陶坷坷捂着胸口,眼睛睁得老大,“那,那我说什么了?”
“你说……说……反正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陶坷坷憋不出了,脸上绽放出调皮的光芒来。
“哈哈,这说明啊,你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葛怡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祁月是她同桌,也是好友,本不该这样损她。
杨略给她打圆场了。
“别闹了。你们都上过那个心理保健课吧,这祁月性情大变,可不是好兆头。”
曾泉大摇其头。
“你啊,真是杞人忧天!好像人家祁月就该整天哭丧着脸似的。”
陶坷坷也说:“就是,这狗尾巴花也有个春天啊。”
葛怡又在责怪陶坷坷口不择言了。
正在这时,祁月蹦跳着回来,辫子一甩一甩,嘴里叼了根棒棒糖,虽说体型略显臃肿,但依然是一副青春少女的活泼模样。走到他们面前,欢快地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呢?”
“在说你呢?”曾泉到底嘴快。
“哦,说我什么坏话?”
“哪敢啊……”
“嗯?是敢怒不敢言?”
“不不不,就说你春光灿烂,朝气蓬勃,这是有喜啊……”
一记八卦掌就脆生生地劈在曾泉的肩膀上。
“你才有喜呢!”
曾泉轻轻给自己掌了嘴。
“嘿,瞧我这张嘴,话都说不利索。我是说,你这是有喜事啊。”
祁月顿时笑逐颜开。
“那当然!”
陶坷坷也来了兴致。
“跟我们说说看,是哪家的帅哥啊?我们帮你把把关。”心里却在想:是哪位兄台品位这么独特,倒要见识见识。
祁月一脸的不屑,用手指点了点几个男生,摇了摇头。
“你们啊,唉,tooyoungtoosimple,整天想着那点事。”
“好,您不young也不******,那您的喜事是……”
“真想知道?”
众人都在点头。
祁月一脸神秘,眼睛定定地一个一个看过去,然后缓缓地吐字。
“你们看到的我,真的还是我吗?”
这话一说,众人面面相觑。
过了半晌,曾泉说:“你,整容了?”大家都暗笑:哪个整容医生技术那么差,估计得关门歇业了。
祁月摇头。
陶坷坷忽然一拍桌子,作恍然大悟状,指着她。
“你中彩票了!快,快,请客!”
祁月依然摇头。
她的一番故弄玄虚,让杨略心里也有了极大的好奇。
“那你是收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他是当玩笑话说的,谁知祁月的脸上骤然绽放出笑容,还打了个响指。
“Bingo!”
陶坷坷顿时大受打击。他是立志要去德国留学的。
“我这都没敢申请呢,你悄没声的,怎么就申请成功了?你这是闷声发大财啊!”
葛怡一把抱住她。
“真的吗,祁月?”
可祁月依然摇头,脸上保持着笑意。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们看到的我,眼前的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得,又回来了。陶坷坷等人失去了兴趣。此时上课铃响了,就各自回到座位。而祁月依旧喜滋滋地看着天花板和窗户,与周边凝神静气的同学相比,真是飘飘然有超凡绝俗之感。
下午的课结束了,葛怡和祁月去打羽毛球。路上葛怡不免又追问了几句,祁月靠近了她,轻轻地说:
“葛怡,其实,你看到的我,并不是我。”
“祁月,你又来了。”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现在的我。”
“……”
“你不懂?”
“不懂。”
“那我告诉你实话,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好。”
祁月在葛怡耳边轻轻地说。
“我……穿越了。我是从6月9号穿越过来的。”
“啊?”
看祁月一脸的认真,葛怡觉得她要么是开玩笑,要么就是脑子真出问题了。
“你知道6月9号意味着什么吗?”祁月一脸神秘地问。
“高考结束了,我们解放了。”
“没错!”祁月的眼睛里露出狂喜的光芒,“你终于理解了。我就是从那时候穿越过来的,顺便,我还带来了高考答案,全部哦!”
“你怎么带来的?”
“全在脑子里。”
葛怡愣了半晌,不知该怎么接茬。
“难怪你都不听课了。”
“那当然!有了高考答案,谁还去听课啊。葛怡,这事我告诉了你,可别说出去。咱俩关系好,到时候我会把答案透露给你的,咱们一起考上名校,哈哈——”
葛怡心里莫名地害怕起来,一时拿不准祁月说的是假话,或者是疯话。她希望祁月忽然噗嗤一乐,就像愚人节常玩的那套把戏一样。可祁月一直在畅想,而且眼神无比愉悦和真挚。
葛怡忽然想到了一个破绽,可以试试祁月说的话到底属于哪一类。
“祁月,如果你是三个月后的你,那现在的你藏哪里去了呢?”
祁月猝然一惊,微笑凝在脸上,眼睛瞪得老大,思考了很久,脸上渐渐退去了血色,变得苍白可怕,嘴里不自然地抖动。
“对啊,现在的我呢,到哪里去了?肯定在家里。不对,我早上刚从那儿来,根本没看到。在学校?还是在街上?她,她,不,是我,我到哪里去了?”
她看上去很不安,一会儿捂着脑袋,一会儿又前后徘徊,眼睛四处乱瞧,凄凄惶惶的无所适从,嘴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一转身,往体育馆的方向走了。脚步很急,很飘。葛怡看她不对劲,赶紧跟上去,一把拽住她。
“祁月,我是逗你玩呢,你不就是你吗?”
“不,你不懂穿越的原则,要是现在的我丢了,出事了,那以后的我都会消失。我……你别拉我……我要去把我找出来。”
葛怡快要哭了。
“祁月,你别吓我!你,你别玩了!”
可祁月对她不理不睬,猛力挣脱了她的手,径直朝前走去,一路往树丛里张张,向角落里望望,连垃圾箱的盖子也掀开看看,嘴里不住嘀咕:
“不在这里……不在……我,我去哪儿了?……”
葛怡一时六神无主,心里又极害怕。因为在这一刻,祁月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怪物一样,显得无比陌生而恐怖。她没有办法,就想要找个人来帮忙。可她刚才是在羽毛球,所以连手机都没带。她只好跑到一旁的小卖部,拿起电话机。可是打给谁呢?照理说,她该告诉欧阳老师。可她只记得杨略的手机号码。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拨了过去。
杨略在篮球场上知道了情况,也丝毫不敢怠慢,给打电话给欧阳老师,打了报告,就跑到运动场与葛怡会合。
“祁月呢?”
葛怡看到他来,心情安定了些。
“她往体育馆那边去了。”
于是,两个人一路小跑,体育馆里却没有,体育馆旁边就是教学楼。杨略眼尖,透过他们教室的窗口,看到有人爬上椅子,去够那个黑板上方的挂钟。而看衣服的颜色,应该是祁月。他们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梯,教室的门却被锁紧了。透过楼道边的窗户往里看,只见教室里只有祁月一个人,站在椅子上,给挂钟调了时间和日期,又挂回原处,然后从椅子上跳下来。
“祁月,祁月!”葛怡拍着玻璃,大声地喊。
祁月转过脸来,显然是听到了,却并不理会,闭上了眼睛,嘴里在默念着什么,忽然睁开眼睛,小跑了几步,一头撞在了墙上。
葛怡尖叫了一声。
祁月摸摸额头,似乎晕了一会儿,往四周看了一圈,发现葛怡和杨略还在窗外,脸上就露出绝望的表情,并且惊慌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定了定神,看看挂钟,又闭上眼睛,嘴里絮絮叨叨,念着什么咒语,然后,看她的样子,又要去撞墙了。
葛怡和杨略一起大喊:“祁月,不要啊!”
正在这时,欧阳老师到了,身后还有几个保安。他用钥匙打开了门,冲进去,一把将祁月拦腰抱住。
“放开我!放开我!”
祁月像一头困兽一样,拼命挣扎,双臂乱挥乱打,脸上糊满了眼泪,声嘶力竭地叫道:“我要回到一个月前去,要不然,我就找不到我了!”
欧阳老师和几个保安压根就听不懂,几个人一起动手,又是抓胳膊,又是抬腿,将奋力挣扎的祁月架到办公室里去,按在了椅子上。祁月还在不停地喊叫:
“求求你们,让我回到一个月前去。”
欧阳老师累得气喘吁吁,回头问杨略和葛怡。
“她这是怎么了?”
葛怡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欧阳老师还是一头雾水,但基本确定了情况,就拿起手机,给医院打了电话。从他急促的话语中,杨略和葛怡听到“妄想”、“没有自知力”之类的词语,心里越发着急。因为他们上过心理健康课,知道这是精神疾病的表现。
祁月终于累了,瘫倒在椅子上,嘴里有气无力地念叨着。
不多时,就来了一辆救护车。祁月不愿去,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护士架起她,从办公室出来。祁月大声喊救命,一路挣扎,死命地蹬腿。全校的师生都站在走廊上看,但她终于在寒风中被塞进救护车了。
随后,从欧阳老师的嘴里,大家得知了一个消息,祁月被怀疑是精神分裂了。
“每年两个。还有一个是谁呢?”
一条小道消息在各年级悄悄蔓延,大家都在起劲地议论。据说,近几年里,学校每年里都会冒出两个不正常的学生,要么是“神经病”,要么是自杀的,其中又以高三学生为主。你瞧,今年才一开春,祁月就占了个名额。
但精神分裂毕竟不是传染病,所以大家觉得与己无关,并不恐慌,反倒有种猎奇的刺激感,个个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神色。
只有杨略和葛怡等人觉得忧伤难言。他们与祁月朝夕相处,虽说祁月一直抑郁寡言,但到底是个乖巧的女孩,做起手工艺品来十分拿手,十字绣的手机套啊,针织的茶杯垫啊,剪纸啊,都极精致,做好了常常送给大家。只可惜她成绩不好,一切特长都只是邪门歪道,自不免倍感压力沉重,前途无望,心里淤积着太多阴郁的毒素。
葛怡说:“其实,我们有谁敢说,自己的心理绝对健康呢?”
杨略也叹了口气,点了点头,静静地注视着葛怡。葛怡也发觉了,与他静静地四目相对,然后又静静地转过脸去。
第二天,欧阳老师开了个班会,脸色沉重地说起了祁月的事情。
“昨天,祁月去了医院,吃了点药,神智清楚了。还好,她的情况不严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不过,作为老师,我没有好好保护她,真的感觉很难过,很歉疚。”
他说,祁月是个农村孩子,家境贫寒。但她很争气,从小学到初中,成绩极好,一直是学校的状元,得到了老师的青睐和同学的羡慕(或许还伴随着疏远),这令她深感自豪。逐渐的,成绩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成了真正的精神贵族。家里穷一点怕什么?我有成绩!相貌一般怕什么?我有成绩!没什么朋友怕什么?我有成绩!
她凭借着这种精神优势,一直升到了高中,满怀憧憬地来到全省数一数二的学校。忽然,她发现自己的优势不见了。在成绩方面,她只能排到一百来名。在文体方面,她啥也不会。而身边同学个个优秀,有人满口流利英语,而她的英语还带着地方口音。有人对历史掌故如数家珍,而她只记得历史书的哪一点。还有人钢琴舞蹈都很在行,而她从未摸过琴键,穿过舞鞋。好吧,她会做手工艺品,可是,这个与高考可没有什么关系啊。
于是她一下子就懵了,优越感荡然无存,精神支柱摇摇欲坠,陷入了抑郁沮丧之中。
或许她为自己的出身深感自卑,觉得如果自己生在城里,父母都是博雅的知识分子,她必然也会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外语更是说得流利。或许她深夜里默默哭泣,因为看不到前途。
她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自卑,抑郁,很难和现在的同学交心。而她以往的同学,又因为她升入名校,地位变得悬殊。如果她还去倾诉,说自己心情不好,就好像嫁入豪门而向穷姐妹抱怨鲍鱼龙虾太腻味一样,难免遭人饱含嫉妒的讽刺。
于是她陷入寂寞,只能抱着课本,不住地学习,做题,学习,做题。可是,在压抑的情绪中,学习是件艰难的事情。她找不到乐趣,只凭借着意志力,像攻克堡垒一样,孤独地向各门学科发出冲击,但她的排名并没有进步,这又加重了她的抑郁。
这些负面情绪在心里压抑得久了,慢慢熬成了一锅毒汁,无处释放,就一点点腐蚀着她的心灵。终于有一天,刺激性事件发生了,像催化剂一样,让她产生了幻想。这个刺激,或许就是期末考试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