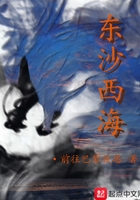瓦里图斯·奥古斯都是东部帝国——梅里城的皇帝,管理国家的责任自然落在他的肩上。尽管这名号不小,但他的领地不大,臣属稀少。梅里城如孤岛悬于山谷密林之中,城市人口刚过两万,包括大约三千白人和一万九千混血人种。在城外的湖边乡村,以及梅里城东岸居住着两万六千黑人臣民。
这天,听取报告结束,皇帝回到宫廷御花园一处藤蔓覆盖的凉亭,用一个多小时与近臣闲谈,并聆听乐师的演奏。皇帝的闲暇时间就是这样度过。这时一个近臣走来,报告贵族福浦斯要求觐见皇帝。
“觐见的时间已过,”皇帝愠怒道,“让他明天来好了。”
“他坚持请求陛下的恩准。”
瓦里图斯对侍从说:“难道我就不能有一会儿放松?非得让福浦斯这样的傻瓜拿些莫名其妙的瞎话来打扰我吗?”
一会儿,当福浦斯来到皇帝的面前,皇帝一脸的冷淡。
“我来了,最尊敬的陛下!”福浦斯说,“为了尽一个罗马公民的职责,我首先关心的应是皇帝的安全。”
“你要来说什么?”瓦里图斯粗鲁地说,“快点说!”
“梅里军团来了一个陌生人,自称是一个蛮族人,来自日耳曼,但我相信他是来自撒奎纳琉斯军团的密探。据说在那里卡修斯成了苏布拉图斯高贵的客人了。”
“你听到了关于卡修斯的什么?他与你要报告的事有什么关系?”皇帝问道。
“我是听说的,这个……”福浦斯结结巴巴地说,“当然也可能是谣传……”
“我听到的关于卡修斯的谣传太多了。”皇帝说。
“我只是听说,”福浦斯红着脸不安地解释,“我不知道真相,我只是听说。”
“那么,你究竟听到了什么?”皇帝又问道,“说出来!”
“这种说法在澡堂子里很普遍,你派卡修斯出使,结果他图谋叛变通敌,立刻去见了西部皇帝苏布拉图斯。苏布拉图斯把他待为上宾,他们合谋计划攻击梅里军团。”
瓦里图斯听了皱着眉头说:“没有根据的谣言!”他又问,“那这和那个陌生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没有人向我报告有这么一个陌生人?”
“这我不知道。”福浦斯说,“这也是我加倍感到有责任来报告的原因。因为窝藏这个陌生人的人是一位非常有势力的贵族,他可能有某种野心!”
“他又是谁?”
“塞普蒂默斯·法沃尼乌斯。”
“塞普蒂默斯·法沃尼乌斯!”皇帝叫起来,“不可能!”
“不是完全不可能,”福浦斯大胆地反对,“陛下只要回想一下,卡修斯和勒普斯,也就是法沃尼乌斯的侄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法沃尼乌斯家就像卡修斯的另一个家一样,所以卡修斯转而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野心在宫廷之外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陛下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
皇帝听了不由激动起来,离开座位来回踱步。告密者的眼睛眯起来仔细看着他,福浦斯内心充满了邪恶又得意的预感,认定他的话一定发生了效用。
瓦里图斯终于停下来,转身向一位侍臣道:“如果福浦斯是满口胡言的话,那么就让海格力斯神杀掉我吧!这个陌生人长什么样子,福浦斯?”
“他是个白人,面色与我们贵族稍有不同。他装着说我们的语言,却故意夸张某些音节,假装不熟悉我们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他欺骗手段的一部分。”
“他是怎么到梅里军团来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官员向我报告?”皇帝问。
“这你要问勒普斯,”福浦斯回答,“他是看守国门的司令官。城外湖上村庄把这个人送来的时候正是他当值。陛下也知道,只要对当值的人敬献点儿孝敬,这些人就可以假冒一些角色。”
“你这么清楚这里面的门道,福浦斯,”皇帝说,“让人不得不怀疑你也这么干过。”
“陛下英明……”福浦斯吓出一身冷汗,发白的脸上强挤出笑容。
“那么,”皇帝转身对一个官员说,“把法沃尼乌斯、勒普斯还有那个陌生人都给我抓来!”
话音刚落,一个近侍走进花园报告:“法沃尼乌斯要求觐见陛下。同来的还有他的侄子勒普斯,还有一个陌生人。”
“带他们来!”皇帝说。对刚派下正要去抓人的官员说:“我们听听法沃尼乌斯能说些什么。”
不一会儿,法沃尼乌斯三人进了花园。当他们走近时,法沃尼乌斯和勒普斯不约而同都瞟了福浦斯一眼。
皇帝问勒普斯:“为什么没有马上通知我捉到一个俘虏?”
“是有一点耽搁,陛下。”年轻的官员回答说,“我让他先洗澡,换件衣服才好见陛下,因为他毕竟是个蛮族头人。”
“你带他到这里来干什么?”皇帝说,“我们梅里军团不是有土牢给那些撒奎纳琉斯来的俘虏吗?”
“但他并不是从撒奎纳琉斯军团来的。”法沃尼乌斯不高兴地看了一眼福浦斯。
“那么你究竟是从哪里来?到我们国家来干什么?”瓦里图斯转向埃里克。
“我来自日耳曼,一个你们的历史学家知道的地方。”埃里克回答。
“我想你曾经在你的国家里学过我们的语言吧!”瓦里图斯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道。
“是的,确是这样。”
“那么你从来也没有到过撒奎纳琉斯军团吗?”
“从来也没有!”
“我猜想你大概去过罗马。”瓦里图斯笑起来。
“是的,多次去过。”
“那么现在那里谁是皇帝?”
“现在那里没有皇帝了!”埃里克回答说。
“罗马没有皇帝?!”瓦里图斯惊叫起来,“如果你不是来自撒奎纳琉斯军团的密探,那么你也是个疯子,或者你两者都是,因为只有疯子会希望我会相信这样的故事。没有罗马帝国,真的吗?”
“现在确实没有罗马帝国了。”埃里克回答,“我听勒普斯告诉我,您的国家与外面世界失去交往已经是一千年了。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国家再说你们的语言了,只有僧侣或者学者还会说这样的话。蛮族日耳曼、法兰西和不列颠都建立起实力强大的文明帝国,而罗马现在只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勒普斯这时满脸笑意对叔叔法沃尼乌斯小声说:“我对你说过你会喜欢他的,看在上帝的面,我希望他会告诉瓦里图斯关于轿子的故事,现在那里的轿子每小时会跑五万步呢!”
这时埃里克的态度和语言中都有一种令人不得不相信的力量,就连瓦里图斯也对这些貌似荒诞的故事半信半疑了。
皇帝转向福浦斯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人是来自撒奎纳琉斯军团的密探?”
“除此以外他还能从哪儿来?”福浦斯强辩说,“我们知道他不是出自梅里军团,那他肯定只有从撒奎纳琉斯军团来喽。”
“那么说你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了。”
福浦斯无话可说,只在那里嗫嚅。
“出去!”瓦里图斯皇帝发起火来,大声地说,“我以后再跟你算账!”
福浦斯满脸丧气地离开了花园,他恶狠狠地盯着法沃尼乌斯和埃里克的眼神,说明他不会就此罢休。在福浦斯离开花园以后,瓦里图斯看了埃里克好长时间,好像要弄明白站在他面前的这个陌生人究竟是怎样的人。
“那么现在罗马是没有皇帝了。”瓦里图斯边沉思边问,“当撒奎纳琉斯领着他的步兵队离开埃及时,涅尔瓦(公元35年—98年,古罗马五贤帝时期第一位皇帝。)还是皇帝。那是涅尔瓦统治的第二年,罗马历848年2月前六天。从那天以后撒奎纳琉斯军团再没有收到过任何从罗马来的消息了。”
埃里克听了,赶快在心里把瓦里图斯嘴里的日期换算成公历。然后说:“2月1日的六天以前,”他重复道,“那应该是1月25日。848年,也就是涅尔瓦死亡的那天,用今天的纪年应是公元98年。”
“那么涅尔瓦以后的皇帝又是谁?你知道吗?”
“是图拉真(涅尔瓦病逝后继位的罗马皇帝。)。”埃里克回答说。
“为什么你一个蛮族人知道这么些关于罗马的历史?”皇帝问。
“我是研究这些事的学生。”埃里克回答,“这个专业是我的志向,我要成为这方面历史的权威。”
“你能把涅尔瓦之后的历史都写下来吗?”
“我能把我读过的、记得的都写下来,”埃里克说,“但是这要花很多时间。”
“那么你来把这些都写下来,”瓦里图斯说,“你会有足够时间的。”
“但是我没有在你的国家长住的计划啊。”埃里克不同意。
“你必须留下来,”瓦里图斯说,“而且你还要写完瓦里图斯·奥古斯都——东部皇帝的统治史。”
“但是……”
“够了!”瓦里图斯打断,“我是皇帝,这是我的命令!”
埃里克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勉强笑了笑。罗马的皇帝,以前只是陈旧的牛皮文书和风吹雨打的碑刻残片,直到现在才变得真实起来。
这里确实是一位皇帝,尽管他的帝国不大,不过几平方公里,和一大片沼泽地的沿岸,坐落在一个不知名的峡谷中,他的臣民数量也不超过五万。但它毕竟是一个帝国,统治它的是一位皇帝,瓦里图斯·奥古斯都。
“来,”皇帝说道,“我领你去看看我的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方便你工作的地方。”
所谓图书馆设在一条长廊尽头,是一座圆形屋顶的房间。瓦里图斯骄傲地展示这里整齐摆放的数百卷牛皮卷宗。
“这里!”瓦里图斯随便拿起一卷说,“这是关于撒奎纳琉斯的故事,以及直到我们梅里军团建立的历史。拿上它,在你有空的时候读一读。这段时间你可以和法沃尼乌斯和勒普斯生活在一起,我要他们对你负责。以后每天你可以到宫里来,我将口授我的统治史。现在你可以和法沃尼乌斯一道走,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
埃里克他们三个人走出皇宫,埃里克哭笑不得地对勒普斯说:“有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一个俘虏还是一个客人?”
“我看你两者都是,”勒普斯回答说,“即便你还算半个客人,那对我们也算幸运了。瓦里图斯皇帝是一个自负、傲慢而且残忍的人。福浦斯在我们觐见之前就说了我们许多无中生有的坏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皇帝后来改变了态度,我不知道,但我们总算很幸运。”
“但是要好几年才能写成一部罗马史。”埃里克抱怨说。
“可是你如果拒绝这件事,你会远远活不到完成一部罗马史所花的年头。”勒普斯说。
“梅里军团的生活也并不难过。”老人法沃尼乌斯插进来说。
“您说得对。”埃里克说,脑子里完全填满了老人女儿美丽的面孔。
回到家中,埃里克以一个考古学家的本能,迫不及待要仔细阅读皇帝给他的古老卷宗。他立刻回到拨给他的居室,躺在一张长沙发上,解开捆扎的线绳,打开了发黄的文卷。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卷手写的古老的拉丁文文书,充满了涂改、删削的文句,年深日久的纸张也发了黄。这和他过去看过的任何手卷大不相同,不像是那些保存良好的专业史家书写的罗马史。只要看上几眼就会发现,它很可能是一些军队的非文书专业者的手迹。
这些手稿文句拙劣,辞藻生涩而僵硬,还有不少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或埃及的俗词俚语,此外,还有许多小地名和很少见的历史名词,可能在他们那个时代也鲜为人知。这增加了埃里克阅读的难度。文本中提到的有人曾经救过撒奎纳琉斯性命的那座埃及小城,似乎在今天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但正是在这里,撒奎纳琉斯的名字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里于公元90年战胜了敌对的涅尔瓦,而后来涅尔瓦却成了罗马的皇帝。而撒奎纳琉斯,一个帝国的创建者却在罗马古代的任何编年史中了无踪影。许多历史事件从这尘封已久的文书中重新活跃在埃里克的面前。
带着浓厚的兴趣,埃里克读到了撒奎纳琉斯怀着不满和愤怒被涅尔瓦贬谪到遥远的底比斯古城。
撒奎纳琉斯以第三人称在这里写道:“撒奎纳琉斯,第十罗马兵团第三队的长官,于罗马历846年驻扎在底比斯城亦即涅尔瓦黄袍加身不久,被指阴谋反对皇帝。
“大约于罗马历848年2月1日的前五天,一罗马使者来到底比斯城,传达涅尔瓦的命令,调解撒奎纳琉斯返回罗马加以逮捕,但撒奎纳琉斯并无意回到罗马。由于无人知晓此事,撒奎纳琉斯当即以短剑杀死了这名信使,并且在部队中散布来人是罗马派来的刺客的消息,而撒奎纳琉斯出于自卫将他杀死。
“撒奎纳琉斯称涅尔瓦将派出更强大的兵力来解散部队,因此他说服部下跟随他沿尼罗河寻找一片新的国土。在那里他们将远离妒忌与邪恶的罗马皇帝涅尔瓦。此后不久,他们就开始了远征。
“正当他们即将远征之时,有一支船队,有近百艘帆船来到附近的海港进行贸易。这一队商船每年都带来丰富的商品,有丝绸、珍宝、香料以及其他许多商品。他们也把这些商品装饰在骆驼背上,沿尼罗河上游的一些城市运送,在亚历山大港再装船运到罗马去进行交易。
“随行商队的还有数百名来自印度,甚至中国的奴隶,也有一些遥远的西北亚的浅肤色人,这是商队从蒙古劫掠者手中买来的。这些人大多是年轻的女孩,是准备运到罗马进行拍卖的。对于撒奎纳琉斯和他的部下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军团洗劫了船队带来的所有妇女、奴隶和财物。
“接下来,这五千步兵队先后到过几个地方。但直到罗马历的83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才发现了这条隐蔽在群山中的峡谷。于是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撒奎纳琉斯军团的王国。”
“读得有趣吗?”一个声音在门口说。当埃里克抬头看时,勒普斯正站在门槛边。
“很有趣。”埃里克坦率地说。
勒普斯耸了耸肩说:“我猜如果由那个老撒奎纳琉斯来写出真相也许更有趣。”他接着说,“他持续20年的统治我们知之甚少,他于撒奎纳琉斯20年——相当于罗马历873年——被人暗杀。这个老家伙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城市,而且颁布了新的历法,还把他的头像铸在了金币上,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金币。但是在梅里军团我们试图尽可能地忘记撒奎纳琉斯。”
“那么我常听你们提起的撒奎纳琉斯城是怎么回事?”埃里克追问道。
“它是撒奎纳琉斯最早建立的城市,”勒普斯回答说,“过了一百多年,那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变得没有保障,一切都得祈求于暴虐的君主。也就在这时,欧努斯·哈斯塔革命了,他率领几百个家族来到峡谷东面的这个岛上,建立了城市,成立了梅里城,已经1700年了。这些家族的后代生活得相对和平也安全,只是一直与撒奎纳琉斯城保持着战争状态。”
“基于相互的需要,两座城市经常进行一些商业交流,但这种交流也不时被劫掠和战争打断。两座城市彼此的矛盾、怀疑都因为畏惧会被另一座城市兼并。”
“不过现在梅里城在它皇帝的领导下既幸福又满足了吧?”埃里克问道。
“这个问题如果我诚实地回答了,我就会失去幸福和满足。”勒普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
埃里克又问:“以后我每天都要到宫里听瓦里图斯讲他的故事,写他的统治史,我会更了解皇帝,但同时也许会招来严重的麻烦,或许对你和法沃尼乌斯不利,因为皇帝声言你们要为我负责。我愿意保证,我绝不会把从这里听到的讲出去,如果有什么是你事先提醒过我的话。”
勒普斯轻轻倚着墙,玩弄着他佩刀的刀柄,一面在思考什么。少顷,他突然抬起头盯着埃里克说:“我相信你。首先我感到你是一个可信任的人;第二,伤害我和法沃尼乌斯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梅里城的市民并不喜欢这位皇帝,他既傲慢又残忍,不像我们习惯的先帝那样。
“上一任梅里皇帝是一位仁慈的人。但是当他去世时,他的儿子才一岁多。所以,瓦里图斯也就是老皇帝的兄弟才接了王位。
“前一位皇帝的儿子,也就是瓦里图斯的侄子名叫卡修斯。因为他深孚众望,所以引起现任皇帝的嫉妒和憎恨。最近他被皇帝派出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去到了峡谷西面的某个地方,不少人都以为这是事实上的放逐,只是现在这位皇帝坚持说事实上并非如此。没有人知道卡修斯接受的命令是什么,他在一天晚上秘密地只带了几个奴仆就出发了。
“人们都相信他是被派往撒奎纳琉斯军团刺探军情。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这个使命等于派他去送死。假如这是事实,那么人民会起来反对瓦里图斯,因为他的侄子卡修斯在梅里军团是非常有威望的。
“好!行了,我不再用梅里军团里的不愉快的事打扰你了。拿着你的读物到花园里去吧!那里的大树荫要比这里凉快多了。我一会儿也会到那里去。”
当埃里克伸展了身躯躺在法沃尼乌斯家花园里树荫下的草地上时,他脑子里不再想撒奎纳琉斯军团的历史,甚至梅里军团里某些人的灾祸都一股脑儿忘到九霄云外。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探索者和一个考古学家,他应该留在这里,探索这个峡谷中发生的历史故事和这里的政府、居民、风俗。但是长时间把自己关进东部帝国圆拱形建筑的图书馆,用苇秆笔和拉丁文书写古罗马的历史,对他来说实在没有多少吸引力。
亚麻布新衣的沙沙声和穿在脚上软软的凉鞋踏在花园的砾石路上的感觉都时时打断他的一些异想天开。只有当他看到法沃尼娅美丽的脸庞,这一切,诸如古代罗马、筹划逃跑计划等等都被女孩甜蜜的微笑驱散到九霄云外,就像晨雾遇见了明媚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