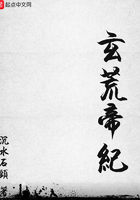自从那次离别,再也没有了梅雨婷的音讯。任之良打过几次手机,都无应答。一股淡淡的愁绪笼罩在任之良的心头。他说不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在和朋友的闲聊中,对异性之间是否存在友情的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异性之间,除了爱情,没有友情可言。而他却坚持认为,异性之间是存在友情的,只是这种友情不同于同性之间的友情罢了。有人问他,这两种友情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也回答不出来。他问自己,他和梅雨婷之间,与林思凡之间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友情?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也不完全是。他和梅雨婷是萍水相逢,没有亲情也没有利益关系,处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说什么,无拘无束,开心娱悦。他想,这其中不排除异性间相互吸引爱慕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吸引,关键不在“性”,而在于心,在于说不明道不清的一种微妙的情愫。他和林思凡也一样,尽管他们做过同一件工作,为了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同力合作过,但把他和林思凡联系在一起的,绝非这个,也非纯粹的性,而是另外一种东西。
这段时间,她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他知道,这是暂时的,不会永久地消失。这个鬼丫头,不知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正在酝酿着什么鬼主意,出其不意地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告诉他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让你喜也不是忧也不是。梅雨婷则不同,她八成是永远地消失了,有可能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他后悔那天走得太急,没有送送她,没有好好聊聊,建立某种联络方式,跟她进行联系。现在一切都晚了,除了深切的怀念,还能怎么样呢?
任之良正这样想着,王一丹进来了,她面带笑容,问:“在忙什么呢?”
任之良站起来,不冷不热地说:“也没什么忙的。你坐。”
王一丹坐下来,嘘寒问暖,一幅关心爱护部下的样子,她始终笑眯眯的,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堆起的笑容里,很容易让人想起“无知”二字。
任之良给她沏了杯茶,放在她的面前。说:“请喝茶!”王一丹接过茶杯,似乎在不经意间,轻轻地碰了一下任之良的手,任之良微笑着回到自己的座椅上。王一丹喝了一口茶,咂巴咂巴嘴,说:“好茶!”
任之良心里说:十块钱能买一斤,也算好茶?嘴里却说“王局长喝着好就行。”
王一丹说:“我那儿有筒好茶,是我的一个亲戚从杭州带来的,顶级的西湖龙井。有空给你送过一筒来。”
“多谢王局长。那么好的茶,放我这里也浪费了,还是留着你招待客人用吧!”
“哎,你这就分生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嘛”
“谢谢王局长。”任之良嘴里这么说,心里却说,哎哟,看人家领导说话多有水平呀,就这么点事,就难呀福的,同当同享,看人家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呀!他不经意间看一眼王一丹,心里说,呸,你肉麻不肉麻呀!
“在这里,我就算是新兵蛋子了,任主任是老人手了,又是大家公认的多面手,还望任主任多多支持帮助。”王一丹毫不掩饰地说。
“王局长说笑话,”任之良说,“如果哪些事做得不到,还望领导多多包涵,多加指教,我们尽量做好就是了。”
王一丹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容,喝了口茶,对任之良说了些关心体贴的话,任之良有一搭无一搭地应着。末了,王一丹说:
“我想换换办公室,我给局长谈了,局长让我找找你,你抽空给办一下吧。”
任之良说:“换没问题,不过,再没有那么大的、带套间的办公室了。你坚持要换,也只能和科室换了。这不委曲了领导?”
“你看是不是和白局长换换,我想他该想得通,我这个情况不是有点特殊嘛。”王一丹说。
这可就难了,任之良想,在班子里,最怕的就是厚此薄彼,同样是副局长,你凭什么换人家的办公室呢?任之良挠挠头,有点为难地说:
“我和白局长谈谈,看看人家本人的意见,再换好吗?”
“行,我想他会理解的。谁都知道,现在我用的是我老公用过的办公室,感情上总不是个滋味,白局长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我看问题不大。你说是不是呀?”王一丹加重了语气,任之良听得出来,她用的是商量的口吻,那意思却是不容你商量的。
他知道,骆垣虽然红过一阵子,但必竟是英年早逝,在官场上混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在他们看来,这个晦气鬼用过的办公室自然是有晦气的,你王一丹忌讳,难道别人就不忌讳?任之良想,看起来是件小事,无非是两间同样大小的房间在两个人之间做个调换,如果搁在老百性身上,是个最简单不过的等价交换,而在两个官僚之间,就有一个谁先提出来,满足谁的愿望的问题,这样,简单的一件事被赋予了政治涵义,事情就不好办了。因此,此事实际上并不小,连局长都不愿接手,把球踢过来,我怎么把人家的办公室换过来呢?他心里这么想着,嘴里还是应承了下来。王一丹说着感谢之类的话,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王一丹出去,任之良感到屋子里阴森森的,到处弥漫着一股淫荡和邪恶之气。他马上想到,在动物界,其个体就是用气味来辨别自己的同类,辨别同群落的成员和自己的亲属,辨别自己的朋友或敌人的。它们还用气味跟踪猎物,寻找走失的子女和回家的路。人类进化到当前,嗅觉的主要功能被大脑所替代,不再用气味来辨别敌我。但他想,某些退化了的器官的功能在特殊情况下会被强化,帮助大脑对所要认识的事物做出判断。比如鼻窦,在人类的早期,充满了气味受体,是早期人类用来辨别气味的重要器官。而现代人类,虽有这个器官,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能,退化为毫无用处的东西。如果有点用处,那就是在此时此刻,任之良的鼻窦的功能被唤醒,使他的嗅觉功能异常突显,帮助他认清给他办公室留下气味的这个东西,是他的同类还是异类,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
想到这里,任之良自己也笑了,不管同类还是异类,人家现在是自己的领导,是他的服务对象,她目前提出的问题是要给她换一间办公室,他得想办法满足她的这一要求。他先去白副局长那里,开门见山地说了他的来意,果然不出他所料,白吉福显然就不高兴了,说:
“这又不是她家,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换!”
任之良有点尴尬地笑笑,不知说什么好。
白吉福原想,徐树军一走,这个局长的位子非他莫属,没想到,眼看到手的肥肉不经意间落入他人之手,另外两名副的也调到其他单位当一把手了,只给他调了职级,被称作“正县级副局长” ,他正窝着一肚子的火呢,又来一个骚娘们挤兑他,他还哪来的好态度呢。
他见任之良站在他对面,十分尴尬的样子,觉得不妥,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说:
“你说任主任,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好像是她们家,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老公用过的屋子,她都嫌,难道别人就不嫌?”
任之良有点委曲,他说:“我也是例行公事,来你这儿把话说到。你不愿意,我给局长回个话,能交差就行。”
任之良觉得,自己该做的工作已经做了,双方意见告知局长,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于是,他去局长那儿。局长是从外面调进的,他对此人早有听闻,但了解不多。有人说过,到了一定职务的干部,细究起来都有过人之处,比如王一丹,开发自己的黄金口岸,利用自身资源方面就比一般女性高明得多。不知道这位局长有什么过人之处。
在官僚机关,领导班子内部的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一个部门二十来号人,大大小小十来个带“长”的,谁知道谁的背后是哪路神仙,综合起来,就是一张巨大的网,得罪了谁,就等于得罪了他背后的神仙。因此,谁能平衡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谁就是过得硬的班长。新来的局长姓高,名明胜,不知他在解决领导班子内部问题上,是不是高明?
任之良进去后,高明胜站起来,笑一笑,示意任之良坐。任之良坐下来,不经意间看一眼高明胜,此人个儿不高,圆脸盘,不大的一对眼睛,看上去平和而自然。任之良大体了解一点,这人从政之前是一位搞学问的人,曾专门研究过河西地区的历史和这一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出过几本这方面的专著,颇得学术间的赏识。
进入政界,他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据说他平易近人,作风扎实,经常深入农村发掘民间文化艺术,与农民兄弟拉家常,侃大山,乐此不疲。多年下来,交了不少农民朋友。让他出任负责救灾救济工作部门的首长,是不是就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种品格。因为,这个部门的工作对象大多是弱势群体,特别是灾民和生活特别困难的人,这就需要它的掌门人有一颗爱心,有一种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对人民群众无私的爱。
“有事呀?”高明胜坐下来,侧着身,面对着任之良,问。
任之良汇报了王一丹要求换办公室的事和他跟白吉福协调的情况。高明胜笑一笑说:
“这事,王局长刚来就找过我,说她不想在骆垣用过的屋子里呆,想和白局长换,我理解,睹物思人,也是人之常情。我原来想,她和白局长的屋子,结构、设施都一模一样,只是一个在四楼,一个在二楼,换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就让她去找找你,让你给协调一下,能换就换一下。现在谁也不让,你有什么高招?”
任之良摇摇头:“我能有什么高招?”停了一会儿,他说,“不行我给王局长说说,先就这么用着,以后再说。如何?”。
“你说呢?”高明胜笑笑,问。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这是一件小事,做做她的工作,打消那个顾虑,也就行了。现在人家既然提出来了,执意要换,你不换,就是个事情。她会把情绪带到工作中的。我想还是换一换吧。”
“可人家白局长不愿意呀!”任之良说。
“不一定非得和白局长换呀。”向明胜说。
“局里再没有这样的房间了,怎么换呀?”
“我搬到四楼去,让她搬我这里。”
“这……”任之良想说点什么,被高明胜的手势挡住了,他说:
“就这样吧,一件小事,何苦弄得那么复杂呢。省点精力,还是多想想工作上的事吧!”
就这样,任之良一件棘手的事,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任之良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三楼和四楼之间跑趟子,组织人员搬东西,刷墙壁,折腾就是一个多礼拜,总算把这事给摆平了。
两个空缺的职位,都由外面调来的人填补了,所以既没有空出科级职数,也没有空出副科级职数,科长们也好,科员们也罢,没有了奋斗的目标,也就没有战斗的必要了。大伙在那里发了一阵子牢骚,也就渐渐风平浪静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就又出事了。有一天,刚一上班,高明胜就把任之良叫到办公室,他一脸严肃,问任之良:
“王局长家出事了,你知道不?”
“不知道,什么事呀?”
“他儿子死了。”
“哦,”任之良一脸惊讶,他镇静了一会,心想,这完全是她家的私事,总不至于叫我为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写悼词什么的吧。他顺便问了一句,“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今天早晨的事,非正常死亡,公安上的都过去了,我们也过去看看吧。”高明胜一边收拾写字台上的文件一边说。
任之良和高明胜、白吉福一起赶往事发现场。现场就在王一丹的楼下。这里围满了人,死者身上盖着一条床单,附近有斑斑血迹。几个公安人员在测量现场,提取证据。骆家的人骂骂咧咧,一片混乱。王一丹听是高明胜来了,她流眼抺泪的,对高明胜他们说:
“也不知道是早上几点钟,屋里还黑着呢。我还没有起床,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开窗户,我衣服也没穿就走进孩子的卧室,隐隐看到他站在窗台上,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呢,我刚要叫,他就……”说到这里,王一丹已泣不成声,就像小孩子一样,伏到高明胜的肩上抽泣,“我也,我也吓懵了,披,披了件衣服下来,他就……,我一看,他,他手里拿着一把苍蝇拍子……你说这孩子,大早晨的,你打的什么苍蝇呀!”
高明胜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让任之良照顾她,自己和公安人员接了个头,公安人员说,基本可以肯定,人是摔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还得做进一步的调查。
该做的做完后,尸体被送往医院的太平间,王一丹被公安人员带去问话。任之良忙着安抚骆家的人。其中骆垣的弟弟骆老六最难安抚。这人人高马大,行为举止十分粗野。他大字识不了一箩筐,是骆垣为他买了个假文凭,又在市内的一家企业办了个招工手续,调到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此人没有文化,故干不了什么事,干点杂活,自己又不愿意,单位有什么福利,他又一分钱的亏不吃,为此,动不动就闹事。单位领导碍于骆垣的面子,又怕本人的那横劲,不能把他怎么样,也就放任自流,想干什么干什么得了。这样他便成了一个闲人,成天在社会上惹事生非,干一些蝇营狗苟之事,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看守所里进进出出过好几次,在社会上还小有一些名气。
公安人员要带王一丹去问话,他硬要跟着去。他说:“我就不信是打苍蝇去了摔下楼来的,肯定是这个骚货害死的。我哥就是不明不白死的,我们没有找她的啰嗦就便宜她了,她又害死了我们的侄子,这会是说啥都不能放过她了。”
公安人员说:“这事得一个一个来,我们先问你嫂子,你先在这儿等着,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再找你。好吗?”
任之良也说:“你看,家里来了这么多人,我又不太熟悉,你还是和我一起,先照料着让家乡来的人住下来,其他事情,慢慢再来,你说呢?”
骆老六哼哼叽叽地说了几句粗话,也就不再坚持跟着公安人员去了。
任之良在附近的旅馆里开了几间房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骆家的人安顿下来,就紧跟着骆老六,生怕这人到什么地方去闹事,再惹出其他麻烦事来。骆老六骂骂咧咧的,非要找王一丹算账。任之良尽说些好话,跟着人家的屁股转,总算没有闹出什么事来。任之良想,别人家的事,自己给一个混混陪笑脸。你说这是什么事呀!
除了王一丹的打苍蝇说,再也找不出别的说法来。尸检发现大头得有深度梅毒,下身已经开始溃烂,警方怀疑他的死是否与此有关,但对王一丹家里的侦察结果看,大头死前一两天内,王一丹家中确实没有什么异常,也找不到王一丹加害的任何证据。那么这个花季少年真的是为打一个苍蝇,不慎从自家的窗户摔下来毙命的吗?
那天,大头在睡觉前洗完下身,王一丹跟到他的卧室,要看看他的病情,他怎么也不让她看,王一丹就骂开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嫖了一辈子,嫖死了。你看看你养的这宝贝儿子,这都成什么样了,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大头也不是省油的灯,反唇相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男盗女娼,你认为我不知道呀。为了那个破局长,你们什么事没有干过。这会儿在我面里耍威风,还要不要脸?”
“你怎么说话呢,啊!我们干什么了?就是干了什么,还不是为你!你这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说出来,我们男盗女娼,我们怎么好好的,这病怎么就偏偏让你给得上了,啊!没话了?你说呀。”
大头气不打一处来,他几乎咆哮起来:“就算我不对,你们管过我吗?我得了这病,是脏病不错,你们给我买的这是什么药,吃这么长时间根本就不管用。这能怪我吗?”
“我能怎么办?啊!噢,闹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王一丹养了个好儿子,年纪轻轻的就知道嫖娼了,我光荣啊我?”
“你就知道我、我、我的,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你们一个大撒手,把我撂给亲戚养,就像没爹没娘的孩子。这会子出了事,所有的不是都成我的了,你们对得起谁呀!”
王一丹一时语塞,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就流了下来,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她说:
“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你也有责任,你就不该跟上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跑。这会有病了,咱们看病。这个双休日,你就去医院看,好吗?”
大头沉默了一阵子,说:“还是你带我去看吧。”
“这不行。”
“那我也不去。”
“乖儿子,你听我说,你呢,谁都不认识,就是一个病人,和所有的病人一样,去看你的病得了。我就不一样了,认识的人多,万一传出去,我不要紧的,传到你们学校里,你可怎么呆下去呀!”
“就是那样也比我一个人去的好。”
“你怎么这么犟呢,啊!真是气死我了。”
母子俩红脸黑脸的说了一阵子,王一丹去睡觉了。大头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爬起来,轻轻地地了床,悄无声息地关上门,回到写字台前,悄悄地打开电脑,上了网,搜索出医药网上关于性病的网站,一页一页往下看。
自他得了这种病,他曾无数次浏览过这类网站,反复看过有关这种病的症状、发展过程和可能出现的结局。他留意过贴在街头巷尾“根治性病”的广告,一想起那些广告上耸人听闻的言辞来,他就不寒而栗。今天,他看了一些有关这类病描述性的文字,又看了一些图片,再看看自己的下身,他觉得他的病已经很重了,他认为已经不可救药了。他越看越怕,心里一阵恐慌。胆颤心惊地关了电脑,上床躺下来。
不知躺了多久,他有点迷糊了。不一会进入了梦乡。他在梦中看见了自己,他见自己赤条条地躺在大马路上,有不少人围了上来,对他指指点点。他从人群中挤进去,看见自己一丝不挂,生殖器官已经完全腐烂,爬满了白色的蛆。浑身上下,被红红的斑点覆盖着,面目全非。人们看一眼,就都捂着鼻子走开了。大头看着自己,心口也堵得荒,连气都喘不上来。他企图长长地伸伸腰,好让自己喘口气,但怎么也伸不出自己的胳膊。他有点急了,就使劲蹬腿,这一蹬,他醒了,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满头大汗。他从床上坐起来,急促地喘着气。那个可怕的梦总是萦绕在他的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口渴得十分厉害,想倒杯水喝。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又犹豫了,他怕惊醒王一丹,此时他谁都不愿意见。他又回到电脑前,坐到椅子上,眼睛呆呆地看着台灯,台灯发出轻轻的嗡嗡声,在静静的夜里,显得那么恐怖。
他想遵从王一丹的意思去看病,但他一想到大夫和别人那鄙视的目光,想到以后同学们对他退避三舍的情形,他又打退堂鼓了。怎么办呢?梦中的情形历历在目,如果到了那个份上,还不如一死了之。对,死也是一个选择呀,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何必受这份熬煎呢!
怎么死呢?他悄悄地下了床,打开写字台的抽屉,那里有他经常吃的药,他把所有的药瓶打开,想把它都吃下去。就在他吃下去的那一瞬间,他想到卧室里没有水,他又怕到客厅里去倒。他看着手中的药,问自己,这些药毕竟不是毒药,这样吃下去,能药死吗?万一药不死,岂不是又要惹人耻笑。他犹豫了好一阵子,觉得还是另找出路为好。这时他看到了墙上的电源插座,他想起了他曾经被电打过的经历,想找一根电线,把自己电死,找了半天也没有电线的踪影,他又忧郁了,就是找到电线,如果自己在半道上后悔了,手一放松,岂不是功亏一篑。
他非常沮丧,重又上床躺下来,不禁又一阵胸闷气短,十分难受。他坐起来,感到自己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就这样折腾了一 夜,他把目光投向窗口,窗口显出微光,他看看表,天快亮了,如果再找不到死亡的途径,今天就死不成了。他看着窗户,心里有了主意,从那里跳下去,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轻轻地开了一扇窗户,向后看了一眼,慢慢地爬上了窗台。他在窗台上犹豫了一会,听到了邻居家开窗户的声音,他知道,早起的人家已经起床了,这时不跳,还等何时?他心一横,闭了眼,身子向后一倾,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人世界的一切烦恼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了。
王一丹苦思冥想,实在想不起是哪里出了差错,老天对她竟然如此不公。好好的,丈夫不明不白地死了,不久儿子又死于非命,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哪路神仙?她想找马半仙问个究竟,又一想,骆垣不是对马半仙言听计从吗?从改造祖坟到装修房屋,哪一件不是依马半仙的神谕仙旨进行的?到头来,非但没有飞黄腾达,竟然遭遇飞来横祸,弄得自己家破人亡。看来这神仙也有走眼的时候,或者压根就不是什么神仙,装神弄鬼而已。
对大头死亡的社会舆论,王一丹自始至终坚持打苍蝇摔死一说。社会舆论却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飞长流短,不时地灌进王一丹的耳朵里。其中有一说,说是大头越长越像某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又面临着升迁的压力,他的竞争者正在拿他的作风问题给他做文章呢。于是在其授意下,由王一丹设计害死了他们的儿子。
真正的死因,除了王一丹之外,没有人能说得准。她后悔过,后悔没有给儿子早点治病,后悔没有在当天晚上答应儿子要她陪他去看病的要求。别人的议论像刀子一样扎在她的心上。她想,人类普遍的看法是虎毒不食子,其实,护仔行为在动物界普遍存在,否则,这个物种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了,何况她是人,她怎么能害死自己的儿子呢。大头不是自己丈夫的孩子,但千真万确是自己生下来的,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怎么能够加害于他呢?别人如此猜测,可见把她看成连自己的儿子都敢害死的毒妇人了。人言可畏,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一想到这些,她就浑身发抖,直冒冷汗。
她不敢到人群中去,一到人群中,她就感到有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她,就像千万束箭头射向她的脊梁骨,使得她毛骨悚然。她上班也不到别人的办公室去,生怕别人指指点点,小瞧了自己。自己没有看书看报的习惯,也不会玩电脑,没有多少工作,就是有,也没有哪样工作是自己会做的,别人也不会让她做什么事的。剩下的一件事,那就是陷进无休无止的胡思乱想和不堪忍受的懊恼之中,上班实际上成了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
出了这事以后,甄恪以及和她同床共枕过的男人们,没有给她打过一个电话,没有过只言片语的安慰给她。她想不通,这些人在和她进行性交换时,是那样的狂热,那样的甜言蜜语,在那个时候,她就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可如今,她简直成了温神,见着她躲她都唯恐不及,不要说重温旧日的美梦了。她想到这里,就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把天下的男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方解她心头之恨。
这时,有人敲她的门,她赶忙拿过一份文件和一支铅笔装作批阅文件的样子,然后喊了一声“进”。
进来的是任之良,手里拿着一些发票,递过去,对她说:
“这是孩子的事情上,亲友们花下的,你过过目。”
王一丹睁大眼睛看着任之良半天,才低头看那一堆发票。看了一会,都是骆家的人在大头发丧期间的住宿费、餐费、饮料费,还有水酒费,一共好几千块。她伸长脖子问任之良:
“你的意思是……”
“这笔费用单位没有地方开支,你看……”
“任主任,这我不管。我承认,这些是在处理我孩子的后事期间骆家的人花的。可他们要来,又不是我请他们来的,来了又没有节制地花。你看看,我家出那么大的事,他们还花天酒地,这费用我能处理么?”
“当时骆老六那么横,不由着他,他就要闹事,谁都管不了他。这人你是了解的,我也实在是为难。”
“还是那句话,我不管!” 说着,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看我都这样了,都落井下石,够人的来欺负,不够人的也来欺负,我还怎么活呀!”
任之良听着不对劲,什么是够人的,什么是不够人的,当时骆老六煽动骆家的人要闹事,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这会子怎成了欺负人了?他叹口气,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再说,这么大的一笔开支,单位不好处理,自己又垫不起,真是难死人了。他站了一会儿,说:
“不行你先放下,过后我们再商量好不?”
“没有什么商量的,我不管。”
“这就有点为难我了。”
“这有什么为难的,谁花下的,找谁去要。骆老六他不是有工资吗?跟他们领导说说,从工资里扣。”她一边说,一边抽泣,一副委曲的样子。
“好吧,我试试吧。不过,骆老六那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天王老子都管不了,谁敢扣他的工资。”
“他还没有王法了?”她说着从旁边的抽屉里撕了一片卫生纸,擤了一把鼻涕,不满地瞪了任之良一眼。任之良感到再没有说下去的必要了,也就再没有说什么,转身出了王一丹的办公室。
任之良出去后,王一丹越想越气。相当年,她是何等风光,有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又有多少人把望着上她的“黑名单”,走进她的网,得到她的一点残羹剩餐,像任之良这一级的干部,她连看都不屑于看一眼的。可如今,墙倒众人推,世态炎凉呀!
王一丹怀着这样的心态,艰难地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她回到家里,冷冷清清的,也不想吃饭,倒在沙发上就睡,脑子里一塌糊涂,怎么睡也睡不着。她有气无力的爬起来,找了几片安眠片,从热水器里接了一杯凉水,一仰脖子喝下去,重又躺下来,不一会就入睡了。
她在迷惘中看见骆垣向她走来,他笑眯眯的,握往她的手,她想起自己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眼泪就一下子流下来了。她伏在他的肩头,心中有说不完的话要向他说,可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扑过去搂住骆垣的脖子,感觉它硬梆梆的,好不冰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具骷髅,向着她呲牙咧嘴,顿时,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她的四周。她放开他,惊恐地望着他,想大声呼喊,却又喊不出来。她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双手蒙往眼睛,眼泪夺眶而出。当她再睁开眼,那骷髅像一阵轻风,随风飘散。
她看看周围,想辨出方向,好找到回家的路。但她没有见过这是什么地方,云遮雾罩的,看不到多远。她站起身,艰难地走了几步,碰见了大头。大头浑身是血,两眼血红血红的,她怕极了,转身想走开。不想大头在她的前面拦住了她的去路。大头面目狰狞,一副恶相。他拿出一条绳子,就要往王一丹的脖子上搭,王一丹惊恐地向后退,不想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她一个趔趄向后倒去。她赶忙翻起身来,发现地上遍地是骷髅,发着蓝色的光,使她心惊肉跳。
她想逃出这片恐怖之地,一时之间,她的周围出现了许多人,她仔细看看,都是和她有染的那些男人们,这下,她可有救了。她打起精神,向他们招手,可他们个个煞气腾腾,不怀好意地向她逼来。她感到绝望了,憋足了劲大声叫喊,就这样被自己喊醒了。
她大汗淋漓,沙发扶手上淌下了一滩眼泪。此时天完全黑了下来,她害怕极了。她慌慌忙忙地打开所有的灯,屋子里灯火通明,但王一丹的心里却一片黑暗,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她打开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枪战片,镜头中枪声大作,一派恐怖景象。她惊慌失措,在换频道时按下了电源开关,电视画面刺溜的一声消失了。心想这电视怎么突然停了?真是活见鬼了。心里越发害怕。她狠狠地按下电源开关,并换了一个频道,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恐龙,张着巨大的血盆大口,好像要吞了她似的。她并不知道这是电脑制作的,也不懂得恐龙在六千七百万年以前就灭绝了或进化成为鸟类。而她对她生活领域之外的东西又知之甚少,以假乱真的电视制作效果,使她误以为这是存在于现时的一种庞然大物,只是平时没有看到过、听到过罢了。她想,这世界真是变了,连这样的怪物都出来了,并在大众传谋上亮相了。
王一丹连连换了几个频道,都不是她想要的。她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浑身也感到不自在起来,就像千万只蚂蚁在啃食她的骨头,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她在沙发上翻来覆去,挥之不去的恐惧笼罩在她的心头,她揪住自己的头发,发出了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第二天上班,不见王副局长,高明胜让任之良打了几次电话,不见接听。高明胜想起最近他的这位副手的所作所为,自言自语道:
“她能有什么事呢?就是有事,也应该打声招呼呀。”
“叫小黄去看一下吧?”任之良说。
“这样吧,你手头没有要紧的事,你去一趟。”
“好吧。”
任之良说着就往外走。他到王一丹的门口,敲了半天门,没有反应。一种不祥的感觉堵在他的胸口。他给高明胜汇报了这里的情况,高明胜想到她儿子的事,无论如何得找到她。于是他请求消防队的支持,不一会消防队来了一辆消防车,一名消防队员爬上她家的楼层,从窗户上看进去,王一丹在屋里,这位消防队员向任之良打了一个手势,告诉他室内有人,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任之良作了一个让他进去的手势,那消防队员敲碎一块玻璃,破窗而入,迅速地打开了门。
任之良进去,只见王一丹斜躺在沙发上,蓬头垢面,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任之良,任之良凑过去和她说话,她满脸惊恐,慌忙往后躲避任之良。任之良心想,不妙,这个女人疯了。他定了定神,轻轻地对王一丹说:
“王局长别怕,我是任之良。”
王一丹越发害怕的样子,她嘴里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从沙发上站起来,呆呆地发了一会呆,就大声大气地叫起来,并拿起手边的东西向任之良砸去,任之良示意那名消防队员控制住她,那消防队员上前从后面抱住了她,她疯狂地咬消防队员。任之良给高明胜打了个电话,说明了王一丹的情况。
局里派车把王一丹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她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得已,只好把她送进外地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任之良想,这个曾经在这座城市里很有名气的风流女人,如今家破人亡,连自个儿是谁都认不出来了。她有可能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她的余生,可惜的是,老百姓将为她支付后半生的工资和高昂的医疗费用,直到她的肌体死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