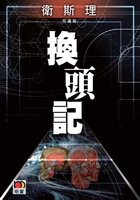任之良把小羊还给了它原来的主人,就是上次他们落实边界纠纷协议时,特别会说话的那位中年男子。
他对任之良特别热情,他往“三叉”里添了些牛粪,架起火皮袋,一边吹火,一边跟任之良聊天。不一会儿,水开了,他给任之良冲了一碗酥油奶茶,整个帐篷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醇香气和怪怪的烟味,任之良突然想到“人间烟火”四个字。他想,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烟火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到如今,离开烟火也能取暖,也能做熟食物,故而,不知这烟火在人类的生活中还能燃烧多久?
中年男人站起身,瞅一眼挂在帐篷中间顶梁柱上的羊皮袋子,他走过去,从羊皮袋子里取出一把小刀,又从帐篷的一角摸出一块磨刀石来。任之良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于是说:
“不要瞎忙乎了。要是吃羊,我早把这个小羊给吃了,还跑这么远给你送来呀!”
“我知道,你这是闹着玩个新奇,”那中个男人说,“哪里真的为了一个小羊羔,让你跑这么多的路,受这么多的苦呀!”
任之良笑笑,心想,是呀,你说你救了一只受了伤的小羊,大老远的从山里带到城里,托人养这么大,再从大老远的城里送到山里,说给谁谁信?可他确实这么做了,这会,那只被他救活的小羊就在帐篷的附近吃草。而这位牧人却说他这是玩新鲜,也许有点道理,也许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他也说不上来。他说:
“你真聪明。就算是吧,但我也不忍心吃你的羊。”
“羊养下就是让人吃的,你不吃,那我们就该喝西北风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他看着中年人,仍旧笑笑,说:“你还是留着卖吧!”
“你是怕我招待不起你呀。”中年男人叹口气,“说实话吧,我也馋了,好长时间没有动荤腥了。要是不来人,我还真舍不得杀个羊呢,你来了,是我跟着你沾点光,动动荤腥解解馋。你就这么不给这个面子呀?”
“吃你的羊,我给你面子?”任之良笑着说,“你可真有意思。”
“我说的是真话。”
“我知道是真话。”
“那你还推托个啥呢。”
“我说的也是实话,真的。”任之良说着,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小刀,套上刀鞘,放入皮袋里,“我们聊聊天,拉拉家常,比什么都强。你还是过来坐,我们聊聊天吧!”
中年男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过来坐在任之良的对面,给他添了点奶茶,说:“你这人真怪。”
“真不好意思,这都第二次见面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
中年男人笑笑:“我姓杨,弟兄们都喊我四哥,你叫我杨老四就行。”
“好,那我也叫你四哥好了。”
“你怎么叫着顺口,就怎么叫。反正都一样。”
任之良笑着说:“你的羊都有名字的,比如‘黑脸脸’、‘黄眼眼’、‘白鼻梁’什么的。何况你呢,能没有名字?你是不愿意告诉我罢了。”
杨老四欠欠身子,笑眯眯地说:“嘿,你也知道这个?”
“老杨哥,我也是农村里长大的,小时候也放过羊,我的老家就在这山下面的马莲沟呀,我怎么能不知道这个。”
“哦,是本地人呀!”
“你以为我多‘洋’呢!”
他们就这样闲扯了一会,任之良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传闻佚事,说:
“我小时候老听老人们说,这里的狼很多,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有是有,不过比过去少多了。”
“哦——,对羊群没有什么威胁吧?”
“我放了几十年的羊,没有遇见过。我听老人们说,狼这东西,人不惹它,它不会伤人的。”
任之良说:“可能是吧,狼是一种很智慧的生物,长期以来,能够始终与人和平相处,这可能就是它的生存之道吧。”
“要是你惹了它,它会对你不客气的。”杨老四顿了顿,“六零年那当儿,人饿极了,就进山打野兽吃。听老人们说,那时候,成百上千的人进山围猎,人们叫喊着,敲着盆盆罐罐,拿着棍棒,从四面八方往一起围,赶围到一起,呱呱,什么黄羊呀,青羊呀,狼呀,狐狸呀,兔子呀,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这样围剿一次,能拉几十车。我们的命就是这些野兽的肉给救下的。”
任之良点着头,说:“这事我也听说过。”
“从那以后,狼反了。”他话匣子一打开,讲了很多关于狼与人为争夺这片草原发生的血腥故事。
任之良和杨老四聊天聊到很晚才睡。第二天起床已日上三竿。杨老四赶着羊群去放羊。任之良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喝了一碗奶茶,便出了帐篷。这里的空气特别新鲜,他深深地吸口气,顿觉精神百倍。他信步向前走了一段路,来到与邻县的分界线,那段又被重新修好的铁丝网,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下,闪着点点青光。他在这里驻足,放眼望去,远处山峦叠嶂,天山相连,白云悠悠。辽阔的草原上,隐约可见成群的羊群、牛群和马群。阵阵微风,吹来草原的清香。
任之良不觉越过铁丝网,走向草原深处。他在碧绿的草丛中,又看到了他熟悉的马莲花,这是一种极普通的花,叶子长长的窄窄的,墨绿墨绿的,虽不怎么起眼,但在他的记忆中却是那么难以忘却。他记得,在他小的时候,手脚灵巧的妇女和孩子,一根一根拔下来,拿它编织成各式各样的玩艺儿。那个时候,编织马莲织物成为他童年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至今还记忆犹新。马莲花儿蓝里透白,有股淡淡的清香。在此后的岁月里,任之良见过、养过不少的花,但对马莲花却情有独钟。
眼前,成片成片的马莲花,点缀着这块草原,也点缀着任之良的情思。他走了一段,坐在一片马莲丛中,点了一支烟,慢慢地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来,青烟在微风中慢慢地飘散,消失在清新的空气中,任之良感觉不妥,他在自己的鞋底上蹭灭烟,放回到烟盒里。他下面是湿漉漉的草地,软软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
他索性躺下身子,望着蓝蓝的天空,思绪万千。上面是蓝天,蓝天是什么?是空气中的微粒折射了太阳的蓝光。因此,空气和阳光,在哺育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创造了美的景色,真应该谢谢苍天!
蓝天之外是什么?他想,是无数的天体和弥漫在天体之间的宇宙粒子,就是因为有了蓝天,阻挡了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粒子和各种各样的射线,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命才得以生存和繁衍,我们这颗蔚蓝色的星球才如此生机勃勃。
星体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不知道。科学先驱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由无穷小的超弦子构成的,于是形成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不同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时存在,其内部的折叠和弯曲形成不同空间之间的捷径,但我们目前还浑然不觉,还无法寻找和利用这些捷径来往于各空间之间。
他想,如果某个时刻,人类找到了不同空间之间形成的“虫洞”,摆脱了碳水化合物的束缚,自由地驰骋在广袤的宇宙,在各星系之间自由地穿梭,人类才算真正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任之良胡思乱想了一阵,感到身子下面有点潮,他翻起身,远远望见了散布在草原上的羊群、牛群和马群,不禁想起杨老四讲的人与狼大战的情景。
自从围猎以后,草原上的狼总是伺机对人和人豢养的家畜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对人类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不时有人和畜被狼咬伤或咬死,有时几十甚至几百只狼组成的狼群,把整群整群的羊或马从草场上掳走,然后咬个一塌糊涂。以牧为生的牧民的生存受到狼群的严重威胁。
据杨老四讲,有一天,他那个村子里有一个从旧军队里复员回家的老兵,此人在下山的路上碰到一个狼窝,从狼窝里掏出两只狼崽子,带回去养在家中。当天夜里,几十只狼把他的家院围了个水泄不通,等闻讯赶来的村民搭救,此人全家已被狼咬死,狼群已成功救出自己的孩子,凯旋而归了。村民们发现,这家人的院墙和屋顶被狼挖了好几个洞,狼是从这些洞中悄悄地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了它的敌人,救出了它的孩子。这说明狼是一种高智慧的生物,在与人的战争中,十分讲究战略战术。
人当然是不会任狼宰割的,人们用现代热兵器武装起来,向狼发起了反击。根据杨老四的述说,在狼与人的战争中,狼群中有着高度发达的作战指挥系统、灵敏的通讯联络系统和完善的团队编制体系,在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狼们运用了运动战、游击战、伏击战、山地战、麻雀战等各种战略战术,表现出英勇善战的品格和宁死不屈、顾强战斗的精神,把万物之灵的人们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这里的人们负出了惨重的代价,对狼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才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任之良想到这里,叹了一口气。他想,现在我们知道,狼也和我们一样,它们的灵魂中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凶残的一面。它们有它们的家庭、社会组织和领土主权,有爱也有恨,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这里原本就是它们的王国,它们在自己的领土上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它们遵循着自然法则,与各个物种友好相处。是人首先向狼发难,在这和平安宁的草原上引发了两个高级物种之间的战争。显然,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就和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一样,战争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没有什么悬念的。那就是狼类遭到人们毁灭性的打击,它们在付出成千条生命的代价之后,悲壮地退出了这片土地,成为亡国奴,流浪在外。在这片草原上,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不到狼的影子。
后来发现,人们在这场战争中,在遭到狼们沉重打击的同时,还遭到自然母亲的打击,在此后的岁月里,这里的生态平衡被人为打破,两千多平方公里的草原成了老鼠、野兔和旱獭等草食动物的天堂,大片大片的草场被这些动物的洞穴占据,原本繁茂的花草被连根吃掉,裸露的土地受到风蚀水浸,昔日生机昂然的大草原变成一片死寂。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才恢复到今天的模样,但过去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再也不会再现了。
良久,任之良站起身,背着手,漫不经心地往前走去。初秋的草原上,阵阵秋风吹过,有那么一丝凉意。他的脚步不时地惊起草丛中的蚂蚱、蜜蜂、蝴蝶和不知名的昆虫。他不禁打了个寒颤,抖了抖身子,一丝悲情掠过心头。他想,他是这片草原上的不速之客,而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在不远处,他看见了这里的另一类主人——旱獭,它们发现他时,直立起来,机敏地转动着小脑袋,东张西望一阵后,迅速地淹没到花草丛中。
像这样的小生灵,在这片蓝天下不知还有多少。还有寄生在这花草上、旱獭上和各种各样的昆虫上的各类微生物,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在这个生物群落中,各生物物种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是交换,是战争,还是同生共死?人类对此的认识微乎其微,但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们在为生存而战,在生存斗争中,在不断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以更好地适应环境,把自己的基因永恒地传播下去。
远处传来牛的吼叫和马的嘶鸣,隐约听到牧人高亢的小曲。你把这样的生活场景浓缩到一张白纸上,我们就可以见到史前人类的生活轨迹了,拿人类的文明史去衡量,是在非常遥远的过去,但拿人类的进化史相比,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是谁主宰着生物的命运,操着生物的生杀大权,让一个物种生息繁衍,而让另一物种灭绝?这一切是必然的,还是偶然事件造成的?人类站在生物进化的顶端,能不能够说,人类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左右自然演化的历史,更不能创造自然演化的历史。我们的命运仍然操在自然母亲的手中,生活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摇篮中,母亲小小的失误,就会让我们永远地在这个摇篮中消失,或变成其他什么东西也未可知。走出这个摇篮,还需借助母亲的力量,让我们吃着母亲的乳汁健康地成长,直至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形态的时候,我们再向母亲说一声再见。
不知不觉中,任之良走进了森林,一股湿润的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生长着茂密的乔木,苍松翠柏,清爽宜人。林间铺满了厚厚的一层松柏针叶,脚踏上去软绵绵的,十分熨贴。任之良走了一段路,坐在一块石头上,贪婪地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他突然想到,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的对面出现一只狼,它会怎么样呢?它向他扑过来,咬断他的喉咙,一口一口地把他吃掉,还是它睁着惊恐的眼睛,怪异地望着他,友好地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平静地离去?
他读过不少地方志,了解这块土地的历史。在这片古老的森林里,曾经生活过原始人类,如今,他面对他的远祖曾经的家园,眼前浮现出一幅幅活灵活现的远古人们的生活画卷。那时的人们靠采集和狩猎摄取营养,如今的人们靠种植和养殖摄取营养,这种摄取从本质上讲,没有丝毫的区别,都是通过劳动,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维持自己的生命,养活自己的后代。区别仅仅是手段不同,使用的工具不同,摄取的方式不同。而就是这微小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数十万年的光阴。从人类饲养第一只家畜,播种第一块土地到如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如何发明和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个轴转动。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轴,从人类自身的改造上动过脑筋,做过尝试。如果现在开始,我们做这样的尝试,到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不知还要走多长的路?
一阵风吹来,任之良打了个激凌。他站起身,往前走了一会就回头了,他不敢再往前走,他怕迷失方向。他想象着,如果他迷失在这片森林里,他将怎样生存下去,直至找到走出森林的路,重新回到牧人的帐篷。那太可怕了,他不敢再想下去。
任之良回到帐篷,杨老四正等他吃饭呢。饭后,任之良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到黄昏时分。此后几天,他每天都到草原深处走一走,转一转。脑袋里想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晚上回来再和杨老四聊上半宿,心情十分畅快。杨老四也乐意交这样的朋友,他成天和牲畜打交道,难得有人和他聊天,并且还是一位健谈的人,一位诚实的人,一位在他看来无所不知的人。
就这样,任之良在这里一呆就是几天。公休假还有几天,他想应该去看看母亲了。
他辞别杨老四,徒步下山,回到了马莲沟。
地震发生后,在外界的援助下,这里的人们住上了新房,而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和生活水平,与二十年前似乎没有什么两样。母亲也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干燥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那是沉重的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烙印,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她的活力正在一步步地消失。
她看见儿子,开心地笑了。坐下来后,任之良说:
“你好着呢吧?”
“没病没灾的,有啥不好的。只要你们当儿女的好着,我也就好着呢。”母亲笑呵呵地说。
任之良笑笑:“时间长了也没来看你,你不怪我吧?”
“你把你的事往好里干,妈老了,打发一天算一天,你呢,就不要老怗记着妈了。”
任之良心头一热,眼圈有点湿润。他知道,妈尽管大字不识一个,但妈心中有一杆秤,抱着一个古老的祖训,那就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子能为公家做事,这就是她精神生活的全部。任之良在母亲面前感到十分惭愧,他清楚,母亲一直以为儿子在外面做什么大事,在为国家效力呢。而事实上呢,他成天都干了些什么呢?和他一样的、坐享其成的、靠税收养活的人们又在做些什么呢?母亲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国”字,而我们中的有些人,早已把这个字抛到了脑后,除了追名逐利,再也没有使他们感兴趣的事了。
母亲问他,想吃点什么,妈给你做去。任之良说,不必了,随便点吧。他问起了侄子欣亮的学习,母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她说:
“这娃,跟你小时候一样,又聪明,又用功。”
任之良说:“用功就好,你也不用太宠着他,把他给惯坏了。”
母亲嘿嘿嘿地笑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不一会,她的笑容渐渐地消失了,声调有点低沉地说:
“你们兄弟俩,就这一个男娃,兄弟走得早,你又在外边,我不心疼再谁心疼他呀!”
“妈妈也是,这事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放在心上呀。”任之良知道,在母亲的心中,除了弟弟的死,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隐隐做疼的一块心病,那就是自己没有男娃。从宗法制的意义上讲,自己将身后无人,这是人之为人最大的遗憾。母亲自然懂得欣星是儿子的骨肉,当然也是自己的骨肉。毫无疑问,不论是欣星还是欣亮,带的都是她老人家播撒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欣星和欣亮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任之良想,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人们总是循着男性的血脉寻找自己的根,女性被排斥在宗族之外,没有儿子,就在该宗族中断了血脉。因此,在母亲的眼里,欣亮是任家的根苗,而欣星生来就是别人家的人。只不过不忍心在任之良的面里说出来罢了。想到这里,任之良心中多少有点不快。他脱鞋上了炕,顺势半躺在靠墙的铺盖卷上,一副疲惫不甚的样子。母亲问他:
“你该好着呢吧,怎么又瘦又黑的?”
任之良随口应付了几句,便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一觉醒来,母亲的饭好了,欣亮也放学回家了。吃过饭,任之良感到精神了许多。他翻着欣亮的作业本,问了欣亮几个问题,便半开玩笑地说:
“你奶奶说你又聪明,又用功,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正确?”
欣亮有点委屈地搓着头,咕哝道:“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嘛!”
任之良正要说几句老师的不是,他想了想,还是忍住了没说。这能怪教师吗?不能。任之良知道,像马莲沟这样的小山村,本来就出不了几个有文化的,在山外受过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外面的,有谁会来这里,受这份苦,遭这份罪呀!因此,像这样的山村小学,任教的,大多是本村念过几天书的小青年,你能指望他教出什么水平呢!欣亮跟欣星所享受的教育资源,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任之良轻轻地叹口气,对母亲说:
“老妈呀,我早说过,你带欣亮和我一块儿过算了,你就是不肯,我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看,眼看着你一天天老了,伺候不动欣亮了,再说,你得让欣亮接受良好的教育呀!“
母亲说:“良子呀,我也没啥想法,是你们的那日子我过不惯呀。再说了,良子,你不要怪妈说话直,你挣着多少,妈知道,城里头花销大,我和亮亮去,你的日子过不到人前头呀!”
“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呀,妈妈。你都多大年纪了,该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义务的时候了。”
“我还动得动,等我动不得了,你咋折腾都行。”
“可欣亮的学习耽误不起呀。”
“我就不信这个 ,你不也是在这里上的学,还不是考上大学了?”
“这都老皇历了,现在跟我那时候不能比了呀。”
母亲一时无语,从她的表情看,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会带着孙子进城的。良久,她又问起了欣星:
“那丫头肯长,又长高了吧?早晨起早点,给娃打两个荷包蛋,娃娃正是长个子的时候,不要亏了。”
任之良说:“你啥时候操个够呀我的老娘!”
母亲笑笑:“娃娃,啥时候咽不下这口气,啥时候都得操呀,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任之良望着年迈的母亲,眼睛又一次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