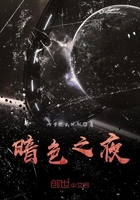母亲能跟儿子算账吗?母亲就没有委屈吗?诚然,在工房子用女工推大磨淘金的时代,抱着一根磨棍扭动唱歌,石粉浆漫流,比较方便,花大姐没有使自己受委屈,度过了金子一样的好年华,大工小工和老板,碰到手上的一个都不放过,兼及其他。可是后来呢?嫁给了当兵没打过仗的人,常常咳嗽,幸亏有镶牙的牙医拾漏补缺,给她镶一颗金牙吃东西,她总算没有饿着肚子,还顾得上挑肥拣瘦,嫌包大万那样的身子太短,脸长得不好看。可是再后来呢?咳嗽了大半辈子的男人在牌坊那里被车撞死,巧遇许言明,老中医也只剩下嘴上的功夫了,送药的能力差不多耗尽了,真的像大表姐说的那样是个“联想的鸡子”了,她还敢指望“赶集”和“进城”吗?她本是好人家的女人,生就了****的身子,容貌不算上乘,天赋过人。老天爷并没有规定,好东西都是给漂亮女人吃的嘛,说到家,女人吃东西并不是用脸嘛。可是她脸上的皱纹一多,连包大万那种她过去看不上的,都不肯要她了,要横眉冷眼地问她能干什么了,要把她交给一只德国公狗了,她只配给人强奸了,强奸时连草厚一些的地方都不找,把她当成一只皮肉硌不疼的老母狗了。那个人爬起来就能骑上车子跑,在车子上直直地站着蹬,爬大坡,不说“得歇歇”,真是个好样的。男人女人都要趁个年轻的时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年轻嘛,吃得好嘛,牙口好胃口就好嘛,想吃就吃嘛。儿子啊儿子,娘的眼泪似水淌,只能让它往肚里流。母亲最高贵的品质,就是不向儿子倒苦水,她只能给儿子交待事实:就是没有钱。昂子不相信,说一句不用透明胶布封嘴的疯子才敢说的话,吓死人了:
“你都小康了,还没有钱给我逛窑子?”
花大姐倒不给他把嘴封上,只让他看清现实,说:“卫生城验收了,我上哪儿挣钱给你嫖?”
不发疯的儿子矫情的时候,张狂的时候,鬼祟的时候,做了坏事的时候,会对母亲撒谎,母亲发了疯,也会对儿子说实话。就是这样,国家验收团从小学生列队持花挥动的路口通过,离开了三河,小学生扔掉一端钉了铁钉的木棍,花大姐就从扫大街的岗位上下岗了。她没有能力,留住验收团多住些日子,她也没有权力,让卫生城验收不合格,从头收拾。老天爷呀,儿子正在发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女工正在失业,为什么不建一个卫生城,永远验收不合格,让人有活干呢?卫生城如果非要验收合格才行,建一个卫生妓院,让母亲去打扫也好嘛。母亲的工资挂在账上,打一个白条,空里来空里去,转给儿子,也免得儿子玩得发了疯,让****掏空了兜。花大姐心事重重,把满腹哀怨朝着许言明发泄。她忘记了儿子好了病,她曾经发动起暮年的老激情,感谢过老情人了。她埋怨许言明开错了处方,用错了药。老中医行医大半生,有给人送药的经验,他送过一回还想送,就应该明白,用“想吃就吃”的办法,可以治饿肚子的病,可是不能治疯病;饿肚子,吃饱了就不想吃了,然而疯病不行,一种疯病,用想吃的东西治好了,另一种疯狂紧接着就会发生,那不是别的疯狂,就是贪婪的疯狂啊,无底之洞,永远也填不满的。
午夜,沉沉无边的夜色像贪婪的疯狂弥漫了宇宙,人造的卫星仅仅能在茫茫太空划过一点光亮,花大姐忧心忡忡地睡过去了。她在莽莽的荒野上跋涉,荆棘榛莽剐破她的衣服。她走过干涸的河床,找不到水洗一洗身子。她走上没有人影的大道,有人突然从路沟里跃出来,拖着她向草厚的地方走,剥下她的衣服。她听见身上伏的人呼呼喘息,她想看看对方的模样是不是年轻,极力睁开眼睛,看见朦胧月色里目光不正,从斜侧的上方打量她,她慌忙大叫:
“昂子你个兔崽子,我是你妈!”
儿子明明白白地打消她的误解,说:“我要你的金牙。”
有多少事情功败垂成,都毁在说明上,说话之间,最有利的时机已经失去了。花大姐奋力挺身推儿子一把,儿子手中的锤子没有来得及敲到她的口中,掉到了地上。
大道无言,只有不加说明修功的人,才有望修成,定慧双修,他们从来不说废话,万千经卷都是对修不成的人讲的,咒语也是如此。三百年前,仙姑洞的尼姑曾经预言,三百年后有人在此修成异功,弄假成真的莫姑默默修炼,如期成功了。开发成旅游景点的仙姑洞,严格说来,并不是修功的好地方。不过,全世界的道观寺院,都被来来往往的游客挤满了,高德大师还是不断地修出来,有一些跑颠颠地去开会,鼻梁上架了眼镜,衣袋里装了手机,到特设的餐厅去吃饭,不破禁忌。自从日本人佐多太郎渡海而来,寻找秃尾巴老李母亲的墓有了结果,在仙姑洞附近立碑,增加了新景点,仙姑洞旅游区的游客没怎么显着增加,莫姑修功,却有了新的气机。她打坐入定以后,只要一想有一块石碑青铮铮的,立在仙姑洞旁边,就会看见一条长长的青蛇钻进水里,长驱直入,其势威猛。她趁机闭关,片刻也不松懈。她以意驭气,搬运“河车”,上冲“玉枕”,下透“夹脊”,撞任督,达会阴,子宫震动,****膨胀,她频频提肛,小肚子一紧一紧,像小孩子吸一个空奶瓶似的,小牛饮水也是这个样子。她变仙人坐为狮子坐,两腿劈开不收拢,要炼出大功,便于狮子大开口。她两手拄地,放在腿间,假装一座石碑立在那里,也不在话下,她微阖双目,睬也不睬。游客中也有人炼过功,像日本人佐多太郎一样,想跟她比试功法,她心情好的时候,就婉言拒绝,介绍他们到海滨乐园去,还特别提起四斤半娃的盛名,让人向往俄罗斯功夫。看了她仙风道骨关心红尘的样子,谁也不去深究一下,好功夫是不是就等同于好身架。也没有人从功夫的渊源上,去探究一下,深植于中土的异功什么时候跋涉过茫茫戈壁,穿越阿拉木图,征服过俄罗斯大公。千真万确,这种功法习惯漂洋过海走水路,登上大洋中的孤岛,比如珊瑚海域的霍尼亚拉呀,加勒比海的尼加拉瓜啦,它就是不便于走陆路,在沙漠中举步维艰。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原本有望先掉头南下,灭掉南宋******,把中国功夫装上马背驮着,再往西走,传向俄罗斯。可惜他记住了祖上受过胡人欺凌,急于报仇往西打,没有顾上。据艾特玛托夫说,成吉思汗西征时,他行辕的大帐篷顶上,最初一直有一片白云罩着,他拔营行进时,白云也跟着走。由于他的****和杀伐,白云中途消失了。艾特玛托夫没有再往下说,其实,那一片白云,正是中国功夫的气机,能随着征战的马队移动,降下雨来。可是战场上的杀伐过重,锦被上的杀伐不得不有所收敛。功夫用到了马背上,床上的功夫就要失传。海滨乐园的四斤半娃得不到中国功夫的真传,凭大取胜,顶多也就像跟奥瑞里亚诺·席冈多比吃的“母象”美女卡蜜拉·萨加斯杜梅一样罢了,只是个图腾式女性,“压骨头专家”,跟疯子饕餮者比试,能把人的疯病治好,跟理智的大食客对擂,就显出美中不足了。理智的人讲究招招入式,覆周环,下缺盆,过醴津,陵渤海,上常山,入玄门,一步都不许弄错。虎游蝉附,兔骛鱼嘬,热十动,接十节,观八动,听五音,每一招都不离经典。试问,俄罗斯四斤半娃粗粗拉拉的,有什么功夫应对?她根本无法跟修成异功的莫姑相比嘛。只有疯子才会丢下莫姑去找她。不过,不疯的人要上莫姑的床,也不是那么容易,她的床上铺了坐垫,坐垫裹了黄缎,除了皇家和尘外,没有人配得上那么黄。所以好多不疯的人被她拒绝,听她介绍四斤半娃,就往海滨乐园去了。山情海韵,既然不能兼得,那就单取一瓢饮吧。莫姑的异功留给包大万受用。她喜滋滋地告诉包大万,她修成了异功,志得意满的样子不像仙家那么清明洁净,活脱脱还是凡尘女子被风情****熏透的浊乱沉迷。包大万一听大喜过望,立刻就要试功。脱光了衣服以后,包大万想起,莫姑曾经夸耀过异功能饮水,他要先见识一番再试。他哗哗地倒半盆水,往莫姑的臀下放。莫姑用手往后挡,推托说:
“出家人不饮浊水。”
包大万用手撩了水让她看看,说:“干净嘛。”
莫姑说一个跟卫生城小册子上一致的理由:“它不饮冷水。”
包大万笑笑说:“它还挺娇气。”
包大万拿起仙家也用的人间暖瓶,把水兑温和,莫姑还是坚决拒绝了,她为包大万着想,认真地说:
“算了吧,别把你吓坏了。”
莫姑夸下的海口,把包大万激怒了。他此生曾经被好多人瞧不起,他瘸腿的鞋匠父亲,临死得不到一双女人的鞋子,火葬场的瘸腿烧工瞧不起他,要先领饭吃了再烧,他建起自己的火葬场,烧全三河所有人的父亲和母亲,人人都要从他的大烟囱里过。他的身子又短又粗,想女人快要想疯了,****成性的花大姐瞧不起他,要求他把身子长得像头一样又大又长再说,他建起自己的海滨乐园,治所有男人想女人的疯病,花大姐送上门来,他宁肯推给德国狗,疯儿子要治病,得拿着钱来。他有金雕岭金矿采挖不止,手里握着金子,腰里别着金子,还有冷库贮藏时鲜,他在女人堆里打滚儿,再也没有人瞧不起他。他是市政协委员、着名企业家、预备役少校,他在女人的手下屡败屡战,从来没有说过服输的话,唯一的一次,只对彭妮娜说过,需要疯子对付她。莫姑修功,本来是得了他的资助。神仙只有不吃饭,才有资格瞧不起给饭吃的施主。莫姑即便修成了美国功夫,她也没有理由瞧不起中国爹——她修功未成的时候,跟包大万交合到好处,常常“爹爹、爹爹”地叫。乔乔结婚后,倒不再叫“干爸、干爸”了,只剩下诗人流涎吐沫“啊啊”的空洞,讨论会过后,也没有大的起色,还是些老诗。包大万真的气愤莫姑瞧不起他,他不再让莫姑饮水看,也不用手端开盆子,而是一脚踢翻,床铺湿了一半,他就在干松的一半躺下,让莫姑施展功法。他倒有心像一盆水一样,摆在莫姑臀下,让它含了管子吸,可是他实在压不住心中的愤怒,他颠上倒下,不把莫姑当修成了异功的仙姑待,倒像对待一匹母马似的,像对待一条母狗一只母山羊似的,翻来滚去,滚到了床铺透湿的一半上,根本不问问对方嫌不嫌凉。修成异功的莫姑果然不含糊,此功发起来,能嗞嗞地吸进半盆水,肚子也不见高起来,功一松,哗哗地吐出来,肚子也不会瘪下去,身体外面的水自然不在话下。莫姑保持沉默,暗暗发功,任凭包大万百般折腾,她自涵养吮收。她闭了眼发功不休,包大万浑身抖动,摇晃抽搐,啊啊大叫响彻了仙凡两界。秃尾巴老李母亲的魂灵听见大叫,从飘渺处飞来,在日本人立的石碑跟前停一停,又赶快飞走了,她闹不清,人间功夫修得为什么会让儿子大叫,像要死一样。神仙母亲生儿子,或者从肩膀上生,或者从胁下生,她自然不懂得“痛”和“快”原本是相连的,是从同一个地方产生。霎时功收法止,莫姑睁开眼睛,看出包大万脸上的神情不一样了,像秋霜打红的一片叶子,像大水漫过的一片菜地,红彤彤坦荡荡的,再也没有了原来的煞气。莫姑先不问他服不服,只问他好不好,他有气无力,叫好不迭。莫姑问他像什么,他想一想回答说:
“像拔火罐。”
又否定说:“不,像勒着脖子上吊。”
又修正说:“像踩着小肚子拔去。”
莫姑笑了,这才问他服不服。
包大万点头说服了,他不免有些害愁,说:“我怎么办?”
莫姑指给他唯一的路:“也练功呗。”
包大万不屑地说:“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