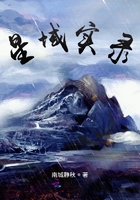海滨乐园绿生生的夏天,乔乔回来了。她是包大万的干女儿,回来是很自然的事,季节也恰在好时候。京华虽美,凉爽的海风却吹不到那里去,有钱人还是要到海边去避暑,不管是不是富人的干女儿,有钱就走。海上的凉风顺着波涛,往靠近天堂的地方吹,让人想念舒服和惬意,神思遄飞。在海滨乐园的那一边,老龙头长城脚下,砖石被海水泡得长了厚厚的绿苔,前朝皇帝的诗刻在石头上,又被后人镏了一遍金,辉耀着风流皇帝自大的胸怀:“我有一勺水,泻为东沧溟。”皇帝的一勺水里,三伏天泡满了红男绿女,涨潮时,花花绿绿的泳衣会漂到大海的另一边,泳衣的带子上留了男人的牙印,显然是被男人的牙齿在水中咬断了。乾隆皇帝的魂灵捡起来看看,自愧不如,不敢再随便作诗了。
乔乔却一举成了诗人,好像成心跟包大万过不去似的,一见面,她就念出一首诗,让包大万答对:
鹅鸭水里游,
牛羊山坡追,
天上下大雨,
满地水多美。
包大万念书不好,倒不缺诗才,他要是有耐心,稍加思考,想一想,有一个时期,大家在地头上赛诗,他一口气就能念出六首,每一首都不离开“社会主义”,他就能对上乔乔的诗,充满新时期特色。他积攒了对乔乔太多的激情,一心想跟她赶快上床,把诗写到床单上,他就顾不得念诗答对了,动手就剥乔乔的衣服。乔乔挡回他的手,再念一首诗,自由体:
一看到你,
我就充满信心和勇气,
必胜的信念树立起,
争取最后的胜利!
包大万颇不服气,说:“那可不一定。”
乔乔来不及念出第三首诗,包大万把她抱住,解除她诗的外衣,直达诗欲的本质,却原来仍然不容易。乔乔去京华念书,学会了新的武装。去掉了外面长一些的衣服,她里边自肚脐以下,交叉盘结了一些带扣,复杂多变,看不清来龙去脉,细看似乎也有规律,却找不到头绪在哪里,系了疙瘩的死结在什么地方。比起在天涯海角随便写诗的老皇帝来,包大万尚有锐利的牙齿,他一根一根咬,也能把所有的带扣咬开,拼命作诗。可是他没有那么多耐心润笔。他急得乱扒,想在带扣间合适的地方扒开一个口子,想不到带扣像顽强的水生植物,消灭了还会生长,刚刚以为扒得可以了,手指头一拿开,带扣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封严了。无奈中包大万想到了动刀,他把祁丽英装了杀人犯腰子想杀他的刀子操在手上,恶狠狠逼近乔乔,乔乔一害怕,一只手伸到背后一摸,重重盘结的带扣无声脱落了。乔乔再念两句诗:
来吧,来吧,
丢下钢刀拿起枪,
咱俩来比量……
包大万不容她空口念诗说大话,把她流诗的口子紧紧堵住,她滑溜溜的诗句硬要往外流,也要等包大万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夺罅而出。包大万又欢喜,又新奇,他把干女儿送到京华念书,天气大热,竟让他得了一个诗人。女诗人满口流诗,盘结的带扣后面倒没有变得文绉绉发酸,还是原来的老本色,赤灼灼火辣辣热腾腾湿乎乎,锦心绣口,诗囊密藏。包大万一番番深入,探囊取诗,他恍然明白了乔乔的诗意:牛羊在山坡上追,就是追着赶着求媾嘛,天上下雨,地上流水,就是男人出汗,流到女人的池子里,鹅子鸭子跑进去洗澡嘛。他终于败在了乔乔手下,让乔乔胜利的诗没有变成空喊。他像一般没出息的男人一样,在女人身上用完了力气,耗尽了激情,才想起了作诗,所以这种诗原本节奏分明,富于韵律,可以分行排列,也让他念成了拖泥带水叽里咕噜的散句,像他在床单上写下的一样不利落不鲜明,勉强断开,也是这个样子:
离地三尺一道沟
一年四季水长流
不见道士来挑水
只见和尚去洗头
他喘息不定地念完了,停一停问乔乔:“你说是什么意思?”
乔乔枕着他的胳膊想半天,想不出什么意思来,就说:“你这是朦胧诗,我不懂。”
包大万把乔乔的一条腿扳上来,一只手伸向诗的中心,拨开朦胧,逐句讲解,层层深入,照章演示,揭橥出鲜活的题旨,到最后总结说:
“这不是朦胧诗,是谜语诗。”
乔乔说:“朦胧诗就是叫人猜谜。”
包大万问,朦胧诗能不能把道士猜成和尚?
乔乔不容置疑地说:“当然可以。”
包大万把一根指头插向朦胧诗的诗眼,说:“谜语诗就不能那么猜,洗头的是和尚就是和尚,不是道士。”
乔乔问,谜语诗为什么那么刻板,让人为难?
包大万让乔乔看清谜底,说:“和尚不戴帽子才洗头,道士戴着帽子嘛。”
乔乔接触到谜语诗的大海边,不敢再依仗从京华学来的文化随意作诗,为难包大万了。她解除了最初诗的武装,再也不把复杂的带扣装到脐下,她即便重新装上,包大万掌握了机关,也只是举手之劳,把手往后面一伸,就能打开,像城里的一些重要部门,前面的大门口站了岗哨保安,绕到后面,就能够摘除戒备,那只是装在后面的一个小扣子嘛。再紧要再隐秘的部门,后面的小扣子也举手可除,除掉之后,前面的****大开,花径待扫,水流诗泻,可搞腐败。盛夏的海滨乐园外边,是热热闹闹的大海,这一片大海,也属于前朝皇帝的“一勺水”域,“东沧溟”的骄阳下泡满了男女身体。有没有乾隆皇帝游泳的照片呢?风流的前朝皇帝把大辫子盘到头顶,像一座金雕岭,身边围了满汉全席的浴女,穿了不同民族特色的泳衣,会游泳的太监不穿裤衩警卫,冻紫了嘴唇,谁都不在意他们。“腊雪难为白,秋旻差共青”,大自然的色彩,被皇宫禁苑的肌肤无情地比下去了。自从伐倒松林里的树木,海滨乐园建起来,每年都有人在海水里淹死。有人开车从城里来,在车里边换好泳衣。车玻璃从里边糊了“朦胧纸”,他们能从里边看见外边的人,外边的人却看不见他们在里边换衣服。他们从车里边拿出折叠的橡皮艇,在外边充气,再从车里边抱出西瓜,装到艇子上,一男一女划进海里。橡皮艇越划越远,海边的人渐渐地看不见女人雪白的臂膀了。拿了望远镜的人调好焦距,瞄准了看,才能看见男人压在女人身上波涛起伏,橡皮艇在海水里打转。火辣辣的太阳烤着,忙碌喘息的男女必定口渴,他们要吃西瓜解渴。男人把西瓜放到橡皮艇沿上,一刀切下去,橡皮艇随着西瓜也裂开一道口子。他们在橡皮艇上坐起来,要吃西瓜,海边拿望远镜的人就不看了。等到拿望远镜的人再把镜头架起来,就逮不到海上的目标了。乔乔大发感慨,作诗一首,像所有诗人一样,使用夸张的语言,夸大了海上的惊险:
惊涛骇浪稠,
你是一位舵手,
船破了,
你也得到了好受。
很明显,乔乔的诗人情怀,赤裸裸倾向于那位不认识的男性,女人的贡献只隐晦地做了暗示,深得诗法。此诗她在跟包大万交欢的时候不念,包大万就不知道,她脑子里还藏了浪漫的想象。她跟着夏侯狗王学画画,准备先画鸡,再画狗,由禽兽入手,步入艺术的殿堂。做了包大万的干女儿,进京都念书,在艺术的惊涛骇浪中翻滚不久,她就发现,写诗比画画离艺术更近,更省力,不必支起画框,走着坐着站着躺着都能出诗。她丢掉画画,改为写诗,两只手立刻变得干干净净的,不像过去那样常常沾了油彩墨汁了。夏侯的狗王越做越大,专注于视觉艺术,笔下的形象总是毛茸茸的,真的不常看见光光滑滑的乔乔。京都太大,埋没一两个艺术天才,像大海里淹死个把做爱切西瓜的男女一样平常。乔乔离京,重回三河,才算找到了她的艺术之根,有望长大。包大万的头又长又大,那里面应该饱蕴了诗的矿藏,供乔乔开发。包大万并不探究乔乔在京都的生活秘密,干女儿学成归来,报效于他,看一看重重盘结的带扣封在前面,大可放心。包大万淘金致富,遵从实实在在的经济法则,只要把金子沉甸甸地握到手里,金洞子曾经被什么人的钎子开掘过,都不必计较。他不好想象,不尚浪漫,所以他绝不带着乔乔到海上去划船。海边浅水里泡的人散尽了,乔乔在海水里作诗,硬把他拉进水里交欢,他也脚踏实地,让乔乔的腿勾住他的腰,身子在水里漂起来。乔乔长得比他高,他立在浅海斜坡的这一边,一仰头,能咬住乔乔胸脯上一块肉,正好。总的来说,包大万还是不太喜欢跟乔乔在水里行事,他的优势在陆地,不在海上。他头重脚轻,不会游泳,海水荡漾起来,浅水里站着他也害怕,他不是惊涛骇浪里的好舵手,倒要常常任船摆布,让乔乔笑话他。在陆地上,他就掌握了主动权。乔乔虽然进过京,有了艺术手法,床上床下,还是包大万操纵她,频频进攻。像曾经把祁丽珠从楼上叫下来,看德国牧羊犬得贝****,有贵妇人带着小狗来,包大万也会把乔乔叫下来。等不到看完狗把戏,包大万扯上乔乔的手就走,不及上床,倒在地板上就重演起来。在德国牧羊犬和贵族小狗叽哇的叫声中,乔乔使用京华的华丽技法,虚实兼顾,把包大万送上天堂,倾听天籁,她娇喘吁吁莺啼唧唧,抽空子提出一个建议:
“咱结婚吧。”
包大万等落花流水喘息平定了再考虑,说:“不知道包勇能不能同意。”
乔乔不满地说:“我是跟干爸结婚,又不是跟干儿子结婚。”
包大万要在乔乔的胸脯上掐出水来,说:“我是说,你比儿子还嫩嘛。”
乔乔忍住痛说:“这有什么!”
她把包大万的手拿开,告诉他京华婚姻的新风尚:有钱的老头子,老掉牙的艺术家,专娶嫩得出水的小媳妇,小媳妇私下里按年龄叫儿子爸爸。
包大万问,老掉了头发的大官娶不娶小媳妇?
乔乔告诉他,大官老了,不把小媳妇娶进家里,在外面买一座小楼养着,按时叫秘书开车,拉了大官去幽会。
包大万问,大官跟小媳妇开“会”的时候,秘书干什么?
乔乔轻描淡写地说:“给大官站岗呗。”
包大万吁出一口气说:“那我就放心啦。”
乔乔问包大万,有什么不放心的?
包大万重复说:“我就是怕包勇不同意。”
乔乔问包大万,怕不怕祁丽珠不同意?
包大万把手一挥说:“这是我们家的内政,她不是家庭成员。”
乔乔酸溜溜地说:“她可是你的助理呢。”
包大万哼一声,说:“我叫她理,她才助。我不叫她理,她助个鸟。”他把乔乔的嫩手抓起来,放到毛茸茸的鸟羽上,说:“你给我理。”
包大万陡然硬起来的态度,决定了他商讨家庭大事的时候,不会有祁丽珠参加。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家宴,只有乔乔、包勇和他本人出席。他像金雕岭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跟人家谈判一项业务,把对手当成酒徒,等喝过了三杯酒,才谈意向。包勇听了以后,没有表示反对,只提出一个疑问,他看着乔乔说:
“我爸跟干女儿结婚,我叫她什么?”
不等包大万回答,乔乔大大方方地说:“随你的便。”她紧接着吟出两句诗:
不管你叫我什么,
我也是你的小妈。
包大万叫出一声“好”,又说“对”,也诵两句诗:
社会主义大步迈啊,
捡到篮里就是菜啊。
包勇端起酒杯,说:“那好,祝小妈快活!”
于是一家三口在桌子中间碰杯,包大万和乔乔胳膊与胳膊交叉相挽,提前喝下交杯酒,然后,一家人兴高采烈,策划起婚礼庆典。包大万是一家之主,说了倒不算了,要听儿子和小妈摆布。乔乔闯荡京华,常常到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去逛荡,主张举行广场婚礼,氢气球拖了长长的绸带,能直接飞到天上去。她的设想,遭遇了最大的地域困难,三河地区还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广场,能装下京都才会有的奢华,三河县城正在创建卫生城,也没有辟出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广场,好让人举行排场的婚礼。包勇就此主张,因地制宜,把婚礼拉到金雕岭上去举行。不必担心矿山荒凉不喜庆,可以装扮,把红绸子搭到山顶上,搭三条,从山顶一直搭到山底,一对新人踏着红绸子上山,在鹰鼻子上接吻,套上戒指。乔乔接受了包勇的铺排,却指出,他的创意抄袭了一个“爱母体味”,电视上曾经有过三条红绸子从山顶一直铺到山底,比比画画的男人踏了红绸子唱歌。包大万听明白了,“抄袭”就是“偷”的意思,立刻揭露那个“爱母体味”,是“偷”了“**********”的“祖国山河一片红”。乔乔再念两句诗,无韵,体更自由:
大偷偷国,
小偷偷鸡。
包家父子一时不明白,她在骂谁。
婚礼逼近,夏侯狗王从京都赶回来,帮助策划,他只赶上写个结尾,就是设计洞房。他仍然力主包大万买一个性爱床。这种床,乔乔在京都已经见识过,只是没有使用。卖床人揿动电钮,空床演示效能,后来又有女店员穿旗袍上去演示。一个人演示的效果不太明显,乔乔已经得出了结论。看了那些起伏蠕动的凸起和坑凹,乔乔没有想到设计此床的男人无能,她只断定那人肯定奸猾,无论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都是个懒骨头。她到了床上,从不偷懒,有多大的劲都会使出来。不过,要是性爱床能帮她省一些力气,她倒可以抽空子作诗。她被夏侯狗王说得有些动心了。夏侯引她走进艺术大门,就是说到床上事务时,最像个导师,令人钦敬。乔乔的心痒痒的,眼角一挑一挑一闪一闪地看包大万。包大万倒不用眼角看她,用一对囫囵眼珠瞪她,问她是不是嫌海滨乐园的床不快活啦,乔乔扭一扭身子否定了,说:
“人家是想让你省点力气嘛。”
包大万拍一拍胸脯,把短短的身子伸直了,又长又大的头昂昂挺起来,说:“老子有的是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