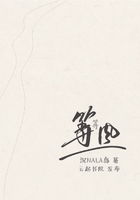那嬷嬷在前面指路,流苏锦绣照旧一左一右搀扶着我。
昔日新碧辉煌的忆雅阁,众妃眼红的忆雅阁,竟然因为常年无人打扫,变得如此不堪入目,我抬起头仰视着那牌匾上的龙飞凤舞,这是他亲笔题记的,在他死后,竟满是灰尘,侧端竟还结出了蜘蛛网。比我曾经被贬时居住的朝华宫也好不了多少,这宫里的人到底是趋炎附势的多。
嬷嬷回头看到我停在门口迟迟未动,便催促道,“太皇太后,我家主子怕是撑不过一时三刻,劳烦您快点。”
我一天便收回了瞩目在牌匾上得双眸,瞟了她一眼,看她那心急的样子。
“急的是你主子,又不是哀家。”说着便也不想与她太多纠缠,也就朝着大门越过她迈了进去。
一入房来,一股异香便袭人而来,让人心猿意马,这异香和长乐宫里焚着的梅花香一样都是他下令调制的。当年只因为我看到梅花无意中吟了一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他便当真记在心上,为我调制了梅花香,说是没有感动那是假的,收到这份礼物的那一刻,我宁愿相信他爱的人是我,可这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而这异香,他起名游园惊梦,很美的名字不是吗?我却知道所谓异香也不过是他所爱女子之体香,更知道这异香除却体香之味更是掺了麝香,只是不曾说破。
映入眼帘的便是贴在墙上的仕女图,不用说也知所画之人定是梑贤皇贵妃,只是这参照的人却是桑妤思,也亏得某人就爱做别人的影子、替身。
遥看画中人倒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境。
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
头上墨玉钗,腰系白丝带。一身孝而俏,却待入宫来。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远。双目无风采,却又好出尘。
这大概还原那年婷玉姨娘死后戴孝时的情景吧。旁边还有题字小楷“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呵呵,一语双关,夸得是昔日梑贤皇贵妃,讽刺的却是依仗伊人容貌得宠的景嫔。实在是太祖皇帝的文风,用眼前人之美,更加衬托梦中牵绊之人,可怜的桑妤思呀!只是他就不怕污了他的她吗?这么圣洁出尘的女子,竟与揽月阁曾经花魁相提并论。男子果真好是无情。
案上还设有一把扇子,一个玉佩,一把宝剑,全部都是他生前的贴身之物。我走上前去,依次拿在手里把玩,物件并非想想中的那么冰凉,仿佛还残留了他的体温,我手握那把宝剑时,忍不住把他贴在怀里,却又是那么失望,这哪里还有他的味道?都快二十年了,就是有也早就散了,所谓体温,也恐怕是桑妤思得日日思念吧。
“太皇太后!”见我乱动案上的东西,嬷嬷赶忙上前阻止。
只是内屋传来了一阵虚弱却依旧妩媚的声音,“芪纞,随她吧。”
嬷嬷愣了一下,便不再阻止。
“弘德夫人,”她唤着我曾经的封号,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只觉得她的语气里怀揣着笑意,仿佛等了这一天已经好久,又仿佛在笑我…“姬妾,病重。咳。怕是。不能下地迎接…行礼了,劳烦夫人。咳。进屋一续。”我没有纠正她,因为我知道,如今的她还一直活在十几年前,就活在他离世的那年。
芪纞朝着内屋走去,很慢,时不时地回头,我知道她在引我过去。我撇开搀扶着我的锦绣流苏,示意她们不必跟来,流苏的神情有些紧张,我知道,她是怕桑妤思对我不利。我冲她淡淡一笑,便跟随着芪纞,一步一步朝内屋走近。
进了里屋,却发现这屋子实在出奇的小,远远不及我过去初为贵人住得流水阁大,屋内只有一个卧榻正对着门,两侧一边是梳妆台,一边是衣柜,再加上挂在墙上的两幅字画,卧室门口立着的翠玉花瓶也没有什么了。
我颦了颦眉,问道,“这忆雅阁的奴才们哪?”
芪纞刚要开口,就闻那卧榻芙蓉帐里的女人,身子微动,接着缓缓回道,“心都不在这了…还留得何…用?都放他们走了。”
我几步上前,犹豫了一下,便坐到了那芙蓉帐边,芪纞想另给我备座,却让她主子阻止了。
我没有急于掀开帐子,反倒是问道:“何时生病生的这麽重了?怎么也不请太医。”
“呵呵,妤思这病太医…咳…又岂能医好…咳咳…”说着她宛然笑道,“。妤思…咳咳…害的…这是…相…思病。”
她的这种说法,我自是不喜。相思病,大概我是没有她病得这麽重吧。
我冷笑着,说道:“是哀家不好,一转眼都快二十年了,都忘了来瞧你一瞧。”
“都二十年了,呵呵,妤思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三郎,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妤思坐在舟里弹着琵琶,好不惬意。忽闻那边有箫音和鸣…。”她没有理我反倒是自说自话起来,一提到她口中的三郎,她的精神似是好了很多,连话也变得连贯了起来。就仿佛这话说了很多年,天天都在重复。
“当时我很心急,便让芪纞出去看看,芪纞出去了,过了一会回来笑着说是个公子,我更加欣喜了,就赶忙让两个舟并在一起,好让我见他一面…”说道着,她顿了一下,似是看看我,“姐姐,你觉得我是不是很贱?呵呵,我知道你一直这么认为,我是你的妹妹,你从不这麽叫我,我也从不敢叫你姐姐,可是我就快要死了…。姐姐…”
我听到这里不知道怎么,突然有些哽咽了,不是为他,只是又想起了那个男人。方打算说些什么打断她,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见我不语,她又继续下去,“我知道我不配,不配叫你姐姐,不配为你和梑贤皇贵妃的妹妹,不配为桑家的女儿,因为我是个…。妓女…。呵呵,一个很贱很贱的妓女…咳咳…”说道这里,她反倒是咳得更加厉害了,“我是个妓女…在他眼里…依然…”
“所以。他只把我当做…梑贤皇贵妃的…替身…。影子…那我也…甘愿…。”
我看她实在可怜,便劝了她两句,“其实,这硕大后宫那一处没有她的影子,你爱他我佩服,可又何必如此执着哪?”我说的不是假话,对这个女人我虽有不屑,但一想到她爱他之深,竟远在其他包括我之内的女人之上,也不免有些佩服。
“姐姐。”她突然又唤道。
“额?”我竟是应了,她强忍着痛竟是要爬起来,我赶忙撩起帐子,她的脸竟无半点血色可言,蜡黄之中还泛着惨白几许斑点,眼角的鱼尾纹也呼之欲出,再不见往日绝色娇美之态,我急忙抓住她的手,竟然是那般骨瘦如柴,她那原本墨黑柔软的秀发竟与我一样早已花白大多了,眼角也起了少许细纹。
想到同样是两个深爱他的女人却彼此之间自相残杀我不禁心软了起来,可“妹妹”这两个字却到了嘴边却迟迟张不开口,好不容易鼓足勇气,音量却小得连我自己都听不清。都这么多年了,我都在想些什么,是在嫉妒吗?嫉妒她霸占了他?何苦哪?没有她,还会有别人,又或许是身为官宦嫡女对风尘女子的鄙夷?我何时也变得如此世俗?。想到这,想到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曾经娴静自若,犹如幽谷百合般的女子已经成了现今的凄惨模样,想要安慰敷衍她一声,好让她得偿所愿,反正不过是个“称谓”,可以对针对任何一个与我平辈从年纪上比讲我小或者说在名位上说比我低的女子。这个“称谓”我称呼过的人不计其数,但对她,这声妹妹却怎么都喊不出来,顿了许久,才勉强说道:“妤思,和哀家离开这里吧,哀家给你请最好的御医,一定能治好你的病。”
这勉强来的话落在桑妤思耳里听起来却像是浓浓地体恤,想不到的是她感动得竟啼哭了起来。
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哄着她,眼底是深深地歉疚。她有什麽错?被卖入青楼又不是她的选择,本来是打算来嘲弄对手的我竟然软了下来。现在的我很是矛盾,正如这世间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很矛盾很矛盾。
“姐姐,”哭了一会,她又强忍着说道,“妹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不必强求,能够在临死之前得到姐姐的谅解,是在是妹妹之大幸。”
回光返照,这四个大字立刻惊醒了我。
“只是有一件事…”只见她又要坐起来,芪纞便过来想要扶她,我先她一步,把她扶起,让床背支撑着她的全部。
“姐姐…咳咳,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说道着她竟又想要跪下,我赶忙阻止。
“妤思,你且慢说。”她即便体力不支,这句话却沉浸在心中一直想说这件事定是在她看来很是重要。
我愣了愣,嘴撇了撇,想到我也有很多地方对不起她,所以无论她有哪里对不起我,我应该也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将心比心罢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反了咬素唇,说道:“姐姐,我就快死了,若是在瞒着你,妹妹怕是死也无法面对三郎…。也无法面对你呀!”
说着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又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姐姐,三郎…三郎其实…。爱的人一直是…姐姐你呀!”
她说道这,我便犹如被电击一般,赶忙抽出被她紧紧握住的双手,竟然猛的站了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失态了,走了几步,我转过身,避开她和芪纞的目光,自嘲地笑道,“这不可能,你不要逗姐姐了,世人都知道永昌皇帝只爱过梑贤皇贵妃。”我告诉她,却也是在告诉我自己,桑榆呀,你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那个人爱的是桑雅,那个他赐名梑的女子,那个被姨妈灌了绝子汤,他反倒来怪你,叫你护着却没护好的桑雅,不是你,你一直都是个肮脏的女人,贪恋着权势,这样的你根本连争都不配。
“姐姐,你也说是世人都知道,你并不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你有怎么会感受不到三郎对你的情谊哪?”她似是在质问我,却让我发疯,为什么都这么多年了还要来开我的玩笑。
“不要讲了。”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可以冷冷地,却还是…。
“姐姐,你知道太后死后,三郎为什么要把你关到朝阳宫?”她并没有因为我的阻止而停止接下来的话,我本想跑开,但内心却还是想听听她的说辞,仿佛若是跑开我会后悔终生。
“三郎一则是为了护你周全,二则是怕见到你,他会深陷进去…。他曾经对梑贤皇贵妃许下一生只爱她一人的承诺,但是他违约了,年少时,那懂得什么是爱情?他怕他见到你就会情不自禁,从此万劫不复,可是…。怕见又怎能阻止相思那?你可能不会知道三郎每天晚上都不得安寝,从一更开始他就会跑到朝华宫,无论下雨或是下雪都会一直站到早朝,都只为了看你和你的儿子过的好不好,吃的饱不饱…。”
她说道这里,我便开始冷笑,嘲讽着自己,后又想到朝华宫的遭遇眼角方有些湿润,心中的感动却不过稍纵即逝,“荒唐!他若是怜我和屷儿半分,又怎会让我们在那朝阳宫那个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晚上还时常闹鬼的地方多呆一日。你就莫要哄我了。”收起了感动,很快地理智起来,想要逃离这里。
“不是。”她语气焦急起来,“真的不是,三郎真的有他的苦衷和无奈,他爱的真的是你呀。
三郎他一直把我当成梑贤皇贵妃,可是和我说的一直都是你呀,我还记得那天…。对,就是那天…”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欣喜了起来,“姐姐你还记得三郎去世的那天,你也在,三郎抓住我的手,其实是把我当做你呀!都是因为我的自私,若是早点让你知道,也不至于让三郎遗憾而终…。三郎,三郎那天问你,若有来生,他若为寻常人,你愿不愿再为他妻…。对对,就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