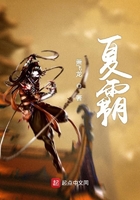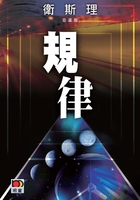莽原上艳阳朗照,幽谷里秋风萧瑟。山壑沟峁之势,渐渐趋于叶脉的形状。临近叶柄处,显得峻峭起来,有一种古铜的色调。雄浑的沉积岩,在粗朴的纹饰里,形成众多姿态迥异的巨大雕像。巉崖与绎紫色霭岚下的山地之间,便是深居于晋陕峡谷中的黄河古渡,即我们的去处了。
站在高崖之颠而鸟瞰脚底,大河呈一个弯弓的模样儿,在深深地湍流着。古渡的村落,拥簇成船的轮廓,静静地泊在岸边。一叶扁舟,正荡于河面上,朝彼岸划去,若一只戏水的蜓蜻。临谷底还有三里之遥,嚯嚯的水声已浮上我们头顶的云天。
向导是一位老人,船工出身,是我们途经公社时搭伴而行的。他身材瘦削,花白头发,紫褐色的脸庞,鼻梁直直的,眉宇下有一双鹰的眼眸。尤其是那线条分明而深邃的额头,象藏着几条默然潜流着的黄河。
踏入村来,正值午饭时分,犬吠声中是炊烟的清苦味。沙滩上,是花生枝蔓的浅黄。石缝里,是菜蔬叶瓣的油绿。石板街巷,石板篱笆,石垒的院墙,石垒的窑舍,石头碾磙,石头磨盘,全都掩映在苍虬的枣树下。秋收秋播的人儿,赶着牲灵从山后回村了。街巷里,有拙朴的老人蜷曲在石板上晒枣儿,抬头见有客来,笑着让捏着吃鲜。蹲在碾盘上的后生,敞着黝黑的胸脯,抱着个大粗瓷海碗,停住筷子,怯生生地望着来人。几个脸蛋红润而身段健美的女子,一手挟着盛衣衫的木盆,一手提着棒槌,端庄地从身边擦过,却扑哧地笑出声来。
向导老人与村人打着招呼,厉声喝走尾随来的一伙看热闹的孩童,领我们径直到了他的窑院里。步入石窑,一条铺了毛毡的石板炕,占去了近一半的地面。家俱不多,却古色古香,一律嵌有亮铜的装饰。瓷瓮瓷盆瓷罐瓷坛儿,都抹拭得乌黑晶莹。坐在炕头,隔窗可见院墙下的马厩,一头枣骝马在绊着前蹄。一旁的狗窝里,大黑狗儿在打盹呢。而嚯嚯的黄河,如同宽阔的湖海,满世界涌流着。
黄河,对于贴伏在她身边的子孙是爱怜的。这古渡口的延水关,自古就曾是一个颇热闹的码头,关里人家,原是靠扳船过光景的。向导老人,从小就闯荡于黄河上,随父兄扳船拉纤。船夫们常从上游买山西的瓷器、铁器,塞上的皮毛、咸盐一类货物,顺流而下。途经家门口,系船停泊一宿,天不亮与父老妻女在岸边拭泪告辞,三五天就抵达了潼关。然后背纤而上,在奇险的鬼路上要攀许多日子。也常有船翻人亡的祸事发生,船家寡母孤儿被暴戾的黄河遗留在这僻苦的古渡口。穷苦人遇上发水时节,便冒性命危险裸着身子下河捞炭,猎取点物什。摆渡于河口的羊皮筏子和木船,则是每日数趟,摆渡着晋陕之间的贸易货物,摆渡着旅人的希冀。
尔后,河道堵塞,河水流量也小了,水上交通逐渐被公路取而代之,延水关的人就只指望于摆渡了。码头萧条了,船工们不得不把生活的希望寄予身后的远山莽原,爬坡去耕耘播种,不是在水上而是在土地上点播收获,渐渐成为庄稼人了。
苦焦的生活,逼使延水关人奋起。自一九二七年陕北闹红的日子,船夫们就组织起农会,闹开翻身了。战争年月里,奔赴延安的青年从这里渡黄河而走向光明。东征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开赴抗日前线。小小的延水关,是红色的驿站,是母亲延安伸出的手掌。古渡的船夫之子,就曾有七十多人参加了革命。边区那阵,隔岸是阎锡山的碉堡群,不少群众被打死打伤,人们只好天亮前吃饭,在后山劳动一天,晚上才回家来。当时,黄河渡口压了口子,十多年没有船只往来。搞起统一战线,延水关设了贸易公司,用食盐、石油与阎锡山交换枪支、布匹,渡口还红火了几日。
向导老人兄弟两个,哥哥到了晋绥,家里他撑着,一直在地方上干事。胡宗南进犯边区,他领着乡亲们过河去,背上婆姨,一手挽一个猴娃娃,踩水风浪里。那阵年轻,血气方刚,水性又极好。划羊皮筏子顺流而下,可以平躺在筏子上,任激流送飘数十里,礁石涡流也不在乎。后来,他做过公社书记,再后因故又回到黄河上扳船背纤,前两年才恢复工作做公社一般干部。二十年间,虽饱经沧桑,但如今公社的事,他还是敢说敢管,一股黄河所给予他的船工的倔性子。
吃罢向导老人的儿媳做的羊肉荞面,我们便出窑院逆流而上,去乘船渡河。河湾的岭崖下,泊着一只木船,浪花在啪啪地拍打着石岸。集体的一只旧船发洪水时被卷走了,渡口上唯一的这只船,是老人本家侄儿们新置的。稍时,向导老人差孙女唤来的船工吆喝着赶来了。掉头看去,四个精壮后生,正虎虎地从向导老人家门口走过。那里是一座凸出的石崖,窑舍原来是悬在黄河波涛之上的。
秋里的黄河滩,在这午后时分,闷热得象是伏天。无怪,年轻船工还是赤脚片子,光着黝黑发亮的背脊。船工中间,唯有一个戴眼镜的后生着件短衫,戴着手表,文气得很,笑笑地呼唤我们,象是帮忙扳船的。久已等候在渡口的几位旅人,背着沉重的麻包,面情坦然,不知家在此岸还是彼岸。他们每人付过一元钱,爬入船中了。我们要付钱,蹲在船帮上闷抽旱烟的向导老人摆摆手,只好作罢。
扳船的后生们,在屁股下垫好老羊皮,操起了木桨。向导老人这才在船沿上敲了几下烟锅,解开缆绳,跳入水中。他背靠着船帮,弓下瘦削的身子,似乎是毫不费劲地一扛,船动了。只见他忽地纵身一跃,跳上船来,操起了大舵。船临入河心,扳船水手的号子象由远而近传来似的,愈来愈响愈有力了。呐喊声直扑彼岸的石壁,被猛地弹了回来,回寰于河谷之间。
船到河面正中,是一排一排几丈高的大浪。曾在山巅上望见的一弯流水,此刻简直成了汪洋,无比广阔。船缓缓地被托上波峰,又呼地跌入波谷。浪峰上见两边是幽深的水的沟堑,天为之开阔。波谷里见两旁是高耸的水的山崖,天也变得窄狭了。时而是凝固了的波涛,时而是流动着的莽原。狰狞的漩涡,奇诡的孤圈,挑逗着每一个企望彼岸的人。这吞噬过无数生命的巨浪,使得我们这些来领略黄河气度的旅人,已丢魂失魄了。一瞬间,似乎生命已濒于死亡的领地。涛声里时隐时显的号子声,使得我们安静镇定,自豪和骄傲油然而生,大自然的黄河,和自己贴得这样近!从内心深处,将自个儿的力量融入动情的呐喊。
扳船水手,大醉酩酊似地仰合着身子。时而伏倒在桨柄上,时而直立起来,又用脚蹬住船沿,仰倒得与船身形成平面。划呀,划呀,一种与命运死死咬住而奋力拼搏的气概。黝黑背脊的后生,呐喊里有深沉的韵和力。而戴眼镜的后生却是沙哑的嘶鸣,一种挣扎着向前冲刺的嗥叫。掌舵的向导老人,则神态自若,用那一种鹰一样的眼眸注视着水的流势,浪的神色。
号子声低了,船靠岸了。原来只是三分钟光景,却似乎是漫长一生的旅程。回望可以想见,木船是斜着被黄河推下几百米后才抵达岸边的。此刻,秋阳又这般艳,大河又是这般平和呢。而彼岸的一切,恍若隔世。
戴眼镜的后生喘着粗气,揩着汗,与我们招手相别,同船工兄弟们去背纤了。我们踏着湿而结实的沙滩,走在山西的地域里,朝危崖下的永和关而去。
这里的村人口语,皆与延水关同。主人与向导老人相互搭讪着,象在河那边一样稔熟。虽一河之隔,都属于远近亲戚,甚至于后山数十里也来往亲密。
我们在代销店买得两瓶汾酒,来到岸边一棵古槐下,等候背纤而来的船工们。河流是弯曲的,船工的背脊是弯曲的。唯有背上的纤绳绷得很直很直,象征着黄河子孙们的生活的信念。在沙滩上,在淤泥里,在石窝里,船夫们拉着他们亲爱的年轻的船儿上来了。
戴眼镜的后生,在扯嗓子呼唤开船了。我们跟随向导老人的脚步走下河岸。
浅滩里是一片片水洼,得脱了鞋子涉到船边去。几个船工后生,在接渡河人上船。有着黝黑脊背的后生,背孩子似地背过一位姑娘,毫无羞怯地开着玩笑。姑娘是前些天经这只船嫁往山西河岸后山的。按风俗,船工接送新娘是不收费的,收了八个缀有红点儿的鸡蛋般大小的白馍馍,就包定了事前事后的摆渡。看那姑娘,不,新媳妇,红红的脸儿,乌黑的粗辫子,晶澈的大眼睛,在后生背上用拳头轻轻捶着后生的光头,笑得铜铃一样。戴眼镜的后生,双手托抱着一位老人,递到船后去。人们围起船舱里一位后生新买的手扶拖拉机,打问价钱,赞叹着,羡慕着。
我们这才想起手里攥的汾酒,便打开来,挨个儿递给船工。后生们硬要向导老人和我们都先喝过,他们才喝的。一时间,你仰脖子,他抹嘴角,都说是好酒。末了,同舟的陌生人,不管老人,还是婆姨女子,都人人抿上一口,这才划动了船。
回程与来时船走过的斜线形成三角,直逼彼岸渡口。天色将晚,河川里起了风,水浪荡得更高了。在河心,跌过三个几丈高低的大浪,直打湿了我们的肩头。而呐喊的号子,更猛更烈。酒后的船夫,愈是添了几分醉意,仰合身子扳动木桨。倒是我们少了畏怯,多了自豪的兴致,扯嗓子合起了雄风般的船夫曲。向导老人,在号子的间隙处,来了几声深沉的吆嗷。
攀着石崖归去,向导老人间道:“这该认得黄河了吧?”是的算懂得了,但还不完全懂得。我以前虽观瞻过吴堡佳县的黄河气势,也领略过壶口禹门的黄河雄姿,也见过大荔合阳黄河的坦荡,和潼关黄河的折向东流,可心脉与黄河的旋律合拍,深深有感情大波的冲动,这还是第一遭呢!是的,黄河失掉了如此狂暴的性格,就不是黄河了。那么,船夫失去如此粗放不羁的黄河,也就不是黄河船夫了呵!
入夜,我们在向导老人家拉话,那位戴眼镜的后生来了,说一起去河滩上散散步。这后生,还真有点儿书生的浪漫气。我们掌着手电筒,走下石岸,向沙滩倘徉而去。
叙谈起来,知道他年方二十,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学,当了两年民办教师,前些时间被减下来的。如今兄弟几个,种着后山几道岭的山地,收成还可以,弄了这只船,抽空摆渡来往行人。日子是苦差些,还挺有意思,他喜欢诗,给县文化馆的《山花》投投稿。想他那扳船的神态,是有一种生活毅力的。问他说下个婆姨没有,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好宽的沙滩哟,泛着亮白的雾一样的清光,一弯小船样儿的新月正划桨在夜天云海。黄河在幽暗的崖下湍流,黑色里有千万种吟咏的声音,汇结成一河巨响。秋的黄河,夜的沙滩,给人几分神秘的向往,几分阴森和寂寥,几分多情的退思和激情的探求呵!
有手电筒的亮光闪来,伴有水桶的咣当声,狗儿前导,是古渡人下河汲水了。一个身影儿溶入河中,担子不下肩,弯腰将两桶一齐按入水里,回头闪着步子走去。狗儿蹲下来,注视了我们一会儿,又倏地撵主人去了。古渡的人,世世代代吃着这黄河水,虽说混浊,却也一经沉淀,便清亮清亮,味儿甘甜得象乳汁一样。
步回灯火点点的村中,听得有人隔着院墙对话,在说派民工修公路的事。公路通了,这河面上要架座新桥的,古渡又要红火了。那是向导老人的声音。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唤着眼镜后生的乳名,让带我们到隔壁去休息。
敲门声中,见新月已划过崖巅,河谷黯淡下来。似乎,是泊在港口的村落与莽原的巨船,在浮动着,颠簸着,用肩肿将新月掩在了身后。不知怎么,思绪又回到了黄河上的船中。
开门的是位老人。走入窑里,透过他擎着的油灯看去,足有七旬高寿了。他是向导老人的那位哥哥,古渡口的革命元老。早年在晋绥当过县委书记,搞过党的理论工作,后来回到故乡,已有几十个年头了。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易经》,工笔正楷地写了数万文字。他拿出收藏的竹笋化石给我们看,说是从后河湾采的。他谈起卜占文化与生命学的深奥学说,使得我们为之折服。在这僻远的角落,竟有如此博学而久历世故的布衣老人,确是令人惊叹。
枕着黄河的涛声,这个夜晚,我想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父亲们,我们一代一代船夫们,经历着生活的喜怒哀乐,仍在韧性地、拚力地划着桨叶,划呀,划呀,向着一个伟大的彼岸。这是一篇多么好的有关黄河的诗文啊!这一夜我失眠了。耳边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一更更,直到雄鸡的啼唱,窗户发白。
《青年文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