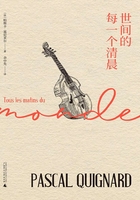隔壁的女人又从大洋彼岸飘来了信息,不过,这回的明信片上多了些蓝色铅笔字:还好吗小雅?你能想象到吗?我爱上了那个流浪画家。不过,令人沮丧的是,他的心里却居住着另外一个女人。为什么呢?有的爱,爱对了人,却爱不对时间;对了时间的,却又不一定爱对人。多么的无奈。但无论如何,祝你一切安好。也请为我祝福,好吗?
我仰头躺在红色五指沙发上,如果他在我的身边,我会枕上他的腿,而他会把细长的手指插入我的发间轻轻梳理,然后会给我朗诵小说中的对白,或欢喜,或悲切……那些日子虽在大脑中反复出现,却又恍如隔世。我在想,我们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呢?我是爱错了人,还是爱错了时间?又是什么,让我如飞蛾扑火一般勇往直前?
那天晚上小辫子还来了电话,让我不要介意马小波的话。我浅浅地笑,“他说的都是事实。”
“可是你并没有错,什么都可以勉强,唯独感情不能。”
那一刻,眼泪突然就没来由地袭上眼底。我是对苏谨朋没有丝毫情感吗?我是对林季阳没有丝毫留恋吗?不,不是。只是因为曾经在我生命中闪耀着光亮的另一个男人的存在,一切都变得没了颜色。如果抛却那10年的回忆,我想我会轻易爱上。可回忆就像瘟疫,肆意蔓延,它为周围的一切都打上了寂寥而空洞的符号,时刻侵袭着我,伤害着我。那些曾经共同经历过的一件小事,共同看过的一小块风景,共同走过的一条小路,都能随随便便把我陷入一片绝望与悲哀之中。
我问小辫子,“为什么有的人,过了那么久依然不能忘怀。”
“因为爱和有关爱的记忆,”她说,“也许有的时候你所怀恋的并不是那个人,而是和那个人共同度过的那些关于爱的时光。”
那么,我忘不掉的,究竟是他,还是他带给我的那10年的春光明媚呢?
一连几日,毒蛇女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一声不响地把手机电池卸掉。关于我和那个男人的故事,她知道的太多太多,她笃定地认为我对林季阳不会有什么感情可言。她回来,想要重新回到林季阳的身边,她当初可以一声不响地离他而去,却不能忍受他在一年的时间里爱上一个心里装着别的男人的女人。女人啊,都是自私的动物。我不是吗?如果不是,那我为什么不能漠视他们的重逢,为什么?
在我离开培训中心的第四天,我在去医院看望马莉院长的路上遇见了林季阳。他停下车,追上我的步伐,怔怔地站在我的面前,“你又瘦了。”他说。
我想回给他一个简单的微笑,却没办法让自己笑出来,结果只得嘴角勉强牵动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去,“哦。”
他伸出手,又突然停在半空中。我猜他是想捋开遮挡在我眼前的碎发,但他什么也没做,手在半空中僵持了一会儿,沮丧地落了下来。
“这几天你过得好吗?找到新工作了吗?”
我轻摇了摇头,“还没有。”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他用右手抬起我的脸,“别对我说这些,让我看看你可以吗?让我仔细看看你。”
我抬起头与他四目相对,“你没有好好吃饭。”他说,说这话时,他的眼里写满不忍与怜惜。
我掂起脚尖去吻他温热的唇,他颤抖了一下,即而把我紧拥在怀里。全世界顿时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互啄着对方的双唇,他用力箍住我的腰,时间就在那一刻定格,那一瞬就此成为永恒。然后,我哭了。我预感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相拥,我预感在下一秒我们就要分离,从此各奔东西,互不相干。突然之间,我陷在无限的悲凉中无法自拔。我想让他再多抱我一会儿,哪怕只是故意的延缓……
“别哭好吗,小雅?”他用袖管为我擦去眼泪。可我无法抑制自己,眼泪不断喷薄而出。
“别再难为自己了,”他说,“三个人的爱情永远无法达到永恒。放了你吧,你也该放了自己,去寻找你自己的那份幸福。”
我把泪眼贴上他的胸膛不断摩挲着,“别说,什么都别说。”
他轻抚着我的头,“我了解,我什么都了解。毒蛇女已经告诉我一切,我输给的不是他那个人,而是时间,是他给你的10年无法替代的美丽回忆。”
“别说了好不好?”我用力摇着头,我哭得不由自主。
“过几天我就会离开。”
“去哪?”
“随我的父亲回香港。我也累了,也是时候回去了。”
我不知还能对他说些什么,这个男人当初带着对一个女人的无限痴心来到这座城市,如今,却又带着另一个女人给他的伤痛离开。而他却爱得彻底,爱得无怨无悔。
“什么时候走?”
“还没定下来。也许过几天,也许就在明天。”
“这么快?”
他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你不要去送我。”
“为什么?”
“因为即使你去送我,也不会挽留我。”
“你要我挽留你吗?”
“不,不要。”他摸了摸我的头,“我走以后,你要好好的。”
我心如刀割,喉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重重点头,一下,又一下。
我们在马路的尽头分手。从开始,我们就爱得互相牵绊,分开该是最好的结局,还他自由,也还我自由。
“你看起来不是很好。”医院里,马莉院长拉着我的手说。
她看起来精神倒是不错,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双眼也有了神采。
“您看起来不错。”我说。
她笑,“自己的病,只有自己最为知晓。”
“别乱想,您要放宽心,会好起来的。”
她摆摆手,“你愿意听完那个故事吗,孩子?”
“您为什么非要讲给我听?”
“因为它和你有关。关于照片上的那个男人,关于经常到孤儿院做义工的富家女,关于那场车祸,关于生存下来的那个孩童,都跟你有着紧密的关联。”
“可我不想听。”
“你必须听我说,孩子,你知道,也许我剩不下多长时间了,我要向你忏悔,向你的父母忏悔。”
“求您别再说下去。”
“不,”她的声音已经颤抖嘶哑,“你要听,照片上的那个男人不是别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啊,你就是当年幸存下来的孩子,你就是啊。”
“不,这不可能。”我起身在病房里转了一圈,“这怎么可能?”
“我知道很难让你一下子接受这个现实,但我还是要向你忏悔,你的亲生父母是受我的诅咒而死,我是个罪人啊。”
我的脑中开始一片空白,马莉院长的情绪很激动,她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因悲痛而激动的情绪让她无法再继续下去。我坐在她的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请求她不要再说下去。她只是流着泪摇头,苍老的手抚上我的脸颊,“对不起孩子,对不起。”
“那只是一次意外,和您没有关系。”我说。
“可我确实诅咒过你们一家人永远不要幸福,而且不止一次。”
我起身抱住她,“都过去了。”
她一句话也不再说,只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她颤抖得厉害。
从病房出来,我去了一趟医生办公室,马莉院长的主治医生告诉我,马莉院长的时间不多了。
“可她的精神看起来已经好了很多。”我说。
医生叹了口气,“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
我瘫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想到如亲人一般的马莉院长就要离我而去,且永远不再相见,我的心里就如迷途般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