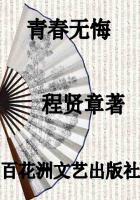马莉院长的病情虽暂时稳定下来,但医生说随时会有危险,我们都明白危险的意思,就是说,她每一刻都有撒手人寰的可能。
“但,她能挺那么久也算是奇迹了。”医生说,“多给她一些鼓励吧。”
我和小辫子久久地相视,重重地点头。
“也许她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所以她才会拼命撑着。”小辫子说。
这天,小辫子的文章获了一个什么文学奖,她举着证书给马莉院长看,她欣慰地点点头,又点点头,那样子像个即将断线的风筝,仿佛稍一放手,她就飞了。那一刻,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哭了,小辫子、马小波、罗西院长,还有孤儿院的几个小孩子……只有我没有,我甚至不曾跟她再说一句话。她示意我坐下来,听她再说些什么,我也只是握着她的手,不断地冲她摇头。最后她紧闭上双眼,让我们都回去。
“马莉院长好像一直都有什么话要对你说。”从病房出来,小辫子问我。
“嗯,”我说,“可能她是寂寞太久了,想找个知心人聊聊天吧。”
小辫子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也许吧。”
其实,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她是想告诉我关于她心爱的那个男人的所有,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当然,还有那唯一幸存下来的小女儿……但,我突然不想再听下去,我怕,我怕听到一些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实,所以我选择逃避。
林季阳来接我,我问身边的马小波和小辫子要去哪里,要不要搭顺风车,马小波轻哼了一声,看也不看我,“怪不得对苏谨朋如此冷漠,原来……”
我不语,小辫子随我上了车,拍拍我的肩膀,“别理他,他就是这副德行。”
可马小波的话,却真的让我动容了。是啊,苏谨朋,那个长相帅气,举手投足都与我的心上人有几分相似的年轻人,如今他在何方呢?是不是已经像我忘记他一样,也把我抛向了记忆的彼端?我不知道。
林季阳把嘴巴轻靠近我,“还生气吗?”
我不说话。他就试探性地把自己的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拿开,握住我的手,然后,一点一点,越握越紧。我气哼哼地把他的手打开。后座的小辫子轻咳了一声,笑了。
下车的时候,小辫子对我说:“小雅,或许,你会比我想象中的更容易幸福。”我站在原地愣住,那一刻,嘴角却流露出那么一抹不自然的笑。
“还生我的气吗?”林季阳从背后抱住我。
“放开。”
“别对我那么凶好不好?”
“放开。”我挣扎着。
“不放,就不放!”
突然就笑了,转头掐他的鼻子,“你会对我好吗?”
“当然,”他伸出右手做发誓状,“我保证,向圣父、圣灵、圣子保证。”
我抓过他的手,捏了又掐,掐了又捏,“真的?”
他重重点头,忽又变得很深沉,“真的!”
“比……还要好?”
“比什么?”他说。
“没什么。”我抱住他,那一刻脑中盘旋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影子。
“你们真的恋爱了?”我在去给林季阳送这一季的招生资料时,在门口听到LISA对林季阳嚷嚷着。
“这是公司,我不想谈论这些私人问题。”
“可你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私人场地,不是吗?”她不依不饶。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这有什么不可以吗?”
我听到她突然不再说话,最后只长叹一口气,“你会后悔的!”
然后她推门出来,撞到门外的我,“走着瞧!”她说。
我走进办公室,把资料放到他的桌子上,转头离去。他站在窗前,凝望着窗外,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EMILY在电脑前探出头来,“喂,晚上有时间没?”
“干吗?”
她眨巴着眼睛,“请你吃饭。”
“为什么请我吃饭?”我说。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吗,同事之间相互请吃饭还需要理由吗?”
我笑。
“怎么样,少陪林经理一会儿,没问题吧?”
我向林季阳的办公室望了望,“去哪吃?”
她笑,“就在公司附近的那家西餐厅。”
“Ok。”我冲她打了个手势,“去就去。”
果然没有白吃的晚餐,刚进餐厅不久,就进来一个挺着啤酒肚儿的中年男人,一进门就急着去摸EMILY的手,她快速躲闪,示意旁边有人。男人见到我,摸着地中海似的脑袋瓜子笑了,“是同事吧,啧啧,也是个美人儿。你们老板可真有福气。”
我不说话,低头摆弄着手指甲。EMILY却突然凑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冲男人仰仰脸,“这是我女朋友。”然后故意提高嗓音,一字一字认真地咬出,“女——朋——友,懂吗?”
男人局促地皱皱眉,“原来你有这种嗜好,那为什么不早说?白白浪费老子的时间。”
EMILY无所谓地耸耸肩,“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吧。”
男人走了,摔门而去。EMILY趴在桌子上哈哈大笑。
我却笑不出,突然有种被人利用的感觉。她把菜单放到我面前,“谢谢你,你帮我大忙了,来,想吃什么随便点。”
我拿起包,“对不起,我要走了。”
她赶忙起身把我拦下,“怎么啦,生气啦?”
“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你这样让我很被动。”我说。
她扑哧又笑出声来,“你不觉得很好玩,很刺激吗?”
“我走了。”我大步向前。
她紧追上来,“好了好了,我的小姑奶奶,我错了行吗?别生气了。”
我皱皱眉,“只此一次。”
她重重点头,“下不为例!”
“其实,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坐下来时,EMILY对我说。
“但这也不是什么好主意啊。”我说。
她摆摆头,“面对这种狗皮膏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能想的办法都用上了。我甚至告诉他我曾经为别的男人打过胎,自过杀,他都无所谓,他说只要他出手,就没有得不到的女人。你说我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笑,“没想到他还是个痴情种子。”
“屁!”EMILY嚷嚷着。我示意她小点声音,她这才放低了语调,“他那是海鲜吃多了,想尝尝青菜的味道。对男人而言,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我说。
“汤姆克鲁斯那样的,又帅又男人。”
我推推她,“你这梦做的可有点儿远。”
她笑着拍我,“其实我也弄不清自己究竟要找个什么样的。找个没钱的吧,小里小气的没个男人样儿,走到哪里兜里都羞涩。找个大款吧,放在家里又不踏实,搞不清哪天就被哪个小妖精勾走了。”
我托着腮帮子听她发表言论,“干吗把感情整得那么复杂?”
“不复杂吗?”她说,“你以为两个人,一条被子,一口破锅就能过日子了吗?”
“如果相爱,为什么不可以呢?”
她大笑,“我保证你是在福堆儿里长大,生活的艰辛一点儿也不明了。”
“那你的意思是,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感情一点儿也不重要?”我说。
“感情固然重要,但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感情迟早会灰飞烟灭。”
我耸耸肩,不置可否。
EMILY说得对,我从小就生活在“童话世界”,一直有一个人为我遮风挡雨。对我而言,他是天。他走了,我的天也便塌了。要么随之塌陷,要么重新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星期天的上午,我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去医院看望马莉院长,我怕见到她,怕从她口中突然听到些什么。有些时候,我也怕见到林季阳,怕自己总是没完没了地拿他和另一个男人比较。
小辫子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有去医院。我说我突然有点儿累。她没再追问下去,而是问起了林季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心高气傲,那时候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我说。
“可他偏偏爱上了你?”
“不,”我否认,“其实,他开始爱上的那个人并不是我。”
“但他现在爱你,不是吗?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过程真的不重要吗?我不敢苟同,在我心里,那些零碎的片段仍在心底最深处闪闪发光,虽然我并不确定是否真的会有我所期许的结果。我突然有些难受,我知道,自己应该把对他的那份情感埋得深一些,再深一些。但我无法做到,他就像我心里的一道缺口,我无法不在意。
小辫子说,“喂,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
其实,我在想他,那么久了,我还在毫无分寸地思恋着他。
那天,我独自在他的房间里坐了很久,天色暗下来,我学着他的样子下楼拉上窗帘,泡一壶咖啡,放一张影碟在CD机里,对身边空空如也的位置说一句:“嘿,今天过得好吗?我的宝贝儿?”然后,我大笑,直至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