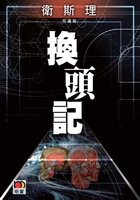1
“生活中的事就像一场剧目,可惜我们都做不成自己的导演。”那天,隔壁住着的女人突然来敲我的房门。贵族犬死了,在一个清晨,突然就没了精神,隔壁住着的女人带它去看医生,被诊断为抑郁症,不久后就死了。
女人的表情有些颓然,“或许有些事情真的是命中注定。”
那一刻,我真想去拥抱她,告诉她,这世间最霸道的事莫过于生生死死,当然,还有分别。而最终,我什么也没有说,而是起身给她倒了一杯蓝山咖啡。那是两天前刚收到的礼物,就是苏谨朋离开的那一天,穿绿色制服的年轻人把它送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突然嗅到了一股离别的味道。我没问苏谨朋那些礼物到底是不是他的杰作,现在对我而言,这一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人走了,他还在我心里,而原本在心上的那些人,却随着时间渐行渐远。
“你一定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惊奇,是不是?”隔壁女人品了一口绿花瓷杯里的蓝山咖啡说。
“老实说,我确实感到惊奇,不过既然你这么做了,就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说。
她笑,“3年了,我把这些回忆藏在心底的最深处,不愿轻易去触碰。”
“总有一些人,一些记忆是无法言说的。”
“比如记忆,比如感情。”她说。
我默默举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咖啡的味道并不十分香浓,久不喝这东西,煮咖啡的功力也到底比他差了那么几分。
“我的父亲,你知道吧?”
我点头,“有名的房产大亨,旗下还有多家酒店、超市连锁……”
她摆摆手,“对于他的风流韵事,想必你也略知一二吧。”
“听说过一点,但听说最多的还是他的小女儿,听说他在几个儿女中唯独对小女儿宠爱有加。外人说,小女儿虽性情顽劣,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羡煞同在闺中的几个娇小姐。”
“那你一定听说,就是这位羡煞旁人的娇人儿,为了一个男人,和她的父亲闹翻,以致离家出走。”
我摇摇头,“这到没有听说。”
“那你有兴趣听听这位娇小姐到底遭遇怎样的情感,又是怎样被一直对她万分宠爱的父亲赶出家门的吗?”她说。
“洗耳恭听。”
她又抿了一口咖啡,“我的情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大学老师,他比我年长20岁,没有什么钱,胡子一大把,可那时候,那样一个男人却对我造成致命的吸引力。我不顾父亲的反对执意要和他在一起。父亲说他是为了我的钱,好吧,我当时就往他的账户上打了几十万元。我对父亲说,凭什么你能用钱包女人,我就不能把钱送给我爱的男人?我说这话时,他的情人就站在我的身边,父亲扬手打了我一巴掌,而这一巴掌把我永远打出了家门。”
“那以后呢?你爱的那个男人呢?”
“他从大学里辞了职,投身股票,很快被股市套牢,几十万元打了水漂,甚至不及听得一个声响。他抱着我说他对不起我,更对不起自己的老婆孩子。我看着他的满头白发,看着他抱头痛哭时眼泪混着鼻涕流下来,突然就觉得有些恶心。我想,我也并不是真的爱眼前的那个男人。”她叹了口气,突然仰头倚靠在沙发上,“只是一场青春的骚动吧。”她说。
“那为什么不回家,只要你低头认个错,你的父亲一定会原谅你的。”
她摇头,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放到嘴边,冲我摇了摇,“不介意吧。”
“抽吧,”我说,“不介意。”
“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爱一个人本身并没有错,也许时间不对,也许爱的人不对,但爱情本身并没有错。”她说。
我点头,表示同意。
“你有没有爱过什么人?”她反问我。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默默地点头。
“第一次遇见你时,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为什么会这么问?”
她笑,“你们彼此注视对方的眼神出卖了你们的心。”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既欢喜又悲凉。如果他爱我,又为何要离我而去,让我独自承受这份孤绝的爱呢?对于我,他是父亲,是朋友,也是情人。但他就是那么轻易地抽身出这样一个角色。而我,却始终无法释怀。
“在想什么?”隔壁女人在我眼前挥了挥手。
“没什么,”我说,“或许爱情真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情,对于我们它既是恩赐,也是惩罚。”
她用夹着香烟的两个手指挠了挠头发,“这话说得真精辟。”
我笑,“那你以后又为何做了那样一个工作?”
“纯粹是帮朋友忙而已,那片子的女主角是我的好友,刚刚成名,怕脱完影响自己的玉女形象。”
“于是你就挺身而出了?”我说。
“我觉得,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后来呢?”
“后来好友红了,而我觉得‘裸替’也是个极有意思的差事,其实人生不过是赤裸裸的几十年,只是有人遮遮掩掩,有的人一目了然罢了。”
“所以你选择了一目了然。”
“不,不是我选择了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我。”她说。
我歪头看着她,“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全然不是房产大亨宠爱的娇小姐。”
她笑,“事实上,我现在已经不是了,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刹那,所有一切都化为零点。”
“你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子。”我说。
“你也是。”她说,“自从那次在我生日派对上见到你,我就对你的印象特别深刻。感觉这个小女孩像个小精灵,而你身边的男人就像阿拉神灯里的巨人,你们该是童话故事里最奇妙也最幸福的组合。”
我轻笑着在沙发上蜷缩成一个句号。我无法对她诉说,她眼里的那个小精灵,现在早已被一段时光打磨得没了棱角。如今,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她甚至不能选择,也无从选择。如果有一天,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归于破灭,我不敢保证这个精灵会不会就此崩溃。
电话响起来,是林季阳。他用异常沉郁的声音说:“欧阳依雅小姐,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份工作了?”
隔壁女人起身冲我笑了笑,“我也该走了,很高兴和你聊天。”
“你还会再来吗?”我抚着听筒对她说。
“会的。”她说。
然后我们摇手道别。
“我有权利辞退一个旷工长达一周的员工。”林季阳厉声厉气地说。
“用我打一份辞呈吗?”我说。
“喂,我在很严肃地跟你说话。”
“我也在很严肃地回答。”
“我现在只想问你,明天到底来不来上班?”
“来!”我答得干净而利落。
他这才笑了,“那今年的年终奖金也彻底泡汤了。”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
“我对待员工一向一视同仁。”他说。
说完,我们都笑了。被人关怀的感觉真好,我想。
小辫子说得对,忘记一个人的感觉就像重生。我不知道我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重生,一年、五年,还是十年?我不确定。但我愿意尝试。如果他已把这份感情抛于千里,我为什么不能呢?
转天,我回培训中心上了班,EMILY见到我时,张大嘴巴把我拉到一边,“我的上帝啊,你可算来了。”
“对不起,”我说,“让大家担心了。”
她摆摆手,“最担心你的还是林经理,他一天往这里跑好几趟呢,就是看你有没有来上班。”
我笑,“找机会我会谢谢他的。”
她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我的冷淡态度挡了回去。如果没有毒蛇女,如果我的心里不是居住着另一个男人,我想我愿意去喜欢一个像林系阳这样的男人,青春帅气,阳光明媚。但,如果只是如果,总有一些事情不接受我们的控制,比如情感。
负责新员工培训的是一个有些发福的中年女人,说话时眉毛总是轻挑着,一脸严肃的褶子。那天见到我,把我从上到下一通打量,好像要一下子把我看到骨子里。我点头抱以微笑,她冷冷地仰仰脸,示意我找个位置坐下。
那天培训结束后,她把我叫住,用英语问了关于我的一些情况,我很认真地一一做答。临了,她摇头说,“你出现了好几次语法错误。”我竟笑了,我说:“外国人说话的时候也不见得时时讲语法,处处谈逻辑。”
“你是外国人吗?”她说。
我摇头。虽然对她这种较真的冷淡态度没什么好感,但还是低头对她的话表示了默许。
EMILY对我说:“你可不要小看她,前两年她在大学里教书,可是那里叱咤风云的人物。”
“那她又为何来了这里?”我说。
她愣了愣,欲言又止,“以后你就知道了。”
中午我和林季阳一起吃了饭,当我问及培训的那个女人时,他也是多躲躲闪闪,一副誓死不说的架势。恍然间,我觉得,这个培训中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再次到医院看望马莉院长时,小辫子拿给我一幅画,“苏谨朋让我转交给你的。”她说。
我打开看了看,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向他索要的那幅画。心里不禁百转千回。小辫子拍拍我的肩膀说:“这回,你并没有做错,不爱他就不要给他希望,暧昧对他更是折磨。”
可是我,为何心里会隐隐作痛?
其实,分手的那天,我是想对苏谨朋说,“别走,留下来。”可是我没有勇气,我指责自己心里想着一个男人却想让另一个男人留在我的身边。
小辫子对我说:“离开是最好的解脱。”我不语。她接着问我:“苏谨朋走后有没有联系过你?”
我把左手举起来,摆了摆,把脸深埋在右手掌心上,我说:“你让我静一静,我想好好想一想。”
我听见小辫子调侃着说了一句,“你现在这副样子,像刚刚失去恋人的小女人。”
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那一刻,眼泪就是那么悄然地从右手五指间点点溢出。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
一连几天,心情突然低落到谷底,给我们培训的中年女人一次又一次敲着桌子提醒我要精神集中,可我无法集中,脑中一直有两个影子在交替奔跑,我感觉疲惫极了。
有天她把我拉到经理室里,指着我的鼻子对林季阳说,她无法忍受我这样的学员,并强烈要求公司把我辞退。
林季阳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给LISA老师道歉。”
我不说话,甩门离去。
EMILY在公司附近的那家餐厅里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雅呀,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帅的女孩儿。”说完冲我挑起了大拇指,“牛,真是太牛了!”
我独自杵着面前的那盘牛肉盖饭,“但愿是在夸我。”
“喂,”她突然探过头来,“老实说,你是不是根本不在意这份工作?”
“谁说的?不在意为什么还来参加这该死的培训?”我说。
EMILY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可是我觉得你一点儿也不在意,刚来公司就请假一周多,参加培训又与培训老师产生矛盾,在老板面前还拒不道歉,更重要的是,你惹的不是个简单女人,她是……”
“她是什么?”
她欲言又止,“算了,反正你这次麻烦可是不小,就看林经理怎么处理了。”
“那个女人有什么特殊的吗,看样子比老板还嚣张?”我说。
EMILY点着头,用手指了指我,“算你说对了,不过这里面的事情,你还是少知道为好。”
我看着她,突然感觉这个20几岁的女孩仿佛一时间历尽沧桑。
EMILY说得没错,我这次的麻烦确实不小,林季阳把我叫到办公室的时候,表情严肃极了,“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他说,“第一,去给LISA老师道歉。第二,打份辞职报告上来。”老实说,林季阳的态度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曾想过自己把辞职信甩在他的办公桌上,大步向前,他会张口挽留,而我会理也不理。那样,才符合剧情的发展。可是他没有,语气甚至决绝的另人心寒。
“我选择前者。”我说。
他愣愣,眉宇间仿若有什么东西突然被舒展开,“你确定吗?”
我轻点了点头,“确定。”
“其实只这间大厦就有好几家不错的公司,如果你需要,我可以……”
我伸手摆了摆,“我去给她道歉。”
从林季阳的办公室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沮丧极了。如果他在我身边,他一定会替我安排好这一切的种种。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向任何人低过头,可是马上,我要向一个自己十分讨厌的高傲女人低头认错,心里不禁百转千回,五味杂陈一时间在心里泛滥成灾。
“你原本可以不做这种选择,反正你也不靠这份工作来糊口。”EMILY对我说。
“事实上,我真是靠这份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的。”我说。
她半信半疑地望着他去年买给我的名牌衣服,“你真会开玩笑。”
我不再解释,也无从解释。事实上,我确实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林季阳的话没有那么决绝,我想我会潇洒离开。可是这次是别人让我走,我就偏要留下来,是生气,也是赌气。以前,他曾说我是那种倔犟到自己为难自己的孩子。这话一点儿不假。
女人显然并不理会我的道歉,凛冽的目光射到我的身上,然后她突然起身捏住了我的肩膀,“别想跟我斗!”
我浑身猛地震颤,这女人的眼里冲满不屑与憎恨,我说,“我不想,也不会跟你斗,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拿好自己的钱,仅此而已。”
她冷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林经理年轻,容易被你这样的小狐狸精迷惑,可我不会,我会看紧你,你别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有什么动静。”
我突然想笑,“您凭什么来威胁我呢?凭你是我的老师,还是凭你脸上比我多几条皱纹?”
“凭我在这里的地位!”
我笑着摇头,“凭你勾引大老板赢来的地位?”
她愣住,即而狂吼道:“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摆摆手,“按照林经理的吩咐,我歉也道了,理也赔了,在今后两个多月的培训期间您还是我的老师,除此之外,我们互不相干。”
她再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也不想听,大步从她办公室走出来。窗外,云淡风清,举目望去,风景各边都好。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刷了卡,下班。
EMILY问我,“你是怎么把她搞定的?”
我耸耸肩,“摆事实,讲道理呗。”
其实,即使大家不说,我也能猜出几分这女人和这所培训中心的些微联系。从见到她的第一天,我就查出了她的一些经历,当然,包括并不怎么光彩的那部分。这些都是他教我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从公司走出来,我仰头望着刺眼的阳光,直到被阳光照得淌出泪来。“谢谢你。”我在心底轻声说。我不知他在何方,我仰望天空,云在走,它能把我的话带给他,我坚信。“是的,谢谢你。虽然你离我而去,但是你教会了我如何生活,如何应对现实生活里的种种困难。原本以为你给我营造了一个童话世界,其实,在童话世界里你就已经教会我如何生活。”我双手合十,在马路边上凝望着来往的人群,把这些话默念给他,也是默念给自己听,给那个已经开始试着接受,也试着尝试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自己听。
这天下班回来,我又遇见了隔壁住着的女人,她似乎生病了,脸色极度苍白,嘴角起了血泡,说话的时候嘴唇轻抖着。
她冲我笑着,“我想我该跟它一起走的,虽然它只是一条狗……”
我把她请进屋里,拿来药箱,那里面的东西,还是上次穿绿色制服的年轻人送来的药品。
“只为了一条狗?”我说。
她笑着,脸上却异常暗淡无光,“于我,它更像一个亲人。但我不配做它的亲人,自己的亲人患了严重的抑郁症,我却全然不知晓,直到它死……我有什么权利说自己是它的亲人?”
“你的菲佣对它很不客气,”我说,“也许离开,对它来说是一种解脱。”
她点头,“是我太自私,我的心里还是会痛,还是希望它活着,即使抑郁,也要活着。”
我望着她,突然想给她讲讲我和这座别墅的男主人的故事,关于爱、关于离别、关于想念……但我并不确定她会喜欢这么一个陌生冗长而又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故事。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明白,任际遇如何的相似,也终不能收获相同的苦涩。
我们蜷缩在沙发上看前几年的贺岁片,她的唇角始终带着淡定的笑,我却不敢看她,我的脑中开始一片混乱,或是一片空白。
其间,我接到林季阳的电话。
他说,“你今天还好吗?”
“不好。”我说,其实我知道他是想问那个叫LISA的女人有没有为难我。
“我在很认真地问你。”他说。
“我也在很认真地回答你。”我说。
“喂,不要跟我耍小女孩的脾气。”
“喂,你也不要跟我端老板的架子!”
他笑,“别这样折磨我。”
我也冷笑,“你可以不接受我的折磨。”
隔壁的女人把目光从电视机上离开,转头望了我一眼。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冷静,冷静,少安毋躁!
“我去找你,现在就去。”他说。
“不,我有客人。”
隔壁女人向我摆摆手,示意她要离开。我单手把她按住,冲她眨了眨眼,她这才重又坐了下来,把目光又投向了无聊的贺岁片。
“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去参加培训了。”林季阳接着说。
“不,”我说,“我凭什么要搞特殊化,就凭我认识那里的小老板吗?”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做你该做的,做一个经理该做的。在公司,你是老板,我是员工,就这样。”
“那好吧,”他说,“希望你开心点。”
“我会。”我说。
电话挂断,我坐在沙发上,想象着林季阳在电话那边无奈的样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像妖精一样的女子。”隔壁女人突然转头对我说。
我把和那个叫LISA的女人的故事讲给她听,她笑着对我说,“真有你的,你就不怕她报复,把你挤兑出公司?”
“因为我知道她和大老板的关系吗?她不会。”我说。
“你就那么肯定?”
“当然,她和大老板私通虽然已经是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但她怕我把更大的秘密抖落出去。”
“事实上,你会这么做吗?”
我摇头,“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更大的秘密,虽然直觉告诉我一定有这个秘密。”
她笑,“妖精!”
我也笑,“你知道吗?做过贼的人都有不能避免的心虚,我大上学时曾看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男人杀人逃亡12年,在这12年间他从没睡过一天好觉,直到被抓的那天,他才解脱。那个女人害怕的不是我,而是埋藏在自己心里的肮脏。”
“嗯。”她点点头,“这话说得不错,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愿为人所知的阴暗面。”
我耸耸肩,想转个话题,“那后来,在大学老师之后,你就没爱过别的男人了吗?”
“当然不是,前段时间还遭遇了一场爱情,很激烈,也很绝望的爱情。”
“你愿意讲给我听听吗?”我说。
她笑,“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好吗?”
我点头,“我明白。”
“他是我第一次拍裸戏的那个导演,依然是有妇之夫。呵,有时我就在想,都说女人有猫性,何为猫性?就是总盯着别人家里的腥。在这一点上,我鄙视自己。”她挪了挪身子,把目光随意落在客厅的某一个角落,“可我希望跟他在一起,哪怕是偷情,我喜欢缠着他,然后一直偷情到齿摇发落。”
“他对你呢?”
“女人属猫,男人却属狗。在与我缠绵了几个回合下来,他突然向我忏悔,说他对不起老婆孩子,甚至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八代,只因跟我在了一起。”
“然后呢?”我说。
“离开吧。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谁都知道他看上了我的那个不愿意在镜头前暴露自己身体的好友,他没想到她竟红了,他成全了她,她是该为他做点什么的。而对于一个甘愿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赤裸身体的女人,你觉得他还会有什么惦恋吗?”
我心里突然酸酸的,却只是沉默无语。她明知道男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但她不拆穿,她成全他,不挽留,连一句话也没有。她说,当一个男人的心已不在你的身上,再多的哀愁又该如何呢?在他眼里仍会一文不值。
“很荒唐是不是?”她问我。
“你真傻。”我说。
其实,我知道她不是一个不会争取爱情的人,她是太疲惫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好友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如胶似漆,她做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开,亦是放弃。在三个人的剧目中,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她选择默默离开,所以我说她傻。但她离开也是好的,她飞蛾扑火般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而那些幸福是他没法给她的。
“会有更好的。”她说,眼里充满落寞的希望,“即使生活欺骗了我一百次,我也相信会有一百零一次的真情。”
“会的。”我说,“只要你相信。”
电视屏幕上,女主角对花心男朋友说:“爱情本来就是件冒险的事,但为了你,我甘愿冒这场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