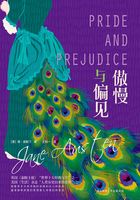也曾想过再次见到苏谨朋时,该是在何种场合,而又该如何使自己看上去自然一些。但,万没想到再见面会是那样一种情景。
“马小波疯了,他疯了……”听着小辫子在电话那边哭得泣不成声,我拿着手机飞奔出去。头没来得及梳,一头愤怒的长发在风中肆意张扬着。司机不无担忧地问:“您没事吧,过了前面的路口就是警察局。”我拍着坐椅高吼着,“谁要去警察局?”司机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
来开门的竟是苏谨朋,我抚住由于跑着上楼而不能均匀呼吸的胸口,愣愣地说不出话来。
“你瘦了。”他闪身让我进去,然后在我身后吐出这么三个字。
我怔了怔,挺直腰,走进了屋里。
马小波住的是一间不大的地下室,由于潮湿,房子里的墙皮已经掉了一半。前段时间听说他要存钱,预备在地上买一套房子,那次还半开玩笑地说,一定要住最高的那层,在地下窝屈得太久了,要到云上去呼吸一下。然而,这一切的想法都建立在和小辫子的婚姻上,是的,他是想要和她结婚的。有时候人也是一种极其奇怪的动物,他爱小辫子,但却不能接受她的那些往事,不断地怀疑与猜忌,终于形成了那次的大爆发,喝了酒,跑出去,出了车祸,小辫子也正式跟他宣布拜拜。他说他会等她,等到她回心转意那天为止,就像她当初一如既往地等另一个男人一样。然而,时间可以抹去一段记忆,但却不能消灭一段历史。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会像虫子一样厮咬着他,他会和她再争再吵,最后还将是一样的结局。
苏谨朋用脚踢开我脚下的酒瓶子,找了个垫子让我坐下来。我才发现,这狭小的空间里,根本没有一个能落脚的地方。酒瓶子横七竖八地倒着,满屋恶臭扑鼻而来,让人做呕。小辫子在角落了蜷缩成一个“Z”形,马小波则跪在她的脚边,用手抓挠着头发,一下一下捶打着。她不理,只独自流眼泪。
我走过去,想去扶起马小波,可他用力甩掉我的胳膊,瞪大的双眼冲满血丝,“走开!”
“喂,小波,别对女人动手。”苏谨朋吼着。
我摆摆手,“算了。”跨出一步去搀扶起小辫子,“我们走。”
“你不能走。”马小波暴怒起身,揽住了小辫子的胳膊,“你给我说清楚。”
“你还想听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们完了,”她抽泣着,“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吧。”
“为什么?为什么?”马小波的情绪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还是因为那个男人对不对?他来找你了?你就想把我甩了,对不对?”
“不对不对,你看,你总是这样猜忌,我很累,很累,你懂不懂?”
“我那么爱你,你他妈懂不懂?”
“你爱我,但你爱的是眼前的我,你不爱我的过去,你不能爱我的全部,而那些往事是我不能改变的事实。既然这样,我们就散了吧,散了好吗?求你。”
他怔怔地望着她,突然不再说话,双手从她的肩膀滑落,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她抬着头,不去看他,兀自用手抹了抹眼泪,拉上我大步向门外走去。
是的,眼泪早已夺上了我的眼框,马小波孤绝的面孔,看了让人心疼。临走时,苏谨朋追出来,拍了拍小辫子的肩膀,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而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对我,“你瘦了,你该多吃点。”我没说话,扭头紧紧握住小辫子的手,原本努力抑制住的眼泪就那么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你说我做得对吗?”深夜1点钟小辫子突然推开我的房门,哭着扑倒在我的床前,“我真的好难受,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对他?”
我懵懂地睁开眼睛,大脑里还回顾着刚才在梦里的那一幕,他终于回来找我,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你?”我摇头,哭着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求你留下来好不好?”
然后是巨大的震颤声,我努力睁开眼,是小辫子扑倒在我的床边。
“怎么啦?”我说,“怎么还不睡?”
“我胸腔难受得快要死掉了。”她捶打着自己的胸口说。
“别这样,”我握住她的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你不是说过,让他失望比给他希望对他更好吗?”
“可我没想到他会那么歇斯底里。”
“总会过去的,那些我们不愿留在记忆中的东西,总会过去的。”我说。其实,我是想说,这次的分手也许会给他造成一个永远不可愈合的伤口。然而,我却没有说出口,是不忍说出口。
清晨,被闹钟第二次吵醒的时候,我惊叫着坐起身,慌忙换了衣服,整理了一头零乱长发,冲出门去。刚开门恰好和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撞了个满怀,见到我,他先是一愣,既而笑笑,冲我挥挥手,“嗨。”
“嗨,”我说。
“您的包裹,”他冲我指了指手里的包裹。
“哦,好,签名对吧?”
他笑着点点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到他洁白的牙齿上,让他看起来像个干净的大孩子。
我是在去培训中心的公交车上打开的包裹,是一盒点心,不同口味,一一排列整齐。不同的是,这回却多了一张打印字条:多吃点,不许减肥。
那一刻,我脑中首先闪出的却是苏谨朋的影子。想到他昨天的话语,想到连日来收到的“礼物”,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喂,鼻涕虫,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只想问你苏谨朋在不在你那里?他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
“难道你没听清我的话吗?我心情不好,别来打搅我。”马小波在电话那边怒吼着。
我也只好挂了电话,马小波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来来回回只会说那两句话——我心情不好,都他妈甭来打搅我!
其实找到苏谨朋又如何呢?直接问他那些一直让我倍感温暖的礼物,到底是不是他的杰作?如果真是他所为,那么,我是该喜还是该悲呢?不不,一定不是他,他不会那么了解我,只是见过几面的陌生人,他也不会对我那么用心的。这样劝慰着自己,心里却翻江倒海的难受。
“我的天哪,你的感冒还没好吗?”EMILY刚进办公室就冲我嚷嚷着,“怎么跟打持久战似的呢?”
我笑,“感冒兄稀罕我。”
“你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吃药打针输液全方位打击它。”
“该采取的都采取了,我现在彻底举白旗了。”我说。
“喂,”她神神秘秘地凑近我,“不如谈场恋爱吧,听说恋爱可以治疗感冒呢。”说完,她扬了扬小脸。我扭头看到林系阳正朝这边走过来,于是冲她皱了皱眉,“去你的。”
“怎么样,战胜病魔了吗?”林系阳把一沓文件放到我的桌上。
“怎么说得跟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一样。”我嗔怪着。
他马上举起双手,“我的大小姐,我可没那个意思。”
EMILY从自己的办公桌向这边探出头来,露出狡黠的笑,“林经理那是关心你呢。”
“听见了没,还是群众的呼声最动听。”他得意地冲我扬扬脸。
我瞥了瞥嘴,“您有什么吩咐吗?”
“当然,这些文件需要整理一下,把历年的学生情况编好号输入电脑里,没问题吧?”
“交给我吧,”我说。
“喂,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林季阳走后,EMILY又从办公桌那边探出脑袋来问我。
“我听到你刚叫他林经理。”
“不是,我不是在说这个,难道他没有跟你说过他的身世吗?”EMILY显然摆出了十足的三八主义精神。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我说,“以前也只是普通同学,他是什么身世凭什么要告诉我。”
“你真的不知道?”她半信半疑地问。
“不知道。”
“告诉你哦,我也是听大楼里其他公司里的人讲的,说林经理是一个香港富商的儿子,这个培训机构不过是他老爸旗下的一个小分支,”她说着伸出小拇指比画着,“毛毛雨而已。”
我摇头冷笑,“你好像对他格外感兴趣。”
“何止是我,整栋大楼的女人,下至未成年,上至老年,哪个对他没兴趣,十足的钻石王老五耶。”
“瞎说,我就没见过这里招过未成年。”
她摆手,“哎呀,别较真好不好?反正他是魅力无法挡,也就你不拿人家当回事儿罢了。”
我不语,低头去翻看林季阳刚拿过来的资料。谁知她竟又凑了过来,“喂,别说我不提醒你,像送资料这样的小事,至于让堂堂一个总经理来干吗?他还不是想来看看你。”
我笑,“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只想说,我们只是朋友,现在是,以后也不会改变。”
她耸耸肩,“当我没说。”而后悻悻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
翻着手里的资料,我就在想,如果EMILY知道毒蛇女的存在,如果她知道这个在别人眼里不可一世的林大经理曾为一个女人伤心欲绝,那么她该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