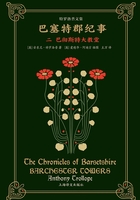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每抽一丝便硬生出一分疼痛。在床上躺了两天,这天,等到了中午,还没收到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送来的“礼物”,心里突然就增了一分落寞。才发现,这段时间完全是这些礼物拂去了我身体里滋长出的那份寂寞和伤感。
也许小辫子说得对,我是该有一份寄托,过自己该过的生活。
人才市场的人头攒动,像个超级大市场。本来是想来这里找份工作,可刚下了计程车,我就打了退堂鼓。始终还是无法完全适应太过嘈杂的环境,早已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那时候,单单看看游走的云变化着各种图案,心里都会多一分甜蜜。
我试着随人群到各企业的招聘牌前推销一下自己,可嘴巴张了半天,一个字也发不出。还好,中途接了小辫子的电话,让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尽快离开这里的理由。
“病还没好,怎么就四处跑?”她在电话那边责怪着。
“只是想出来走走,你说的,要多晒晒太阳,换换空气嘛。”
她笑,“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乖了?”
“一直如此,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
“行了,你要不要赶紧回来,我刚到,有你的特快专递。”
突然间,我感到心情莫名的舒畅,困倦的身体里的所有感觉都被打开了一般。“快帮我看看,是什么?”
“不是包裹,只是一个小小的粉红色信封,要打开吗,还是你自己回来再看?”
“打开,快。”我有点儿迫不及待。
“是一张打印出来的字条,”她说,“等等,我帮你看看写的什么内容。ST培训中心……喂,小雅,是一个培训中心的地址。”
我笑,“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在哪里?”
“在人才市场。”
我听到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音,沉了几秒钟,她说:“小雅,难道真的有先知?”
我却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他就在我身边,我猜。想到这,我迅速挂断了电话,踩着快乐的步伐,大步朝回家的方向跑去。
“不行,你一定要给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辫子把我按到沙发上,一副不让我坦白交代决不罢休的姿态。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是一种预知。”
“真的能预先猜出你的想法,这也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吧?”
我耸耸肩,“事情就如你看到的那样。”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看她的样子似乎对这件事饶有兴趣。
“很早以前。”我说。
“那就是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神秘人是谁?”
我低头去拿茶几上的信封,“知道又能怎样?”
“我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这些年的生活,似乎突然在我头脑里形成了断档。”
“你就记住我依然是十几年前和你一起跳皮筋,和你一起抢糖纸,和你一起打,一起闹的小雅,这就可以了。”
“那么,你要不要去这个地方看一下?”她指着我手里的信纸。
“为什么不去,是该找份工作了。”
“祝你成功。”她说。
“一定会。”我说。
那天,我按照信纸给出的地址找去,在一幢摩天大楼前下了车,意外的是,竟看见了林季阳。有段时间不见,他变了,西服革履,神采飞扬。看样子已经从毒蛇女离开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他向我快乐地打着招呼。我回以简单的微笑。
“你来这里是?”
“应聘一份工作。”我说。
“这栋大厦里有好几家公司,你应聘的是哪家?”
我拿出信纸给他看,“喏,就是这一家。”
他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光亮,“这家不错,祝你好运。”
“谢谢。”我说。
没有过问彼此的生活,没有过多的寒暄,就如久未相见,已经忘却彼此又恍然想起的故人,见了面,点点头,笑了笑,然后擦肩而过。
来应聘的人不多,也不算少,十几个人在会议室的皮质沙发上相对无言。然后,依照顺序一一进入一间镶着“主任室”字样的房间。轮到我时,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在这期间,我从包包里掏出一本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厨房,”是讲一个少女在失去所有亲人后,只有在厨房的冰箱旁才能安睡。想到自己那些辗转反侧,无法安眠的日子,到底何处才是我的安乐所在呢?这样想着,被一个身穿深蓝色套装的女孩的轻声细语拉回了现实,“欧阳依雅小姐,您可以进去了。”
主任室布置的格调很简单,墙上只挂着一个大大的“忍”字,桌上是半盛开着的百合花。
主任室里一共坐着三个人。“欧阳依雅,”其中一个人念着我昨天刚刚传过来的简历。另一个人用英文跟我做了简单的交流,中间坐着的那个人却始终一言未发。其实,从一进门,我便一眼认出,那是林季阳。
我是接受面试的最后一人,临了,林季阳叫住我,“一起吃个饭吧。”
我点头,欣然答应。
“我恋爱了。”在饭桌上,他突然对我说。
“恭喜你。”
“可就在见到你的前24个小时里,又分了手。所以才决定参加这次的面试,试图寻找一个让人舒服的面孔。”
“找到了吗?”
“当然,如果你算其中之一的话。”
“你还是老样子,”我说,“不过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这次的失恋显然没给你过大的打击。”
他笑,“我现在养了一只小猫,只要一回家,它就会腻到我的脚边,都说女人像猫,我到觉得猫比女人温顺得多。”
“所以,你现在和那只小猫相依为命?”
“对,你呢?你在跟谁相依为命?”
我怔怔地望着他,答不出来。
我们在餐厅外分了手,我走在熙攘的人群中,终于想到,与我相依为命的是回忆,是离我远去的他给我的回忆。
回去的路上,我想到了那天晚上,我因为一件小事跟他大吵,他不说话,我就硬把他推出大门。夜了,我在别墅的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孤灯下,心里突然就湿了。我觉得我有一天将会失去他,而且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突然想念很多离我而去的人,也许命中注定我将孤单一人,或喜,或悲。
掏出手机,一遍遍翻看着电话薄,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熟识的人竟少之又少。在毒蛇女的名字上,停了片刻,明知道不会有任何反应,还是播了过去。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是?林季阳?”我试探性地问。
“是小雅吧。”他说,语气温和而平静,却透着几分落寞。
“嗯,是我。你怎么会用她的电话号码?”
“那天我去宿舍找她,发现她已经走了,我在她的桌子上发现了这张手机卡,于是交了费,一直装在另一个手机里,随身带着,想到也许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些什么,哪怕只是一个电话号码,我也希望回应她的不是一片寂寞和冰冷。”
心里突然就泛起了一片潮湿,“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我问他。
“也许吧,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本来就很傻。”
“可你知道吗?”我突然很想把毒蛇女和他家里的所有恩恩怨怨全盘告诉他,可最后还是忍住了,就让善良的人继续善良,让相信爱的人继续相信吧。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我说,“今天见到你,觉得你瘦了,或许你该多吃点好吃的东西,比如今天我们去的那家餐厅的食物就不错。”
“是吗?”
“嗯。”
“都说食物会让人忘却一些不开心的记忆,你觉得呢?”
“那么你遗忘什么了吗?”我说。
他不说,只干涩地笑,“那么你呢?有没有忘掉些什么?”
“没有,”我说,说完我们都笑了。
总有一些事情,即使相隔遥远,也难忘怀,因为它早已深入骨髓。那么,我所思念的那个男人,在某一个我未知的角落里,也会如此思念我吗?
“怎么了?”林季阳在电话那边突然对我说,“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如果有机会,我想经常去那家餐厅吃东西。”我说。
他笑,“放心,以后这种机会甩都甩不掉,你还不知道吧,今天给你面试的几个人都说你不错,这份工作你势在必得。那样,你每天都可以去那家餐厅吃东西了。”
“真的?”
“真的。”
“谢谢你,”我说。
“与我无关,这是你自己的所得,我可是公私分明的人。”
“还是要谢谢你。”
“那就请我吃饭吧,”他说。
“嗯,顺便带上你的猫。”
“你也喜欢猫吗?”
“不,很不喜欢。”我说。
记得那年他带回来一只猫,半夜我被猫的叫声吵醒,起身敲响了他的房门,命令他把它弄出去。他看着我,很无辜地对我说,“我以为你会喜欢。”
“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见它了,”林季阳叹了口气,“我希望它见到的都是喜欢它的人。”
我就笑,觉得他其实也不是我一直认为的花花公子。这个电话让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就像炎热的夏天,猛地灌上了一杯冰水,心里顿时敞亮了许多。
临了,我问他,“如果有天毒蛇女回来了,你会怎么对待她?”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我知道现在要好好过日子,以此来报复她,让她回来的那一天,为当初抛弃我而痛苦。”
“祝你心想事成。”我说。
挂了电话后,我在想,也许我也该好好对待自己,打起精神来,让他回来的那一天,为突然离我而去而痛苦。是的,我也要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所以,我必须好起来,越来越好。
“是不是不喜欢那份工作?”回到家后,小辫子问我。自从我生病以来,她就暂时搬到别墅来住,这样也好,起码说话的时候诺大的房子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回音。
我瑟缩在沙发上,问她,“你知道如果想报复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好好对待你自己。”
她先是一愣,而后眼眶里涌出泪花,“对,你说得对。”
“我突然想去看看马小波,”晚饭后,她突然对我说。这晚的晚饭是玉米粥,很清淡,全然不是她的口味。
“为什么?”我说。
“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他过得好不好,你还会关心吗?”我那么直接地质问她,似乎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小辫子,而是其他什么人,离开了,却又不曾相见的人。
“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他过得好。”她说。才发现在她眼里写着的不只是冷漠。
“如果他过得不好,你会回到他的身边吗?”
她不语。
“那么,如果他过得好,你会后悔吗,会为离开他而痛苦吗?”
“不会。”她说,“因为我不曾爱过他。”
终于明白,原来,会记恨,会悲痛,全因爱过。
窗外,明月高挂。我独自站在玻璃窗前,凝望别墅前的那盏孤灯,想象他在那里徘徊的样子。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对我说他不曾为离开我而悲痛,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对不会!
不知是不是因为感冒没好就跑出去应聘工作,往后的几天,感冒突然加重,身体也一直不舒服,每天的“礼物”变成不同名称的感冒药。小辫子嘱咐我,最近不要四处乱跑。我就吃着那些感冒药,站在落地窗前看月亮一天一天地沉下去。恍然发现,原来,感冒也是一种极为伤感的病。
在应聘工作的第三天,我接到了ST培训中心打来的电话,“欧阳依雅小姐,您被录取了,请问您什么时候能够过来工作?”
我咳嗽着,“再等几天可以吗?我正在感冒。”
对方笑了,但听得出,笑得有些不大情愿,“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她大概不知道,感冒不仅让人伤感,也容易让人意志消沉。
那晚的梦里,我和他吵架,长大的我总是那么无理取闹,他转身欲要离去,我突然拉住他的手,他转头,我却又放了手。他走了,头也不回。我蹲在房间的一角,把自己蜷缩成一个句号。然后他突然推门进来把我抱起。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我说。
“谁说的?”他为我捋去额前被泪水沾湿的几缕长发。
“那你为什么走?”
“怕站在你面前,你会更生气。”
“又为什么回来?”
“怕你害怕,天黑了,你从小就怕黑。”
我就哭了,哭得汹涌,把头枕在他的胸口上,“我以后再不胡闹了,不要离开我,我真的会怕的,真的会。”
他把我的头搂得很紧,“傻瓜,不许你再胡思乱想。”
我睁开眼睛,躺在床上,头已经不那么痛了,而心,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蜷缩着,不得喘息。我用被子死死裹住自己的头,他说过,半夜醒来首先要检查自己是否盖好了被子,那样,即使他不在我身边,他也会放心了。只是,我当时并未放在心上,他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我绝对不允许他离我而去。而今,剩我独自守着这空荡的房子,才发现,我们始终隔着一个天涯。
转天,我在早晨8点到ST培训中心报到,也许时间尚早,那里除了做卫生的清洁阿姨,空无一人。我靠在玻璃门外,张开嘴巴,独自喘息。是的,我的感冒还没有好,但我需要出来走走,小辫子说得对,我不能靠那些回忆消磨掉以后的那些暗淡时光。
清洁阿姨问我,“你是来报名的吗?”
我摇头,“我是来工作的。”
她愣愣地看着我,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你看起来还那么小。”
“过了这年,我就23岁了。”我说。
她笑,“年轻真好,我老了,看到年轻的面孔就格外的羡慕。”
我也笑,想到去年,他生日的那天,摸着我的头对我说,“我的小雅长大了,我却老了。”
生日,我赶忙从包包里掏出手机,翻看着上面的日历。12月20号,原来,还有5天便是他的生日。
9点的时候,培训中心的人陆续到齐,穿蓝色套装的女孩快乐地向我打着招呼,“感冒好了吗?欧阳依雅小姐?”
我笑,原来她就是昨天打电话给我的女孩子。
“没有完全好,但我想已经可以工作了。”我说。
她笑着伸出手,“我叫EMILY。”
我也伸出手,“欧阳依雅。”
“你真是敬业的女孩子。”她说。
我苦笑,她不知道,其实工作也是治疗伤感病的一种方法。
我的工作很简单,整理一些资料,整理一些往年的学生档案,EMILY说我首先应该熟悉一下这里的工作环境,然后还要经过三个月的培训。我点头,其实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治疗那种叫做伤感的病。
中午还是去的那家餐厅,这次却是独自一人。原来这家餐厅是可以点曲的,听服务员说,坐在钢琴前的那个中年妇女是个残疾人,高位截瘫。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一定经历过一场痛彻心扉的爱情,她爱的男人离她而去,而她会因为伤心过度从高楼跳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您要点首曲子吗?”胸口寄领结的服务生问我。
“能点《安魂曲》吗?”
服务生愣住,“嗯?”
我笑,“不用了,谢谢。”
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错误的。就在我要离开餐厅的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坐在弹钢琴的女人的对面,看着她,面露安详的笑。
我叫来服务生,埋了单,轻声问他,“坐在那边的男人是这里的常客吗?”
“对,他和她是一家子。”我见到他的手,指着的是弹钢琴的女人。不禁摇头失笑。
出了餐厅大门,一阵寒风袭来,感觉周身一阵冰冷。轻轻伸手紧了紧大衣,想象着刚在餐厅遇见的那个男人用轮椅推着弹钢琴的女人,走在夕阳西下,也不失为一件十分浪漫的事。
我用午休的最后半个小时逛了一家内衣店。今年,我送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套保暖内衣,尽管我不确定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是否能穿上,但我还是买了。
本来我是想在他的这个生日时对他说:“我以后不会再任性了。”
本来我是想对他说:“希望每一个有我陪伴你的日子里,都能让你感觉温暖。”
本来我是想对他说:“我会乖乖的,只要你不离开我。”
但是他不在我的身边,我无法诉说。我从包包里掏出笔和纸,把这些话写下来,让售货小姐一起包进保暖内衣的包装袋里。付了钱,却没有拿走。
“可以寄存在这里吗?”我问售货小姐。
“当然可以,您是想把它作为圣诞礼物送出去吧?”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的生日多么的好,圣诞节,有那么多人会一起欢腾庆祝,那么,他还会想念我吗?在这个生日,想念一个陪他过了十几个生日的小女孩,还会吗?我在内衣店为他寄存了一份礼物,也是为自己寄存了一份希望。我希望他赶在平安夜把它取走。
出了内衣店,我把双手放到嘴边哈了一口气,然后原路返回,朝ST培训中心大步走去。
“你不该独自跑出去偷吃好东西。”回到培训中心后,林季阳故意板起脸对我说。
“是啊,”我说,“说过要请你的,那么,明天吧。”
“确定吗?”
“确定。”
“这还差不多。”他的脸色这才由阴转了晴。
其实,并非是忘记了,只是因为突然记起他的生日,想为他挑选一件礼物,不希望被别人打扰,而已。恍然发现,在我心里,还是没有人能占据到和他相同的位置。
“喂,”林季阳走了两步又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打起精神来,开心一点。”
“嗯。”我点点头,莫名的失落,莫名的忧伤涌上心头。
“你们以前认识?”坐下来时,EMILY突然问我。
“嗯,同学。”我说。
“怪不得。”
“什么?”
“难道你没感觉到吗?他对你格外的好。”
“你想太多了,我们只是同学,很普通的朋友,如此而已。”
她吐吐舌头,耸耸肩,像个调皮的孩子,“来这里好几个月了,我就从没见他用那种眼神看过别的女人。”
我愣愣地看着她,也许吧,孤独的感觉会让两个孤独的人互相取暖。
用冰冷的手指敲击着电脑的键盘,手底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重重地砸上我心,一下,又一下。有那么一刻,眼泪就那么不经意的翻滚而下,落入唇间,那么咸。
“还是不舒服吗?”EMILY问。
“嗯。”突然趴倒在电脑桌上,不想说话。
“哎呀。”
我抬起头来,看到她桌上的玻璃瓶碎了,零落岁片散落一地。
“真糟糕,”她说,“这是我去年的生日礼物呢。”
“那怎么办?还能粘合起来吗?”我说。
她摇头,“还能怎么办,仍了呗,碎了就是碎了,再粘也不会成为原来的样子。”
继续趴回到电脑桌上,闭起眼睛。碎了也就碎了,我却不能如此潇洒,这个冬日,还是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