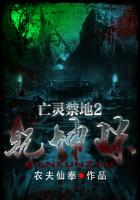十四
现在我不可能再这样轻易地回去了,若是回去了,退一万步讲,再碰到蕾内像今早这样回来,我浑身不起鸡皮疙瘩才怪呢?即使这样的结果会让我和父亲的“战争”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基础,但我已不想这样的结果出现了。
蕾内你已经慢慢地偏离了我的生活轨道,我们在同一条路上不知不觉地愈走愈远,以至于看不见彼此在同一条路上的影子,是你走了叉路还是我偏离了方向,都是吧!——都不是!
你让我恶心——你让我痛恨!
回家,意味着是一种多余的选择。我像是一个城市中的飘泊者,我的心与生活在异地的故人一样,然而我的飘泊时刻更显示出它本身的悲剧性、狭隘性,它就像城市中的一只风筝,一只无形的手拽着它,它能飞出去的也只能是风儿带给它的想象……
啊!——我连想挣脱那只手所需要的危险、消亡的权利都剥夺了,我的脆弱只能让我活着,这只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它力量的强弱均来自于我的心灵。
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男人、女人整天都在编织着自己的故事,这个世界充斥着千百个故事的头和尾,像一张张网,那些盘根错节就是他们的心。
故事有无数个头和尾,也有无数个无头无尾的延伸……我在这张网里疼痛地抚摸着属于自己的那个结……
我说的,我要把自己刚才的奇遇告诉爱达,她能发笑吗?以我现在的这种状态,恐怕连讲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们下午见了面,我有什么理由再去呢?人常见面,本该有的新鲜及神秘感全都没有,对方所在彼此心目中的光芒自然会消减。恋人、情人之间用忍耐换来的必将是巨大的幸福,但同时也是一场残酷的心灵战争,彼此都在用这种幻想构筑高傲的形象,企图用这种形象占据对方重要的价值,然而这种战争的残酷点就在于对方都想到了一块儿,输的一方不是收获不幸就是拥有幸福——周而复始,反反复复……
我没精力去和爱达这样熬着,年龄及经历都让我们必须速战速决。
我决定第二次去找爱达,不仅仅是做爱,还有商讨她离婚后到底怎么打算!如果心情不错,我是否该告诉她斯拉就在这座城市——也许这有点不可思议。不管我的心情是否好,这暂时都会是一个秘密。
来到新城居民小区,我望见了那六层小楼,灯亮着,与别人的房间没有什么区别。
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按响门铃时,屋内长时间没有动静,我贴耳倾听,一无所获。于是我照例下楼,在确认那层灯亮着的楼是爱达的家时,又才不死心地上了楼,重新按了门铃,而且反复几次,依然是照旧。
是她睡熟了忘了关灯?还是出去还没回来以示防贼?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想了许多条理由,就是没有一条理由让自己相信在外敲门的就是那个卡多(假如爱达仍在屋里面的话)。
我在原谅自己的同时,没忘记下午敲她门时的疑虑,还有那一股沐浴后的淡淡的清香。
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时候(刚过午夜12点),爱达的门都不会开了。
要想知道爱达是否真的在家,我差点忘了一个重大的确认方式,那就是看我的头、鼻、腿是否不“正常”。啊!当一切照旧时,我也没心去想了,这奇迹本身就是要两人接触时才能发生……
第二次下楼,屋内的灯亮着,我就愈发纳闷了。
爱达在和我开一个玩笑?!
既然我在这里落空了,那回到公园旁继续我下半夜的守候便是理所当然了。在想回到那里之前,我的心老是嘀咕着。那司机会发现我吗?——这会不会是在自投罗网?当然我不会再像昨晚那么傻了,静坐在那张石凳上,让石凳吸走我屁股上的热量,几乎让它成了两块冰。
今晚,我要把别人用一生散步所需的时间,在公园周围来完成。
再次来到公园时,我已感知我的身体里不停在冒热汗。这时,公园对面的天鹅舞厅正散场,出来的尽是一些喜笑颜开的男男女女,好像今晚的好事全被他们碰上了。此时,我无意用他们的欢笑来惩罚自己,我想的是要抓住凶手,获取那一万元的奖金!我想那时手中掂着那些钞票,脸色肯定不比他们现在差。
我嗤之以鼻,把注意力集中了过来。
当曲终人散时,舞厅大门里出现了一对男女。女的就是爱达,男的我不认识(为什么我要认识呢?),我眼睛放着凶光看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在舞厅大门外不到十米处,爱达和那个男人只是寒暄了几句便各自分开了。我的心松了一口气,想立即冲出去抱吻她,可我不能这样做,只有鬼知道我为什么不这么做。
爱达走了不远,便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搭了一辆篷篷车向城北方向急驶而去!……
只有现在的我才能理解爱达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如果我现在坐车追上她,会是怎样一回事呢?她会责骂我在跟踪她吗?肯定会的!这种伤害是不同于任何别的伤害,这叫什么来着?——是侵犯别人的隐私!
还是等着明天或者后天去吧。
这时,我突然又看见了一个小时以前那三个男人,心里一阵紧张。他们像三个幽灵似的盘结在公园四周。
我想,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得放弃下半夜的打算,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我重新摸了摸斯拉还给我的那一百二十九元人民币,生怕他们发现了我,而洗劫一空。
于是我远远离开了公园,那一万元离我愈来愈远,我的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
天这么晚了,也许他们等不了多久就会走吧!我仍不愿放弃,这样想着,远远地盯着那三个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在我这种念头冒出来不到两分钟时间,他们便坐的士扬长而去。
我庆幸自己运气真是不错,于是大摇大摆地重新靠近了公园。
我看见公园的树都在向我点头示意,好像我今晚有什么收获而提前向我表示祝贺。当然如果今晚真的能抓到凶手,这些树有不可少的功劳,因为没有它们,凶手不可能到这里铤而走险。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既然凶手早已被警察布控,而警察又没丝毫收获,那么凶手来此的可能性极大。
我为自己做出的有力判断空前的在心里鼓了一次掌,那一万元不是唾手可得了!现在我大脑中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以加速的方式提前蹦了出来:拿着这一万元干什么?买一台彩电?抽出一部分作为起诉与蕾内离婚的开支?或者全都用作与爱达结婚时的花费……或者壮大书摊多进一些书……
对!还有斯拉,她在为自己的承诺面临着贫困的袭击!……那爱达现在不是也没工作吗?哦!这笔钱应该全是她们的,她们是上天派来带给我“奇迹”的人,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
正当我盘算着这笔钱最终是该花在爱达和斯拉身上的时候,目标就形同一束亮光把我的心给照亮了。那个黑影也像我一样,在树林里慢慢踱着方步,头不时地警觉地东张西望。与我惟一不同的是,他是在公园的深处,而我是靠近公园的边缘。就凭这一点,他的嫌疑是更大了!当然,我在心里上完全确认对方有重大可疑性之后才能出手。我出手的方式首先是上去抓住他,然后是大叫抓凶手!通过这种让别人去报警的途径最终将凶手抓获。我惟一担心的是,警察最后将那一万元钱是给我还是给那个报警的人?如果我将两个人干的活揽在我一个人身上,恐怕我至少得做出豁出半条命的心理准备,到时那点钱做我的医疗费恐怕都不会够。当然,能够追忆我为见义勇为,勇擒罪犯的先进个人称号,那就另当别论。
现在,我急需一部手机的愿望何等强烈。就在我上前抓凶手的空隙的前后几秒钟拨打“110”,就能达到欲想的目的。可是,我现在即使离最近的电话亭也至少五十米的距离,到时惊动了罪犯,等到警察来时,他是早已像一团云一样被风吹得见不着踪影了。
不管怎样,我不能再犹豫了!
我小心翼翼地在向那黑影靠拢,感觉到我前面的每一步都埋了地雷似的。
这时,那黑影好象已经发现了我的行动,在以比我更快的动作远离我,我想追上他,好像已不可能。我惟一可挽救的希望就是让对方感到刚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这可能吗?
现在,我希望自己的两只脚上突然出现两只风火轮。
正当我失望之际,那黑影在转了半个圈之后奇迹般地主动向我靠来,这下我倒为我的惊喜打了许多问号:
“唉呀,这不是卡多吗?”
“你是?……你是……”
“我是郎滚啊!你老同学爱达的丈夫,你忘了吗?”
“别这样提醒我了,高中我们同一个班吗?”
“都是老同学,都是老同学!”
“怎么在这里啊!”我们几乎同时问对方。
“晚上失眠,睡不着!”
“不是蕾内把你赶出来,不让你上床吧?”
“哪来的话,你呢?说回来就回来了!”
“回来办一点事,还得出去!”
“外面怎样?”
“就是那么一回事,一言难尽!”郎滚长吁短叹起来。
“不把爱达也带出去?”
“老同学,我不想瞒你啊,像你这样的人能生活得如此好,我有时就想,这是不是命运总偏爱你们呢?把你们本该承受的一切痛苦强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去外面真是混昏头了!对郎滚讲出这些话,我根本不想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去分担他现在所面临的困惑!或许就是在外面挣不了钱,养不起爱达,爱达决定和他离婚吧!或者他白长了一副俊模样,那方面的事满足不了她!……
过去天生的一对,可经不起时间地洗涮啊!
“既然我这样的人都能生活得如此好,那你们那些人又会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呢?”
“说得倒也是,老同学,刚才的话是跟你开玩笑,头有点晕,说的话有点欠妥当,愿你别往心里去!”
“郎滚,你的鼻怎么啦?”我们一边交谈,一边走到了大街上。
“不小心摔了一跤,几年不回来,城市变化不小啊,到处都是钢筋水泥!”言外之意,果真是摔了一跤。
“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回来的呢?”
“昨天下午二点半钟的车回来的。”天啊,那不是我与爱达正相聚的时间吗?
郎滚的时间概念比我清晰许多,他所说的时间我还以为是今天呢。
“见到爱达和孩子佳佳没有?”
“没有,再等两天吧,见与不见都没什么意义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次回来就是与爱达离婚的,当然我不会让她这么轻松!”郎滚恶狠狠地说。
“为什么这样啊?”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这四个字成了郎滚的口头禅
“他在城里有别的男人没有?”
“这一点我怎么知道,老同学,你真是有点糊涂了,你们的事可千万别把我扯进去。”我既心虚又高兴地说道。
“我只是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
“如果还能有那么一点希望,我劝你还是别放弃,女人嘛,哄哄就没事了。”
“爱达是铁了心肠,也不知道是哪个男人迷了她的魂?当初我叫她同我一起出去打工,她就是不愿意,说外面累!其实这都是借口,可见她早已变了心!”
“这么多年了,她应该到法院自动解除婚姻啊,为什么她没这样做呢?”
“她是看在佳佳的份上!”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珍惜?”
“她怀疑我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说不寄钱给她。”
“你寄了吗?”
“寄了,还不少!”
“那她为什么怀疑你有别的女人?”
“最近一年我没寄了。”
“还是你这里出了问题!”
“也不是我这里出了问题,而是实际情况决定了的。”
“什么实际情况啊?”
“工作换来换去,在外面每天都要钱开支的,这不能和家里比啊!”
“那倒也是,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为了一个目的,我在郎滚面前变成了一个检察官的角色,他能从我的问话中感知到一点什么吗?既然如此,他丝毫也不会把理由二字串上。”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记得郎滚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回来办一点事,还得出去。
现在我没有一点的兴趣去抓什么凶手了,即使警察悬赏五万元,我也不能再干了(到时候可以另当别论),那个郎滚打乱了我的计划,扰乱了我的心情,并且还想折磨我所爱的那个美人。
如果他想与我斗,我想,我能奉陪到底!不为别的,就为这十几年的时间,他就该乖乖地认输。老同学还可允许他叫,否则……我咬牙切齿,仿佛为这么一个女人我可以完全把命搭上去似的。
总之,我战胜不了自己,战胜别人,这一点我还是可以肯定的。
我不想回家,打算到医院里找一张长凳睡觉。
想着郎滚的鼻血,我真抑制不住地笑:今晚没有他,说不定流鼻血的应该是我。
走在去医院的这段路上,我差点站着睡着了……
天下起了毛毛雨,我为明天地到来忧郁着,我的头有点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