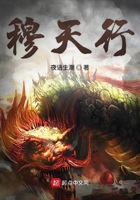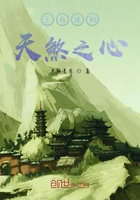谭延桐
美国画家怀斯,我是早就知道的。他画中的叙事感和抒情性,都是我所喜欢的,特别是他的不落烟尘和不落俗套更是我所欣赏的。按说,像怀斯这样一位怀乡写实主义绘画大师,是应该有许多的人特别是晚生代来“临摹”的——因为我见多了蜂拥而来又蜂拥而去的临摹者,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了。
却不。比如宁子的小女儿,就是这“却不”中的一位。
宁子住在美国的西海岸城市Torrance,是一位极其讲究生命品位的华裔美籍作家。她在2006年6月13日发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写到,周末他们全家去咖啡店喝咖啡聊天,轮流着谈一些各自的话题,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怀斯的村庄”。宁子发表意见说,很喜欢怀斯的风景画,希望她正在读七年级的小女儿以后能够多多地临摹一些怀斯的风景画。听到这里,女儿却说,不,她不画别人的风景。
“不画别人的风景”,这句话,让我灵机一动。
是啊,别人的风景,即使再好,也是别人的风景;即使临摹得再逼真,也不可能摇身一变,变成自己的风景。这是肯定的。肯定的事情,却逐渐被世人抹杀了,最后变成了你临摹我,我临摹你,临摹来临摹去,就总也找不到自己了。姓张或姓王,是男或是女,都无关紧要了。
很显然,宁子的小女儿是不想失去自己才不假思索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不画别人的风景”的。我想,她的将来也就可想而知了。世界上有一位怀斯就够了,是没有必要再有第二位怀斯的。她懂。
说到底,重复别人,是最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不仅耗时而且耗神。既耗时又耗神的事儿,也只有那些半睡半醒、傻里傻气的人才肯去做。而且,往往做着做着便纳入了集体无意识的轨道,再也出不来了,这便是自古英雄贵如金的原因之所在。
我不禁就想起了张大千。有一年,张大千去国外办画展,他不无得意地在展厅里走来走去,想听到别人的赞美。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听到一句别人的赞美声。他不禁想,外国人这是怎么了?怎么就不知道赞美别人呢?就在这时,对面走来了一位气宇不凡的观画者,他便控制不住地跑了过去,问人家,你好,你觉得张大千先生的画怎么样呢?那位先生只是轻描淡写地瞥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说了这样一句:张大千在哪里?就是这一句,犹如当头一棒,顿时把张大千砸了个两眼冒金星。后来,张大千彻底摆脱了别人的影子,真正找到了“自己”,据说与这当头一棒有着直接的关系。
多好的一棒啊,这才叫“棒喝”。即使别人不来棒喝自己,自己也是应该经常地棒喝一下自己的。人也只有在这样的不断棒喝下,才会避免生锈,最终锻造成一块好钢,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
泰山有泰山的风景,黄山有黄山的风景,华山有华山的风景,衡山有衡山的风景……这谁都知道,如果它们彼此临摹,临摹来临摹去,肯定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了泰山、黄山、华山和衡山了,大家也就彼此一样了,鼻子、眼睛、眉毛都一样了,再也分不清你和我了。那么,最终的下场就只有一个——可悲。
数来数去,可悲的例子还真有不少,就比如那个以效颦而闻名于世的东施吧,本来,她活得好好的,却偏偏要去模仿美女西施,模仿西施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模仿来模仿去,最终便成了世人的笑料。
当然还有更可悲的,比如我早年在童话里所写的那只十分幼稚的小兔,看见刺猬浑身带刺,还以为它有多酷呢,就忍不住去模仿,在自己的身上扎下了很多很多的牙签。疼得它呀!可是,它却忍着,为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酷,像刺猬一样酷,甚至比刺猬还酷,它坚强地忍着。为了不让别的小兔知道它变酷的秘密,它还偷偷地把主人的牙签全都独占了,兢兢业业地一根一根地往自己的身上扎,扎,扎……扎来扎去,皮肤就发炎了,溃烂了,最终无药可救,死掉了。这就是“临摹”的后果!
如果,他们也能像宁子的小女儿那样知道“临摹”的后果,坚决不去“画别人的风景”,而是一心一意地“画自己的风景”,至少,遗憾是不会走近他们的。为了不让遗憾走近自己,和自己拉关系、套近乎,像宁子的小女儿那样从小就清醒地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无论别人的风景有多诱惑,就是坚决不去画别人的风景,美好的境界自然就成了。
(选自2007年第6期《黄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