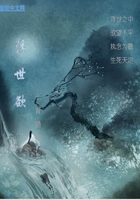里尔用日记和书信记录了他在意大利的感受。在《佛罗伦萨日记》中,他写到了生命、死亡、历史、女性、艺术家的气质等,这些后来变成了他诗歌的主题。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你,我最美妙的,总在促使我有所进步。如果说意大利的日子给我赠送了珍品,那么是你在我的心灵里腾出了空间,从前在这里面布满了梦幻和忧虑。你使我坚实稳固,我这样明朗地回到你身边,亲爱的,这是我能带给你的最好的礼物。”
七月初,里尔克从意大利归来。我们在柏林重逢。走万里路,胜读千卷书。意大利的一段游历,让里尔克有了更多的反思,他的作品明显地比以前要成熟。
不久,里尔克的《骑手》、《骑手奥托.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诞生。这是一首长篇叙事抒情诗,后来出人意料地走红,并成为里尔克诗歌创作中的里程碑。对里尔克来说,这是一种意外的的收获。色彩绚烂、音调铿锵,从头到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诗集《降临节》、《为我庆祝》接踵而至,《图像集》更加升华了他的创作价值。这期间,他还创作了《上帝的故事》,连早期的几本小说,也陆陆续续地出版了。
仿佛情感受到了催化,里尔克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期。
说起那一段时间的感受,里尔克说:“漂浮在我面前的任何一种快乐,都会同时触动、包围我那神秘的灵魂。假如我感受到早晨清新的空气,那么它就会渗透到我的每一个毛孔,直至清晨的清爽和朝气充盈着我的身心的各个角落。有时,我嗅到了果实的芬芳,那芳香就会进入我的舌尖的每一个味蕾,仿佛一个正在溶化的灵魂在喃喃细语,这是一种不可惊扰的精神体验,直至它纯正的香味升腾在我的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和细胞。”
转眼就是一八九九年,我离开俄罗斯已有二十个年头。很早以前,我就和安德烈亚斯筹划着一趟俄罗斯之旅,但这个计划从未实现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思念、对俄罗斯文化的思念,在内心深处不停地滋长。
我和安德烈亚斯决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去趟俄罗斯。这时,正好哥本哈根的布兰兑斯要到俄罗斯去参加一个纪念普希金的活动,他是我们的朋友,最初安德烈亚斯是从布兰兑斯那里了解我的。我们取得了联系,并准备在俄罗斯见面。
和一个老朋友在一个很远的地方见面,这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里尔克,并邀请他同行。里尔克很高兴,安德烈亚斯也没有表示出不满。
俄罗斯对里尔克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尔克为此做了很多的准备,有一段时间他深深地着迷于俄罗斯文学,卖力地学习俄罗斯语言、了解俄罗斯风俗,研究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
大概是在一八九九年的复活节期间,我们终于成行了。我们三个人一起访问了我的家乡彼得堡,然后又去了莫斯科。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四月十七日。
世纪末的俄罗斯山雨欲来,处处给人一种暴风雨的前夜的感觉。里尔克为能体验到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巨大变化而激动不已。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星期,与众多的文艺界人士见了面,如绘画大师列宾、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后来还通过他们认识了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这个女诗人后来还和里尔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次行程中,克里姆林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追记:
“克里姆林宫的穹顶和宫殿红、黄、绿相间,和周围和谐地融为一体,它高高在上,俯视着周围,如同一位慈祥的父亲。金色的建筑点缀在克里姆林宫的四周,如同无数颗耀眼的彩星和一道道锦簇般的彩带......
克里姆林宫的金色与众不同,不论是第一缕阳光洒向莫斯科的清晨,还是沉沉的夜幕,它都能显示出一种皇家的气派,无论夜色多么深沉,都无法泯灭它的光彩。”
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插图作家。他的儿子后来成为苏联时代著名的诗人。通过这位画家的介绍,我们第一次拜见了托尔斯泰。
尽管托尔斯泰的家乡不是我们的首选停靠站,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形象是我们进入俄罗斯的大门。如果说陀斯妥耶夫斯基首先为里尔克打开了俄罗斯灵魂的深渊,那么托尔斯泰则表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诗意的力量。
我们第一次去拜访托尔斯泰,是在他莫斯科的别墅里。那是1899年4月26日。我和里尔克、安德烈亚斯一起,在激动中叩响了托尔斯泰家的大门。他的大儿子打开玻璃门,我们跨进门廊,站在这位耄耋老人的面前。他看上去显得瘦小、伛偻、苍白,他的双眸却不受衰老的影响,向我们传递着不可言说的福祉。
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作《复活》。因为《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托尔斯泰成为俄罗斯的文学大师,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的文化象征。
这一段时间,托尔斯泰无论是从精神上、思想上、宗教上、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被人称为“俄罗斯的良心”。当时,俄国旧秩序正在急剧地破坏,给农民带来了新的苦难,农民忍饥挨饿,大批死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产......面对这一切,托尔斯泰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省:“我过去享受过的所有的奢侈、所有愉快,今天都成了一种对我的折磨。”
我们在托尔斯泰家坐了几个小时,聆听着他的教诲。初出茅庐的里尔克对托尔斯泰怀着一种仰慕之情,像一个孩子一下,依偎在老人的身边,倾听着,几乎没有插嘴。安德烈亚斯说的主要是波斯的文化、宗教和在波斯考察的经历,我则谈了重返俄罗斯的感受。
托尔斯泰说,据他长时间的观察,俄罗斯人对宗教的虔诚夹杂着数不清的迷信,需要有人来启蒙,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给愚昧以棒喝。我们无意中说到了即将到来的复活节,托尔斯泰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参与复活节这样的民间活动中,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迷信和愚昧。
复活节是四月三十日,是东正教的第二大节日。那天,信徒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复活了!”晚上,俄罗斯人几乎倾巢而动,挤满了教堂,人们颂扬着耶稣的恩泽,祝福着他的复活。晚上,克里姆林宫广场举行盛大的复活庆典,教堂穹顶上耸立的十字架金光灿灿,当克里姆林宫悠扬低沉的钟声回荡在空中时,浓烈的宗教气氛感动着每一个人。
尽管托尔斯泰告诫在先,我们还是忍不住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复活节之夜。这对我们三个人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一遇。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民俗,复活节都深深地烙上了俄罗斯民族的印记,深入其中,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俄罗斯民族的信仰和社会变化的原由和动态。
对此,里尔克在后来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有生以来,只经历过一次复活节。那是一个漫长的、别有风味、非同寻常而又令人振奋的夜晚,许多人济济一堂,伊凡·维里奇在黑暗之中敲打我,一下又一下,这就是我的复活节。我想人生有此一次足矣。在那个莫斯科之夜,那种信号在我的感官中奇特地强烈起来,它进入了我的血液、我的心灵。”
这次俄罗斯之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五月二十六日在圣彼得堡参加了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活动。普希金的少年时代曾在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读书,1836年他带着年轻貌美的妻子举家迁到圣彼得堡居住。这时,法国流亡者、俄国近卫军军官丹特士放肆地追逐他的妻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普希金决定与丹特士决斗,地点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决斗场上,结果他身负重伤,鲜血洒在雪地上,两天后去世。这是发生在1837年初的事。
有人说,这是一场阴谋。因为普希金多次流露出对当局的不满,所以才有了这场并非势均力敌的决斗。一个文弱的诗人哪里是一个青年军官的决斗对手呢?
普希金逝世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
里尔克是一个诗人,他比别人更加明白,诗歌是没有国界的,诗人的魅力是不分民族的。普希金展现出的诗歌的生命力,在里尔克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对我们来说,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布兰兑斯正好充当了这次活动的解说人,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俄罗斯最有份量的诗人普希金。
短短两个月后,我们回到了柏林。就像翻看一本大部头的俄罗斯历史和地理,这次只是粗略地浏览了几章,让人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