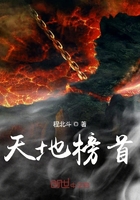一路上,他们两对在前面聊天,欢声笑语的,都不回头看我和曹伊红,仿佛刻意为了给我们创造独立的交流空间。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世上有一些人看到一点苗头就去撮合别人,完全不顾当事人的真切想法。你若拒绝的话他们会说你害羞,继续撮合;你若接受的话,他们很自然就成为一对新人结合的功臣。因为这些人起了头,别的人见了只好附和、起哄了。以至所有人都认为你们真的“有一腿”。虽然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
不过,这样我正好可以好好的施展我的“探秘计划”。
曹伊红素手卷着衣角,低着头不敢看我。我当时认为她很适合我的同学田有光的胃口,他就喜欢这种清纯可人的,只不过喜欢的次数有点多了,后来就赢得了一个外号“田伯光”,学妹们见到他都是不敢轻易搭理的。
我故意沉默一段时间,曹伊红始终不发一言。我只好先开口。
“那个叫美蓝的是你妹妹么?”
“嗯。她调皮的很!”
我问她:“你们两个的名字好怪啊,是不是那种细胞染色的染料啊?”
“嗯。我爸爸是生物老师,爸爸本来希望我是——男孩的。”
我觉得她太腼腆,“可你没有一点男孩子的气质啊!没必要那么害羞吧,大大方方的多好。”
曹伊红一听脸就红了
我问她:“你怎么不念书了?”
她扭捏了几分钟,好像难以启齿:“我——不会——念书!”
我说:“我看你打接地线很熟练的,是个聪明的女孩。怎么不会念书呢?”
她见我提到昨天的事,尴尬异常,干脆不说话了。我又问了几个问题,她还是不说,只是低着头。这下麻烦了,我本来是想先问一些事情做个铺垫,然后再问周荣剑的事,没想到会这样。我打过很多次架,骂过很多人,但从不针对女的,特别是曹伊红这样的,我简直束手无策。无奈,我只好先介绍自己。
“我叫侯杰,在A市长大的——”她突然捂嘴笑了起来,搞得我莫名其妙,难道她知道我在说谎?
我带着点气愤的语气问她:“你笑什么啊?”
她一开始不回答,看我一脸严肃才说:“你的名字怎么那么怪!比我的名字还怪。”
“怎么怪了?”
她终于抬起头,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我恍然大悟:“老爸就给我起这样的名字,我也没办法。幸亏我的喉结不是很突出,否则就真是‘人如其名’了!”
我暗地里感激这个叫“侯杰”的名字让曹伊红开了口。
我说,“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工作呢,别人一叫我名字你就发笑,那可怎么办?”
“别人叫你名字我才不笑呢,反正我不叫你这个名字。”
我忖道:“你不叫我侯杰叫我什么?叫‘猴’么?我又不是动物;叫‘杰’么?太亲密了吧。”
她笑着说:“有事就叫你阿杰,不就行了么。”聊了一段时间,她似乎也放开了。
我突然冒出个想法,不如让她叫我哥哥,也省得别人误会了。
“这样吧,你就叫我‘猴哥’,呸呸呸!说漏嘴了,叫‘杰哥哥’吧,挺好听的称呼。”
“杰哥哥?”她好像在犹豫。
我突然又觉得她有趣起来:“你小我五岁,叫我叔叔也行啊!呵呵呵——”
“我才不叫你叔叔呢。好吧,就叫杰——哥——哥。杰哥哥,大学是个什么样子啊?”
我有感觉她并不是喜欢我,只是对我好奇罢了。她有什么理由要喜欢一个大她五岁的刚认识的人?她只是害羞,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不过这样我倒放心了。
我问她:“你不是不喜欢念书么,为什么还要问大学是什么样的?”
她说:“我喜欢念书啊,可我就是——念不进去。一本书放在眼前看一天就只能看十行,我考试都是班上倒数的。”
还真是个怪女孩!我刷刷的跟她解释一段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多自由,多快乐。她听得眼睛都亮多了,一副羡慕不已的样子。
终于打开了她的话匣子,我刚要问她周荣剑的事,就到了山脚下。走在前面的两对四个人不见了,曹伊红说他们肯定先上山了。我问这山叫做什么山。她说一直叫做雀山,雀山南面有一条峡谷,雀山对面是凤凰山。有一座明代留下来的钢索吊桥连着两边。我问她何家平说的事是不是真的?她说那只是传说,她就见过许多人一个人走过去,桥也没塌掉。
我乘机问她:“那我们不是不用成双成对的过去了?”
“不知道。”她又害羞起来。
我突然想起周荣剑,我顺口说了句:“我要是陪着我喜欢的人走过去,那肯定是没事的喽!”
曹伊红以为我在说她,头又低了下去。
我问她:“你有喜欢的人么?”她直摇头,这么说她肯定不喜欢我了。
事后我才明白伊红当时摇头还有一种解释:她在认识我之前没有喜欢的人,认识我之后就不一定了。
我乘热打铁:“我有喜欢的人,她年龄比我还大。”我喜欢的人肯定不是她了。
曹伊红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只说:“杰哥哥,我们——上去吧!”
雀山已经开辟出了一条上山的路,有的地方还用水泥,石头铺成台阶。树木茂盛,林子里没什么鸟儿的,上山的游玩的人着实不少,都在往上爬。
我们边爬边聊。
我问曹伊红一些车间的事情。先问主任是什么样的,她说主任姓方,叫什么名字自己也不知道,别人都叫他方主任,很胖,喜欢骂人;说鲁国行线长有个外号叫做“鲁花”,因为他时常到线上去督促员工提高产量,员工累得满头大汗,叫做“鲁花压榨花生油”。说到班长周荣剑,我说班长眉头上的那个胎记很别致的,她解释说那不是胎记,是有一次二楼检验房掉下来一块铁板给划的。她称呼周荣剑为“周姐姐”。我心想“周姐姐、杰哥哥”不正好是一对么!我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说你周姐姐挺漂亮的,有没有男朋友啊?曹伊红说,听别人说以前有一个,因为她破了相,两人闹矛盾就分手了。
至此,此行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不过既然来了,还是要多套一些信息出来。
原来班长虽然不用直接干活,但着实是个苦差事。要早起去领导办公室开会,晚上还要报告生产情况,每天都要比员工少休息两三个小时。员工们可以请假,班长却是请不了的。因为没了班长,一个生产段几乎会停滞。又不设副班长,组长的权力不够大,管不了人的。(出勤是由班长写的,决定着工资的多少。)
我说,那我们班长周荣剑是个女的,可真是不容易、不简单啊。曹伊红也点头同意,说五个自己也干不了班长的工作。
我问她,既然那么累,还干什么班长啊;当个一线员工多好,虽然工资少一些,工作却轻松多了么。
曹伊红笑说,周姐姐的志向很高的。班长上面就是线长,当上线长后就轻松多了,不用天天跟着员工一起上班。
如果周荣剑真如曹伊红所说的是个女强人,她还真的不适合我,而且很不适合。我爸爸就是这类人,所以我很少从他那里得到父爱,一直是妈妈照顾着我。不过我不太信任曹伊红现在所说的话,也许她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思,故意让我对班长失去兴趣。事实上,连苏寒都鼓励我去追,我怎么能因为一个丫头片子就改变主意。既然周荣剑这么累,那么以后开线了,得好好替她分忧。要怎么分忧呢?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是自然的了。
这时到了一个岔路口,回头已经看不见山脚了。大多数游人都顺主道往上爬,我问曹伊红走哪条路。她说,他们四个肯定走的中间的主道,我知道左边的石子路有一条捷径通往桥头,我们可以抢在他们前面通过永睦桥到达凤凰山;不过那样就错过了山顶上的雀山亭了。我心想,错过了正好,等下次我约周荣剑来,再去不迟;省得我和曹伊红过桥的时候,于虹薇那个乌鸦嘴室友又要乱说一通。
我说:“咱们走捷径。”
不过,捷径不是好走的。有些地方荆棘丛生,快到桥头的时候,曹伊红右脚崴了。脚踝又红又肿的,她埋怨说自己小时候就走过好几次,都没崴过脚,今天算倒霉了。
上了桥头才发现原来雀山离凤凰山其实很近,吊桥正好修在两座山的最突出的两个地方,跨度有四十多米,桥面距离峡谷底端也有五十多米。如大多数照片上的吊桥一样桥底铺着木板,两边有扶手。桥头一颗松树旁边的大石头上刻着“永睦桥”三个大字。
山顶上树木茂盛,遮天蔽日,凉风吹来,刚流的汗全干了。
已经有几对情侣手牵着手走在桥面上了。不见于虹薇和酒瓶底,身后那条路是从雀山亭通过来的。我心想还是赶快过去吧,否则那个“乌鸦嘴”来了又有文章可做了。但是曹伊红脚崴了,让她一个人扶着扶手摇摇晃晃的过去,决不是大侠所为。
我说:“曹伊红,我背你过去吧?”
她脸红红的,不置可否。不过我已经蹲在她面前了,过了好一阵,她才把手伸过来。“背起来的时候抱住我的小腿就行了。”可是那样她的中心就要向上提升不少,她俯视峡谷的吓得直哆嗦。我问她:“你到底有没有走过这条吊桥?”她说没有,她妹妹和乐义走过。
我试着走了几步,吊桥摇晃不稳。曹伊红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是比苏寒还要重一点。若是在平地上,背她走过去自然不是问题;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她放下来,说还是扶你过去吧。
走到一半,就听到于虹薇在叫我和曹伊红的名字。回头见他们四个已经站在雀山桥头,而“乌鸦嘴”举着一架相机正在给我们拍照。这下可不妙了,要是被周荣剑见到这些照片,追她就难上加难了,后悔不该来玩。我一分心,手一松,曹伊红一个趔趄摔在桥面上,还好桥面很宽,峡底水声依稀可闻。我边道歉边把她扶起来,但见她脸色煞白、浑身发抖。
我本来打算先到了凤凰山桥头。等着他们,让“乌鸦嘴”没事说、干瞪眼;这倒好,她不说已经够吓人的了。
我收回心思,把曹伊红扶到凤凰山桥头。刚松了一口气,就见她眼眶里噙着泪水。我想她是脚崴痛了,中间又摔了一下,所以才这样吧。
酒瓶底和于虹薇,乌鸦嘴和她男友,已经分别牵着手往这边走了。
于是我激曹伊红:“你妹妹美蓝都走过来了,当姐姐的哭什么啊!他们都要过来了,被看见了多没面子!”她见我这样说,眼泪扑簌着落下来,坐在石头上把头埋在臂弯里呜呜的哭了起来。这可如何是好,他们还以为我欺负她呢,早知道还不如不说她。
她哭了一阵,终于在他们到达之前止住了。她把眼泪擦干,说我们下去吧,不要理庞芳和于虹薇他们就是了。我这才知道那个乌鸦嘴就叫庞芳。
这样正如我愿。曹伊红走了几步,脚踝还是痛的很。
凤凰亭也没看一眼,我背着她蹭蹭蹭一口气逃了好远。有人见了还以为是在举行背人大赛呢,不仅曹伊红害羞,我也尴尬了,幸好凤凰山这边游人不多。
到了山脚,曹伊红说要坐车回去。我给酒瓶底打电话,说曹伊红崴着脚了,得先回去,你们好好玩吧。酒瓶底说行,你照顾好曹伊红,我们没关系。
凤凰山离柏油路还有一段距离,隔着一片稻田。
曹伊红说脚好许多了,坚持走了几步又痛得不行。只好让我背着穿过稻田。不过我们很有运气的等到了每天来回两次的凤凰山到紫云山的公交车。这公交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除了司机和售票员,乘客座位就只有八个。车票两块。
有几个大叔大妈拿着锄头、铁锹、箩筐等农具,见我们上来热心的问曹伊红怎么了。曹伊红不答话,我正要说“朋友脚崴了!”谁知曹伊红一把拉住我的手:“杰哥哥,别说!”有个坐在前排的大妈似乎看出什么来。笑道:“小丫头脚崴了吧,肯定是爬山过永睦桥弄得吧。”曹伊红脸刷得一下就红了,那大妈推了推一旁打盹的灰白头发的老头:“老头子啊,给这丫头推拿一下!否则真要让这小伙子背一辈子了。”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看情况我又被误会了。曹伊红赶紧解释:“没——不是爬山弄的——没过永睦桥。”那大妈笑道:“你靖哥哥都叫了,还说自己不是黄蓉么?”曹伊红脸已经红透了,我还没见哪个女孩脸红成这样的。不过“靖哥哥”和“黄蓉”我是听懂了,我也不好解释什么。但见那老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乌黑的木瓶子,从里面倒出一点煤油一样的液体把曹伊红两只脚踝都揉擦了一遍。然后嘱咐道:“到紫云山下车应该可以走了,不过明天最好不要走动。”
我赶忙说太谢谢了,多少钱?
大妈听了又笑了:“给什么钱啊!小伙子真见外。”一车子六个人除了曹伊红红着脸都笑了。
我实在搞不懂她们是什么意思。不要钱就不要呗,何必这么讥笑我。
曹伊红皱着眉头解释:“他是在外地长大的,不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
她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和我肩膀挨着着肩膀,那种在陈丫头身上闻到过的香味又再次出现了,而且似乎更浓一些。我不由自主的和曹伊红靠得更近些。
到了紫云山,我再次感谢神医一遍。我们下了车。
曹伊红说自己走回去,我看她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离公司这么近我又不好背她。我要扶她她又不让我扶。我只好在后面跟着她,到了她家门口。她妹妹美蓝正好出来,看她姐姐一瘸一拐的。竟然指着我坏笑:“姐夫,你把我姐姐害成这样,你要负责哦。”我晕。曹伊红突然来了脾气:“瞎说什么!你要是在爸爸面前胡说,我就把你的事也告诉爸爸。”美蓝做了个鬼脸:“保密!一定给姐姐保密!”
“还不快扶我回去!”然后她回头跟我说:“杰哥哥,我没事的,你回去吧。”
美蓝冲我挥手:“姐夫。再见!”
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