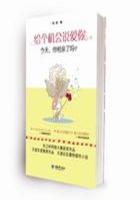我不曾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贵和优越。那是黯淡着的光环,穿过层层叠叠现实的罅隙,能温暖我血肉的寥寥无几,甚至给我带来伤害。事实上,我是一直贪恋着不变的稳定、稳定的不变。就如陈义美说的那样,我很怯懦。因为怯懦,我才惧怕改变,像小鸟一样惴惴不安。貌似坚固的鸟巢,一阵风就可吹塌。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深埋着一些东西,一些只有拨开浓重云雾、钻进黑黢黢的心坟才可一睹那脆弱之极、不可触摸却依旧鲜活着的伤口。那些不堪的阴霾,唯有随着时间无情的流逝,才能在彼此记忆中慢慢的消磨干净。
我羡慕那些可以自由远行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便拍拍身上的尘土毫无牵挂头也不回的离开,尽管这份自由也必定让他们付出孤单寂寞、生活无定的痛苦,但既然命运注定了流浪,何不尽情的去体会,欣赏一路上不一样的风景足可聊以自慰和自我原宥。我向来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看到火车站的石阶上衣衫褴褛、头发花白的行乞老翁无力的吹奏着笙箫。他是否也曾意气风发?是否也曾儿女情长?是否也曾妻贤子孝?他为何会沦落至此?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潇洒,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永远的潇洒。那些抛弃过去的游子,大都埋葬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和一份无法再视的伤情。
火车飞速的前进着。
陈义美给我发来信息:“我们会再见面的。不过我已经对你失去兴趣了。”
我回复:“很好。”
她也回复:“很好。”
我继续回复:“很好。”
“‘很好’是什么意思?”
“你的‘很好’是什么意思,我就是什么意思。”
她回复:“记住:1,不要打扰我;2,我有可能打扰你;3,换手机号码一定要事先告诉我;4,记住上面三条很重要。”
我回复:“我若只记住第一条呢?”
“你会后悔的!”
“我不懂。”
“因为你的心思我能猜透,这点你不用怀疑。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帮你渡过难关。”
“要不要付给你钱啊?”
“你记住就行了。”
“行。我记住了。现在还要不要打扰我了?不的话我睡了。”
“好梦。”
清晨,回到A市。一切景象如旧。
我先做出租车回家。妈妈在家,做好早饭等着我。老爸开会去了。我没提苏寒的事,我只说最近学习压力大,到远处一个朋友家散散心。妈妈没再追问。
吃完后我睡了一觉,醒来后,老妈已经上班去了。我打电话给她,说我下午就去学校,我会跟指导员解释清楚的。
我先做公交去西城苏宏的学校,把我去梅花镇的事说了。苏宏听了颇为惊讶,他说自己还没被姐姐邀请去玩过呢。我大怒,审问他,你姐姐发生那么多的事,为什么事先一点都不告诉我?害得我和你一下子都成了小峰的舅舅。苏宏解释说,是姐姐叫我这么做的,我自己也没办法。我问他酒鬼老爸现在怎么样,他说烟不抽了,酒喝得比以前凶,昨天前还被几个人打了。
我们去操场踢了一场球,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
学校也如城市一样,很难改变。
我此刻倒希望它变化一些,比如校园里残垣断壁,蒿草茂盛,男生女生都变成老头老太婆……变得沧桑一些,才能显出知识满腹的味道,因为我就见过一个弯腰驼背的“全学科博士”,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我学的是环境科学,在学校西区。本来只是个学院级别的学校,在我考进去前,A市教育部门为了增强本市高等学校的综合实力,把我们学院合并到东区的理工大学,于是环境学院就成了理工大学的一部分了。东区和西区之间隔着大半个城市,所谓山高皇帝远,校长大人很少大驾光临,又是后娘养的,因此什么好事西区都是捡的残羹冷炙,教学成绩也办不上去。临近毕业,还发生了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对这些,我虽然不平,更多的是不在乎。因为,我压根就想着一踏出学校大门就自力更生,好好生活一番,做不做本专业的职业无所谓,对那些权啊钱啊的不感兴趣。不是说,我老爸现在是市土地管理局局长我就不愁着找不到好工作。我大一进来的时候就很低调,那时候,我爸离局长之位还差了好几级呢。有什么事情都是我妈出面的,就这样瞒了两年,到大三了才有好事者发现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吴友正就是我老爸。于是我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彻底扰乱了。
房价连年攀升,大家都说现在土地就是金钱,我爸掌管着本市土地的予夺大权,那肯定不用说也是几乎很可能大多数情况下那个那个的了。对这点我想大家都真的误会我爸了,虽然前几任上任不久就被罢免了,但我爸是以廉洁奉公的美名当上局长的。这点毋庸置疑,我家最贵重的东西就是我妈的那架海伦钢琴,还是好几年前花八千块钱买的,以前用的那个旧的是我奶奶传下来的。
但是,人言可畏。暴露身份就成了众人的狙击目标。虽然环境科学这门课我不大喜欢,还是得拼命的学好,否则别人就会说,干部子弟,不用好好学习也是个好的将来。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爸是个普通人或者是个小官,那样我就自由多了。这一年来,有架不能打、有嘴不能骂,着实憋得难受。有的本来和我关系很好的人,现在渐渐疏远我了;有的根本不认识的却常常在我眼前蹦来跳去,跟我套近乎,以为能从我这里占到什么便宜。我宿舍的那几个,就和我打得火热。
我想,郝豪不是这样的人。他和我一个班,住在隔壁的宿舍。快毕业了,突然有一天他问我怎么这么多人针对你啊?我说我爸是市土地管理局局长。他说,局长的儿子怎么了,就该被人说三道四?我说他们都像你那样想就好了。郝豪对网络游戏很痴迷。他是我们班的网络游戏鼻祖,以前会玩的都拜他为师,不会玩的也被他教会了。唯独我,从不玩网络游戏,我倒是喜欢看网络小说,看的速度极快。二三十万字的,两天就能看完。我和郝豪的关系一直很好。
除去纷纷扰扰,我敢说,大学生活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还是快乐万分的。彼此都没了高中时的压力,没有老师家长的压制。大家来自天南地北,充分挥洒着自己对自由生活的想象,可以好好学习,可以好好恋爱,可以好好游戏,不受太多的干扰。这就是大学的自由。可惜这份自由之泉在五月太阳的暴晒下,接近干涸。大家各自忙着考试、分手、考研和找工作。连郝豪和他的那帮徒众都不得不分心去应付毕业来临时的措手不及。
在这种大背景下,逃课是很正常并且很难防范的事了。我之前就有人连续两个星期没上课,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或许是因为我的所谓的特殊背景吧,指导员一开始以为我只是出去一两天,因为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触到了他的安全底线,他就只好打电话了。因此,当我完好的出现在教室里上课时。他便没再说什么,我也就无须解释了。
到了六月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心不在焉了。拍照啊,喝酒啊,赌博啊,接吻啊,花样百出。大家就像笼中的鸟,在放飞前激动不已,猜测着到了比大学这个笼子之外的那个更大的社会笼子里是会一帆风顺,还是凶险万分?
我和两个室友加上游戏鼻祖郝豪四人个人计划一起去黄山玩一次。到了临行的那天早上,老爸的秘书孙姨突然给我打电话。我爸是没有手机的。我在学校里,老爸从来不给我打电话的,更不会叫她的秘书给我打电话,我感到有什么发生了。
我赶到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爸爸不在。孙姨陪在妈妈的身边。孙姨说我爸在外地开会,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是邻居发现我妈出事了,拿我妈的手机打到我爸办公室被她接到的。
妈妈的头上缠着绷带,脸色惨白,眼角还有血迹。她的身上插满各种管子,渐弱的心电图音像刀锋一样割着我的心。
我抓住她的手,跪在她的身边,失声痛哭。
妈妈仿佛听到了我的哭声,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过去。
“小原——你爸爸!”
这是妈妈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我深爱着的妈妈——我不能失去的妈妈——
我想我是昏了过去,我无法在清醒时忍受那样的痛苦——
那个,苏寒也曾忍受过的痛苦。
在那些以泪洗面的日子里,地球停止了运转,时间混淆了昼白。我一直躺在妈妈那架钢琴旁的沙发上,感到了妈妈依旧活着,我听到了熟悉的钢琴声——
在某一天我睁开双眼时,爸爸靠在我身边睡着了。壁钟显示是早上六点。我回到我的房间,学校的物品都已经拿回来摆放好了,桌子上放着我的毕业证书。镜子里的我已经瘦了好几圈,胡渣也已经很浓了。我刮胡刷牙洗脸,然后背起我的背包准备出去。这时爸爸被我吵醒了,他拦住我,把我拥在怀里。
“妈妈走了,还有爸爸。爸爸会照顾好你的。”
我推开他:“不要说妈妈,你再说我又要哭了。”
“你要到哪里去?”
“我想去学校逛逛,别担心,没事的。”
“你出去散散心也好,你早点回来。有事打我手机,我已经买了手机。以后你随时可以联系我。”然后他报了一个号码。
我的手机不知什么时候被谁关掉了,我开机,已经有五十多条信息没看了。
有一条是苏寒的,剩下一半是陈义美的,一半是哥们的。
苏寒问我毕业后在哪里找的什么工作?
陈义美则大多是怪我怎么不遵守她那四条。
哥们的信息一开始问我家里出了什么事,后来就是节哀顺变的话。
我把老爸的手机号码添加到名片夹,便下楼去了。
我家还是和原来住的老楼一样,在三楼。离地面也就十来米高的距离,我跳下去也不见得摔得死。可是妈妈在我那天要去黄山的时候,下楼梯不小心踩空了,从三楼滚到二楼,头撞在了墙壁上。要知道我妈头痛病已经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