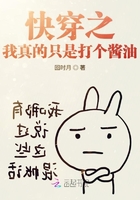公安县城斗湖堤一条叫治安路的街巷里,有一个本地人已熟视无睹、外地人则感到稀奇的景观:街的一边是富丽堂皇的公安宾馆,一边是戒备森严的县看守所。宾馆迎客的霓虹灯,正好和看守所高墙上警惕的哨塔隔街相望。看守所隔壁,还有一个第二看守所,第二看守所隔壁,又是武警公安县中队。曾经有一位外地作家看到这少见的景观,打趣地说这座上宾与阶下囚,仅仅一步之遥。而在这8·6之夜,这里发生了一次更少见的特殊行动:两个看守所在武装押解下实行了一次整体大转移。
战争中突击转移或处决、遣散在押犯,这是规律也是常事。这场分洪大转移犹如战争,一旦分洪,公安县城就成一座被洪水四面围困的孤岛,孤岛中的囚犯就成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分洪预案中已有这样的的部署:公安县看守所在转移令下达后迅速整体转移到江陵县看守所,作临时性异地羁押。
正是斗湖堤全城沸反盈天的时候,两辆从荆州一路鸣着警笛来的警车驶进县公安局。
还没等车停稳车上的公安干警们就纷纷跳下,他们是奉命专程来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的荆州市公安局两位副局长周志洪、陈斌,及市局预审监管支队的正副支队长一行。市局领导与县局领导及两个看守所所长紧急商定:立即抽调警力和车辆,实施陆路武力押解。
仅仅半小时后,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公安干警就在两个看守所集结完毕;同时由县防汛指挥部派来的7辆大客车,也依次停在了两个看守所大门前。高墙内的狱区里,则响起阵阵急促的口哨声,总共165名在押犯全部被叫出了监号。
于是,一个平常只能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才有的场面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警排在高墙与大客车之间,形成一条长长的武装夹道。一队队囚犯在狱警的指挥下通过这武装夹道,鱼贯进入一辆辆大客车。然后由警车开道和压道的这支特殊的车队,隆隆地驶出了这条街巷。当时有几位从外地连夜赶来分洪区投宿公安宾馆的记者,碰见了这个由警车开道的大客车车队,曾驻足观望了一会,不过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两个整体转移的看守所。不然他们会迅速举起摄像机和照相机,让第二天的媒体上出现这则少有的新闻。
这支武装押解的车队驶出城时,遇上了移民入城高潮,车队只得缓缓而行,有时还受阻被迫停下,这使得押解者们心急如焚。165名囚犯中大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刑事犯,其中还有12名判了死刑、死缓或无期的重犯。如果在这人车如潮的转移路上发生犯人起哄、跳车、甚至夺枪等突发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开道车上的市局副局长陈斌和预审监管支队队长陈道中,拿起喇叭一路喊话开道;各车的随车武警和公安干警则个个圆瞪双眼,借着车灯密切注视着车内的一举一动。
车队好不容易行驶到埠河渡口,江水已将近300米长的通道全部淹没。车队涉水上船时,接连有4辆大客车的引擎在江水中熄火,4车犯人被困在江水中进退两难,情况十分危急。为防止发生意外,支队长陈道中和副支队长刘怀艮带头迅速跳进没过大腿的深水中,监护在车队两侧。部分公安干警也跟着下了车,准备合力将熄火了的车一辆辆推上船。当渡口工作人员知道车上是押解的犯人时,感到这非同小可,赶忙调来清障车,帮助牵引大客车上船。
所幸的是整个转移途中,犯人们都显得很安定,没发生异常。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洪水面前的求生本能任何人都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押解者们恩威并重的工作所致。
公安县看守所以管理规范被公安部授牌为“一级看守所”,今夜转移途中狱警们一边配合武警做到押解万无一失,一边细心对犯人予以人道主义照顾。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因车内温度高发生头昏,看守所教导员杨光玉立即拿出纯水和人丹,并亲自喂着犯人服下。
一位家住分洪区的犯人过江时看到满江的大水,担心起一家老小不知转移出来没有,忽然哭了起来。狱警呙陵池马上安慰说你们在押人员都能安全转移,你们家人就更会安全转移。犯人想想呙干部说得有道理,渐渐止住了哭声。
车队午夜时分安全渡过长江。这时,又一位市公安局副局长罗良荣早带领沙市区公安干警守候在沙市渡口,接应车队顺利通过沙市市区,驶上通往江陵郝穴的公路。车队终于连夜安全到达刚刚建成不久的江陵县看守所新址,成功完成了荆州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押犯的整体大转移。
在茫茫崇湖深处
这场大转移的骚动中,不管怎样的紧迫和慌乱,诸如人、畜、财产,或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药、液化气、汽油这些危险品,总还是可以转移的。但有一种东西却使人束手无策,望洋兴叹,这就是鱼及渔场。不过在此危难之际,到底有一位渔场场长和他的职工们,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明智的决断。
公安县是著名的百湖之县,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仅在分洪区内就有因古时地陷造成的崇湖,因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操练水军而得名的陆逊湖,以及与南闸毗邻的黄天湖等这些方圆十数里以至数十里的较大湖泊,先后以湖建成了多处较大的渔场。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崇湖渔场,位于分洪区腹地,是分洪区也是公安县最大的渔场,湖区面积30多平方公里,有养殖水面3000多亩,精养水面1000多亩,恒温养殖房12000平方米。这个远离集镇的渔场,虽年年也有过分洪转移的思想准备,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会成为真的。
当分洪转移令在分洪区层层传达时,县水产局副局长兼崇湖渔场场长肖国清正在武汉。昨天,他听说正在武汉的北京两家客商对崇湖发生兴趣,就连夜驱车赶往武汉与两家客商洽谈。今天下午正当双方为今后共同发展崇湖养殖业谈得很融洽时,家里传来准备分洪的消息。
场长愣住了。此时此地此种场面的他,除了像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分洪区人一样惊愕不已外,还多一份难堪和尴尬。因为这个消息来得太不是时候,他正在向客商描绘崇湖投资环境和前景。
愣过神来,场长很不好意思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两家客商。两家客商当然也一惊,好在人家很理解、很同情荆江分洪区,于是友好地暂停了这次洽谈。
下午5点,场长驱车离开武汉往回赶。年轻的司机起先很慌乱,把车开得像头狂奔的惊马。场长连连地提醒司机:不要慌,不要慌,今天晚上是绝对不会开闸的。
7点半钟,场长和司机赶到沙市渡口,渡口这时已被封锁了,除了驰援分洪区的部队和外县民工及其车辆能够过江外,其它一切人车一律不放行。面对这些毫不讲情面的警察,场长耐着性子陈述他本身就是赶回分洪区去组织转移的,有几千人正在等着他回去。他一边陈述一边还掏出身分证、工作证,好不容易达成这样的通融:车留在这边,人过去。
丢下车和司机,场长一个人挤上渡轮过了江。到了江这边的埠河,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已经到处乱轰轰的街道上找不到一辆去斗湖堤的客车。正在着急之际终于一辆出租车驶来了,他真像见到了救星似地抢上前拦住了车,心想即使花一千块钱也要快点赶回去。但车主坚决地说:这时就是给他出一万块钱他也不跑这趟车,谁知道水什么时候来?
但危难之中总还是有好人出现,最后一位开三轮“麻木”的师傅愿意冒险送他。
“麻木”摇摇晃晃一个多小时才把场长送到斗湖堤,不过到安全区围堤外就不再往前走了。场长问怎么不进城了呢?师傅提醒说:斗湖堤城内不是搞“双禁”,禁了鞭炮和“麻木”吗?场长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管这些?你只管往城里开,如果今天罚了款,罚多少我给你赔多少!
“麻木”终于将场长送回县水产局,场长感激地问要给多少钱,这位憨厚的师傅不好意思地说:平时从埠河跑斗湖堤是50块,今天真的是斗胆跑的,还不知回去时来不来水,就加个倍给100块吧。多好的老百姓啊,场长眼角一下子湿润了,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三张百元的票子,强制地塞给了师傅。并交代师傅说:回去时不要慌,今天晚上是不会开闸的。
这时已是晚上9点半钟,水产局干部和车辆已都奔赴所属各渔场组织转移去了,值班人员已给他临时租了一辆摩托正在等着,他匆匆了解了一下情况后就要往崇湖赶去。
值班人员提醒他吃点夜宵再走,他这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就拉上这位陌生的摩托车手一起到隔壁水产餐馆匆匆吃了点东西。与他很熟的餐馆大师傅给他倒了杯酒,说今天碰巧是他生日,他此时哪有心思应酬这个,不过平时不胜酒力的他此时倒是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真像一位赴难的壮士饮下的一杯壮行酒。
崇湖离斗湖堤近30公里,先要跑完20公里的斗(湖堤)闸(口)公路,然后还要跑数公里的湖区土路。斗闸公路是分洪转移的主要通道之一,这时一路上正星光灿烂,人车滚滚,大转移已出现高潮。好在这位半职业性的摩托车手胆大心细,在人车的间隙和夹逢中左穿右拐,跑到了闸口,接着又驰上一条颠颠簸簸的湖区土路。
摩托到达崇湖场部时,已是午夜11点半了。尽管浑身被颠簸得快散了架,场长仍然是感激地给了摩托车手150块钱。
夜色茫茫的崇湖,灯影人声正闹成一片。崇湖鱼场不仅包括4000多亩养殖水面,还包括3个村的数千亩农田,从事养殖和农业的人口共3000多人。场长赶到场部前,人员已开始转移,大部分就近转移到闸口安全区,小部分转移到县水产局。难的是水里的鱼和猪场里的猪不知怎么办好,干部们急得在地上跳。今年场里刚大养甲鱼,一个精养池里就放养了8000只,目前都已长到七八两重,计算起来总共已有150多吨。池里还养有种甲和种龟。与精养池配套的养猪场里,圈养着1700多头猪,已都过百斤,大的则已达到二三百斤。这样巨大的财产,怎能放弃呢?大部分干部主张拣大的甲鱼和猪打捞出来和抢运出去,能够挽回多少损失就挽回多少损失。
正在这个当口,一身风尘、一身汗水的场长回来了。场长脚还没立稳,就朝着一张张期盼的脸说:大家不要想打捞和抢运了,现在全县都是乱的,哪有人来买甲鱼和猪?
想外运又运不出去,什么车也过不了江。不如坚守在这里,再看一看,再等一等。
见自己的话使大家都沉静了下来,他又接着说: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留下来守场,与场共存亡。
于是,30多名党员和干部迅速忙碌起来:
他们将不能转移的较大的木船灌满水,然后压上石块,让它们沉到湖底,以免分洪后被大水冲走。又将一些小鱼划子三只五只的橇绑在一起,已备大水来后使用。
他们将粮食、油盐、炊具、发电机等等搬上三栋躲水楼,做好坚守的一切准备。
他们将精养池四周拉上电灯,以便夜里守望。
他们将猪场的圈栏打开,把一些两三百斤的猪赶出猪场,让它们暂时到野外去自谋生路。
他们在猪场放猪时,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位中年人站在圈门旁边,用手摸着被赶出圈门的一头头白花花肉滚滚的猪背,手里摸一头,嘴里数一头。当他摸到第8头猪,忽然放声哭了起来。这条44岁的汉子叫段春球,是场部副书记。连书记都哭了,在场的人也都跟着落下了眼泪。
场长这时也想哭,恨不得嚎啕大哭。他在崇湖已当十几年场长,比谁都更想哭。但此时此刻作为此地的最高指挥者,不能也没有时间哭。现在,就在一片哭声中,他又宣布安排场部袁副场长赶到崇湖对岸的东北湖分场去,组织那里的转移和留守。
听说自己的丈夫要单独到东北湖去,副场长的妻子哭着不放丈夫走。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见面呢?但现在是什么时候,怎能和领导的安排讨价还价?最后的结果是妻子跟着丈夫一起上了路。
这时已是下夜了,副场长跨上一辆摩托,妻子坐在他身后,夫妻双双突突突地向着夜幕深处驰去。过去是妻子送郎打东洋,今夜在这茫茫崇湖则是妻子陪郎上战场了。
一个举镇而去的乡镇
拙著《荆江分洪大特写》曾写到过分洪区内一座几经衰荣的小镇:这里有两条小河交汇,形成一个三汊河口。一两百年前有几户渔家来河口施放麻豪捕鱼为生,由此以麻豪口得名。当大物理学家王竹溪在附近的潭子湾出生时,这里已是公安县虎东地区一处繁华重镇,王竹溪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的公立小学度过的。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移民时,由于这里地处分洪区腹地,所以几乎是拔地而去。1954年分洪后,经过洪水的荡涤,原先的镇址变成了一片旷野。但以后由于长达40多年没再分洪,过去的主人们又陆续回来了,一个新的镇子又在原先的镇址上冒了出来。这里不是安全区,没有构筑围堤,全镇一览无余地袒露在洪水的威胁下,但侥幸的心理和发展的欲望,使新的麻豪口镇在这分洪区腹地日新月异地生长。可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40多年前曾经拔地而去的镇子,想不到今夜又经历了一次上下一体的举镇大转移。与40多年前不同的是,今夜是只走人,只急急地走人。
麻豪口镇镇委副书记张光蓉——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同志,经历了今夜举镇大转移的全过程。女书记在黄水套防守堤段上参加紧急转移动员会后,奉命下堤赶回镇里。这时天已经黑了,堤上已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正在着急之时,堤那头驶来一辆摩托,女书记挥手将摩托拦住,可是车上连同摩托车手已经坐有3人了。好在8·6之夜的陌路人都成了好心人,女书记还是挤上了车。由于怕她从车上掉下来,后座上的两位男子只好把她夹在中间。夏天的衣裤都穿得很单薄,年轻的男女这样挤着实在太难为情了,但在这8·6之夜哪里还讲究这些。
女书记赶回镇委镇政府时,见院子里站着一群人,已先一步从堤上赶回的镇委书记正在高声讲话,原来这是在开镇机关战地动员会。镇机关干部一部分安排下村随村转移,一部分安排督促镇直单位转移后随镇机关转移,她被告知去江南村随村转移江北,她在镇机关工作的丈夫随机关行动。“站”地会转眼间就结束了,匆忙中她只与丈夫打了个照面,得知小孩已被姑姑家接走,也就没再顾得进就在机关院内的家去看一眼,又返身走出了机关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