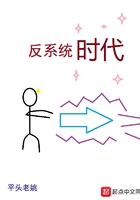他这才急了。妻子现在不在家,借住在斗湖堤亲戚家做烧烤生意,只有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在家看屋放牛。这可怎么办呢?他在堂屋里转了几圈,堂屋里堆着新打的两三千斤稻谷;又跑到屋后的橘园去望了望,橘园里挂满着已有七八成熟的果实;最后又走进自己的卧室里出了一会神,卧室里有他两书架心爱的书。磨蹭了半天,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只保人和书,再加那条牛。财产丢了就丢了,以后还可以再来。就是老婆丢了不也是来了新的吗?我们的“沉杞庐”主人这样一想,才又变得不慌不忙起来。
他先交代两个孩子沿着门前的这条公路,一直往前走到斗湖堤亲戚家去,叫妈妈赶快骑自行车回来收拾吃的用的。
接着去外面牵回了那条牛,暂时系在大门前,等会带走。
然后,他开始在卧室一五一十地清理起两书架书籍报刊。这恐怕是在33万人流的转移大潮中,惟一的一个不顾家产只要书刊的人。
屋外已经天黑了,堂屋里没有图像的电视机仍然在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刚才的那个声音:“……在此危难之际,县委、县政府要求分洪区广大干部群众……”屋外的公路上开始滚过一阵接一阵的人声车影,但他在卧室里不声不响地清理着他的宝贝书刊,似乎忘记了室内外的一切。
不怪他一拿起这些书就忘记室内外的一切,因为这其中真有不少好书。事后笔者在他家见了这些书也爱不释手,更惊叹一位农民家里竟藏了这多好书。诸如《中国楹联大典》、《中国对联大辞典》、《楹联丛话全编》等等这些沉甸甸的大部头,还有多年来成套的《对联》杂志、《中国楹联报》等等,还有《辞海》、《辞源》之类工具书,这套《辞源》竟还是民国版的哩!笔者接触过的国内以至国外各个层次的藏书人可谓不少,但还没有在哪个家里更没有在一位中国农民家里,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的关于楹联的书。
据说风暴的中心是平静的,浪涛的深处也是平静的。现在分洪区腹地的“沉杞庐”这间小室,就像是处于风暴的中心和浪涛的深处,的确静得出奇。这真是个天下少见的“迂鬼”啊!他本来已找来了一大堆塑料袋、蛇皮袋(编织袋)和装谷的麻袋,准备快点把这些书收好。但他拿起这些书来时,一种惜别之情涌上心头。这就像母子惜别之际,妈妈抱着孩子的手久久不愿放下一样。像这本《中国楹联大典》,是从遥远的北京寄来的,是那年百亭征联的奖品,他一拿起就不愿放下了,真想随身带走。但仅这本书就厚达半尺,重有好几斤,这怎能带得走呢?他不禁顺手翻开了那硬硬的精装封面,默默地看着扉页上的获奖印章。
在斗湖堤听到了转移消息的妻子,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一见他还在房里不声不响地翻书看,而家里的东西一样都没有收,忍不住火了他几句。他则不气不恼地说:广播里广的是“舍小家,保大家”嘛!一屋的东西怎么收?只要一家人跑出去就行了。妻子又说:“那就快点走呀,家家户户都快走光了。”他又扬了扬手里的书说:“别的不收,它们可要收哇!”妻子知道这些书是他的命,就催他快点收。这时村组的干部和上面的工作同志也来催了一遍,他这才开始往袋子里装书。
不管是妻子催还是干部催,他还是要认认真真地把书一本本的清好。那些一般版本的平装书,他就先装进蛇皮袋,然后又套上麻袋。像《中国楹联大典》这样的大部头精装书,他则先裹上一层塑料袋,再套上蛇皮袋,最后装进麻袋。两书架书装了好几麻袋才装完。最后一遍上门来催促的县里的同志见这家人光收了几麻袋书,觉得很奇怪。村组干部告诉县里的同志:这是个有名的“书迂子”,他可有才学呢!
现在时间一晃已是下夜了。在妻子的帮助下,他把几麻袋书背到隔壁的一栋二层楼房,寄放在二楼的平顶上。见人家的平顶上还可以放东西,夫妻俩才又抬了几麻袋粮食和书堆放在一起。而那台高压包坏了的电视机,最后懒得搬了。
终于到了最后撤离“沉杞庐”的时候。临出门时,我们的“沉杞庐主人”在屋后橘园里特意摘了10个还是青皮的橘子,拿上刚才清书留下的一沓近期的《对联》杂志和《中国楹联报》。妻子牵着牛,他推着自行车,夫妻双双踏上了往斗湖堤去的公路。眼睁睁地丢弃这好不容易兴旺起来的家,妻子忍不住一路抽泣。而他则一路上都在想:水来了,该不会漫过二楼平顶吧?该不会冲走那几袋书吧?那些楹联书是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
他们魂断在转移路上
下面是分洪区内一位乡镇文化站长,专门向笔者提供的一个故事:
在8月6日傍晚开始的转移潮中,从曾埠头乡和杨家场镇之间的杨麻河边走过的人群,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戴着草帽的人孤零零地站在河心里,不知在干什么。当时人们匆匆赶路,并没有把这个站在河心的人放在心上。可是第二天,有人看见这个人还是站在这里。第三天,还没有见这个人有什么动静。终于有过路人走下河滩,结果河滩上弥漫着一股尸臭,原来这是一个死人,一个站在河心淤泥里没有倒下的死人。
原来6日下午,杨家场镇仁和村一位老汉带着儿子,去嫁到曾埠头乡黄桥农科所的女儿家有事。仁和与黄桥隔着一条杨麻河,往常要绕道从一座桥上走过去。今年入汛以来长期未下雨,虽然外江大水,内河却大旱,这杨麻河干得快底朝天了。父子俩因贪近路,就从这杨麻河的浅水淤泥中水过来。父子俩刚过河,就看见河岸上拥过来一群拉车挑担的人,父子俩一打听是要马上分洪了。儿子反应得快,返身又过河要先赶回去搬家,并交代父亲快去通知姐姐。儿子一转眼就走了,父亲可能是更放心不下儿子这头,也跟着返身要再过河去。大约累了、急了、热了,大约老汉本身就有高血压、心脏病之类,等老汉再次涉足河心的浅水淤泥中时,一口气没接上来,猝死在河心里。由于老汉两腿陷在淤泥中很深,他就这样孤零零地定格在河心中了。
33万人的星夜大转移,你碰我一下,我撞你一下,甚至像那位倒下又站起来的妇女一样被牛踩上几脚,这都不足为怪。使人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相信的是,在这次持续通宵的转移过程中,好几个乡镇都发生了移民猝死。8·6之夜市分洪前指就一连接到这样几个报告,有关单位请示如何处理?这可难住了指挥部人员:这是分洪预案中没有设计的,是人们没有预料的。前指只好这样回答:暂时先由自己处理。据说有的尸体只好草草掩埋在路边的棉田里,有的尸体则被寄放在斗湖堤城郊的火葬场。
这里,让我们沉痛地列举出一些魂断转移路的老少乡亲吧:
埠河镇联合村一位25岁的青年妇女转移中收拾东西时,想带床棉絮。而棉絮高高地挂在屋梁上,她就搬来了梯子。她万万没有想到屋梁上横着的一条电线,已被该死的老鼠咬破皮了,裸露着一截。当她爬上梯子伸手去取棉絮时,不小心碰着了这根裸露的电线,浑身一阵痉挛,从梯子上摔下地,当即身亡。
该镇魏家洲村一位82岁的老太婆,转移时本来已走出了家门,又忽然想起还要带件夹衣,就又颠着一双小脚转回来爬上了自家的小楼。等她老人家拿了夹衣下楼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在了水泥地坪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该镇西流村一位年仅四岁的小孩,转移时被父母抱上一辆拖拉机的车箱。车箱里已装满行李,小孩就坐在行李堆上。父母交代他手里抓住行李不要乱动,说罢又进屋搬东西去了。不一会小孩摇摇晃晃地打起瞌睡,结果从高高的车顶上滚落下来,可怜的孩子哼都没来得及哼一下就过去了。
该镇复兴村一位60岁的老汉转移时由于赶路心切,竟不顾自己的年龄骑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后面还拖了一辆板车。由于路上拥挤,他只好左弯右拐,不小心一头撞在了路边一棵树干,脑袋撞开了花。
夹竹园镇北湖养殖场的一位38岁的外地养鱼人,本来是个血吸虫病人,已到了晚期。得到转移通知后,他一口气疾行十多公里赶到夹竹园安全区,以为这下安全了。可是由于一路上的劳累加闷热,他一到达夹竹园就倒在安全区围堤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事后,荆管局列出了一份《分洪转移死亡统计表》,有名有姓的死难者就有64人(包括以上列举的几人),还有没列出姓名的22人,共计86人。当然这86人并不是都是魂断在8·6之夜,这是整个分洪转移期间的一个死亡统计。
本书初稿本来已照录了这个死亡统计表,后觉得列表公布这些死难者名单似乎有点残忍,因为这对所有死难者亲属都是不堪回首的一幕,故将统计表取消了。但又感到不能不公布这些死亡者名单,因为历史在记下公元1998年8月6日之夜的时候,不能不记下这些为此夜付出最大牺牲的魂灵。犹豫再三,还是列举了以上几则死亡事例。
但愿这些魂断8·6之夜的不幸者们安息,特别是那位正值青春年华的25岁少妇、那位还不谙世事的4岁幼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