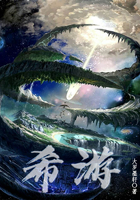张虎地来了一家新人家,据说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干部,全家大大小小一共五口人。渠队长安排他们住在赵老师家的西房,就是原来大食堂的伙房。一辆汽车拉着家具,缓缓停在赵老师家大门口。拴住和几个伙伴被安排搬家具。人们好奇而热心地帮助这家人家,搬家具的搬家具,折箩屋子的折箩屋子,不一会儿就收拾停当了。
渠村长像开会一样地面对着大家郑重地介绍说:“这个是从省城来的干部,姓王,叫王大兴”
王大兴谦虚地点点头,“谢谢大家帮忙。”
渠队长又指着女人说:“这是王大兴的老婆,姓海,海之花。”
一丈青从蒙古包戳了一筐子干粪,走过来,狠狠地瞅厌了一眼渠队长,说道:“海大姐,咱们进家点着火烧炕,别操理他。”
海大姐跟着一丈青进了家,“咱们这里主要就是烧牛马粪,海大姐你肯定觉得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这里没有炭,就烧这个。你看啊,点着柴火,把粪放上去,拉风匣,就可以了,烧炕做饭都这样。呵呵呵。”一丈青边做着示范边说。
海之花嗫喏着:“俺来试试。”说着坐在灶坑的木墩上,刚把粪铲伸进灶膛,一拉风匣,呼的一股烟雾喷了出来,呛的海之花急忙跳了起来,一丈青赶忙帮助海之花拍打身上的灰尘,“哈哈哈,你铲的粪太多了,一下子压上去,猛的一拉风匣,肯定要倒扑。你看着啊,这样的慢慢的拉风匣,铲起粪均匀地撒上去。今天得多多地烧,不然炕冰凉的怎么睡觉呢?”
海之花又坐在木墩上,胆怯地看着灶门,不知所措。一丈青说:“海大姐,难为你了,既然你来到这里,就得学会这样烧火,不然一家子怎么过日子呢?”在一丈青的鼓励下,海之花再次拿起粪铲,左手拉着风匣,这回好多了,灶膛的火呼呼地着着。
“好了,我给你再戳一筐粪,你就这样烧水、做饭吧啊。”一丈青说着将筐里的干粪倒在灶坑。干粪抖露起的粉尘弥散着,海之花捂着嘴勉强地拉着风匣。
王大兴送走人们回到家里,看着老婆在烧火,吃惊地问道:“你这么快就学会了?我来吧,你和孩子们洗洗脸,咱们做饭。”他想,看来困难还是最有教育能力的,在它的面前人的不得不自我提升,而去应对它的挑战,甚至于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也很快能够适应。
饥饿真正地来到了。
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苣荬菜成为人们的救命菜。
苣荬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每年春天伴着坝上的寒风和风沙它会早早露出尖尖的紫绿色的叶瓣,显示生命的不屈,就像生活在坝上的人们一样坚定倔强。传说中的苣荬菜神乎其神,有一位将军在率领士兵征战中缺少粮草,关键时候将士就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吃苣荬菜,最终度过难关。而真正看到它是却又其貌不扬,贫瘠的土地到处都有它的身影,一片连着一片。人们锄地时会毫不犹豫地锄掉它,但是还是要收起它的叶子作为猪的食物。坝上人有吃苣荬菜的习惯,尽管有些苦味,但是人们认为那种苦就是甜。有去除身体里火毒的功效。年景好的时候人们挖来苣荬菜的嫩芽拌凉菜,等到苣荬菜长大时,用叶子和山药蛋丁做成馅,用莜面包成饺子吃。而灾荒年不少人家都是上顿下顿地吃苣荬菜团子,里边和少许莜面。就连往年晾晒在房顶的喂猪的山药渣都掺进苣荬菜团子,米面成为人们的奢望和记忆。
二柱子家了没有可以供他上学的颗粒粮食了,二年初中也熬到了头,他回到家里,在生产队劳动。果儿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往在县城到张虎地四十里路之间,孤独的她甚至也打算就此打住,不再念书了。她的想法一经说出,就遭到来自陶老师的极力反对,果儿爹娘看到陶老师坚决的态度,迅速由犹豫不定转变为坚决反对,站在果儿的对立面。果儿在家里也成为孤独的人了,她哭着抱起书香说:“姑姑成了臭****,人不理狗不爱,就剩下你们两了。”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陶老师眼泪花花地说:“哭也没用,必须念书。爹娘你们不能答应她啊!这件事,我做主了。”
果儿狠狠地瞅厌了陶老师一眼,说:“还是我老师呢,都是你搅和的。”背转身子不理陶老师了。
最终,孤独的果儿怀着寂寥的心情走了。一路上她郁郁寡欢地低头猛蹬自行车,连个说话的也没有,不知不觉来到了黄花滩,阴森森的沙包就像一个个刚埋了死人的坟茔。果儿不由得浑身冒起冷汗,四处张望,恐怖压抑在她的心头。这时,她想起家里人的态度,好想大哭一场,她又想到二柱子,有他我多么放心啊!刚转过山洼,远远看见有车,果儿就像大难中看到获救的希望一样,赶紧用力蹬着车子。不一会儿,追上了车,原来是季洁和他爹季老师,季老师赶着毛驴车送他宝贝儿子上学去。
季老师首先看到了来自后面的果儿,说:“果儿,怎么是你一个人,二柱子呢?”
果儿喘着粗气说:“他初中毕业就不念了,现在就我一个人了。”
季洁说:“看你累的,你上车,我替你骑自行车吧。”
季尚文吆喝着,“吁!吁!”毛驴车停下来,季洁下了车接过车把,果儿上了毛驴车。季老师又吆喝道“驾,驾”,小毛驴甩开四蹄“嘚嘚嘚嘚”一路小跑起来。
“果儿啊,以后就和季洁相跟着,省的一个人寂寞害怕。下个礼拜****两骑你的车子回家,等礼拜日回学校时你在家等着,让季洁去找你一起来。”季老师对果儿说道,扭过头斜着眼瞟了果儿一眼。
果儿这一会儿才静下心来,她擦着汗水,回答:“对,季叔叔说的对,我一个人不敢来,以后二年高中就和季洁相跟了。”
“就是啊,都是同学,相跟着有个伴儿,黄花滩这截路就是让人害怕。”季老师不紧不慢地督促毛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