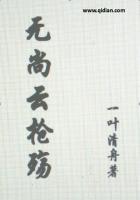面对这种人情冷漠的现状,我们有必要重读《年轮》,让那久违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意,一点点融化我们业已冰封的心。文革、上山下乡、知青、北大荒、返城……这些词汇已经与往昔岁月一起渐行渐远,但是,那些特殊年月里呈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是狂沙吹尽之后留下的金子,成为当代社会人们思想与精神觉醒的参照。
《年轮》里的六个人,吴振庆、王小嵩、徐克、韩德宝、郝梅、张萌,小学及初中六人都是同班同学,共同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痛苦的饥馑年代;然后裹入文化大革命,再身不由己地被命运的大手扫向“广阔天地”北大荒去“炼忠心”。十年之后,他们满怀着希冀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城市,可是这些将青春当做武器投掷出去,却连一枚引以为荣的纪念章都没有获得的男人女人,满脸镂刻着失落、苍凉和幽怨——阔别的城市已经没有属于他们的位置。他们从一无所有绕到一无所有,像钟表的指针从零点又绕到了零点。然而,青春已成为生命之树上最后一片落叶,被岁月裹挟着凋零无踪。
其后,六人的生命年轮在挣扎与徘徊中一点点向前延伸,他们淹没在城市的人海茫茫之中,那么渺小,那么不引人注目,只有解剖一座城市,才会从城市的横断面里,发现他们确实运行着,走出了千差万别的轨迹。
整部《年轮》,由始至终,弥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一种含泪的涩涩的温暖。
饥饿的少年岁月里,每个人都饿得脸色菜黄身体浮肿,韩德宝将来之不易的一块喂军马的豆饼分成一个个小包,给自己的好伙伴们每人吃一点。
中学岁月里,吴振庆的父亲拉人力货车时受伤,断了养家糊口的营生。徐克和王小嵩在如火烈日之下,汗如雨下地帮吴振庆拉车养活一家人。
知青岁月,在荒无人烟的北大荒,王小嵩考上了大学。吴振庆、韩德宝、徐克都在不同的连队,他们各自在齐膝深的大雪地里,抵挡着悚人的狼嚎声,连夜滚爬了近百公里,会合在小嵩搭乘的车子必经的路口,可是东北的严寒让所有的车窗都结满了霜,他们连小嵩的面也没见着,车子就无情地离去。
返城后的岁月里,曾经遭受凌辱,喝农药轻身未遂而烧坏嗓子变成哑巴的郝梅,她唯一的女儿芸芸得了骨癌离世,是这些朋友在她万念俱灰时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张萌,这个表面看起来冷漠而高傲的女子,其实内心隐忍着深重的痛,她的心有不为人知柔软的一面。父母在文革间相继离世,她由一名高干的女儿变成经风遭雪的北大荒女知青。为了返城,她含辱忍垢。为了救出被关拘留所的吴振庆,她四处奔波。
城市,像一个围棋棋盘,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哭有泪的人就是其中的棋子,而摆布这个棋局的是一只只无形的大手,这无形的大手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时代,或者是命运,或者是生活本身。
《年轮》是一部电视剧本,因此它采用的语言及叙述方式都是平实而朴素的,没有艺术化的拔高和诗化。而恰恰是这种平实,让书中的一个个人物,身犹在眼前,言犹在耳边,他们笑的时候,我们跟着笑,他们流泪的时候,我们也会眼眶润湿。不仅是这六个人不渝的友情让人动容,就是王小嵩的母亲,“捡”来的“小姨”、吴振庆的父亲、徐克的父亲、王小嵩的邻居三奶奶,这些处于城市最底层的人们,都有一颗卑微却善良的心。
时代的巨手翻转腾挪,夹扁了无数像吴振庆、王小嵩、郝梅这样的活标本,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像身不由己的鱼儿,被时代的巨浪冲上无水的沙滩而搁浅,腮口一开一翕,艰难地喘息跳腾,却只留下满地残碎而伤痛的鳞片。
在整体荒凉压抑的一个时代里,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爱”,像寒夜里的一星烛火,纵然照不远多少路,却给人以温暖和希翼。
星移斗转,苍狗白云,那个特殊的年代已遥远地离开了我们。而那群“被耽误的一代人”并没有远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的长辈,他们会常常抚着自己渐已灰白的头发告诫我们好好读书,因为他们那时无书可读啊。
他们也许还经历过“下岗”、“内退”的阵痛——“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看着他们已显佝偻的身影重又走进冷冷的风雨,内心五味杂陈。
有人说,当代人“爱”的群体意识已渐渐沙化。这种沙化,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的。爱与被爱,是一种内心的感觉,缺少爱的人,像走在沙漠里缺水的人,以为自己能喝干一口井,其实,我们只需一瓢水就够了。
《年轮》,就是那瓢水,喝过,你会发现,心里原本对爱的感觉已经漫漶不清,而在这瓢清凉而略带苦涩的清水滋润下,逐渐变得清晰可辨。
青春,背负着伊卡洛斯的翅膀
文/纳兰泽芸
看白先勇的《孽子》,看到阿青、小玉、吴敏、老鼠这一群潜沉在黑暗深处的少年,一次次想上升到白日之下,去感受人世的温暖和爱,却一次次被灼痛、伤害时,我都会想到希腊神话里的那个伊卡洛斯,他为了逃离寂寞的孤岛去追寻自己的家乡,背负起用蜡和羽毛制作的翅膀,在迎向光明飞翔的时候,被太阳无情的灼伤,翅膀融化,伊卡洛斯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淹死。
伊卡洛斯对光明和温暖的眷恋和向往,何尝不是那一群在台北新公园最深最黑处逡巡着的迷茫少年,他们对家、对人世间的温情无比渴望。但是,他们却是“见不得光”的一群人,他们遭到了亲人、家庭、学校、社会的集体放逐、不齿和唾弃,只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一群具有同性倾向的“败类”。
在大人们的眼里,他们还是孩子,十七岁,含苞待放的好年华。“孩子”,这两个字就包含着无限的怜爱与疼惜。因此,白先勇在扉页的大片空白里只留下这样几个字:“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然后,整部作品的正文第一行:“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这个十七岁的“我”,就是阿青。
父亲顶着一头苍苍的白发,瞪着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不停挥动着手里的一杆破枪,阿青就在父亲嗄哑的“畜生!畜生!”的怒吼里被逐出家门,不知不觉汇入到那个特殊的王国——台北新公园长方形莲花池周围的一小撮土地,这里被公园里的热带树丛层层遮掩。这个蕞尔小国,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白天他们到处潜伏着,像冬眠的蛇,黑夜来临,他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像一群蝙蝠在夜色里扑腾。
阿青、小玉、吴敏、老鼠、阿雄仔、龙子……这群特殊的人,每个人的心里都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们的被放逐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孝亲恤幼,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思上进,他们其中有些人足够优秀,可是他们同样被社会放逐唾弃得无路可逃,只好沉潜到这个最黑最深的角落。他们是一群传统道德的“叛逃”者,在外面的社会,他们也想得到一丝阳光的温暖和恩泽,可是他们得不到哪怕一点点,于是他们转而梦想在黑暗的深处寻找一丝温暖,梦想在这片黑色泥沼里,能够让心里开出一朵明净的花。
他们迷茫、孤苦,他们也曾挣扎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离经叛道”,在被世人唾弃的同时,他们桀骜不逊的笑面之下,是一张张泪水纵横的脸。也许就像公园里的“元老”郭老说的: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是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孽”啊……
他们在外面的世界得不到阳光和温暖,就在那个黑暗的小世界里互相取暖,然而,他们又像相互依偎的刺猥,离得远了感到冷,离得太近刺得疼。他们的内心敏感而脆弱,渴望爱与被爱,一旦被伤害,就会比常人痛得更甚。
阿青因有同性倾向而被学校开除,这让曾经是军人出身的父亲颜面尽失,痛心疾首,父亲兵败之后逃到台湾变得潦倒困窘,小他近三十岁的妻子离家出走,小儿子得肺炎离世。
阿青的家是巷底最深处一间终年射不进阳光的矮屋,终年发着霉,自从母亲出走之后,父亲常常半夜醉归,路都走不稳,苍老灰败的脸上哭得歪斜悲怆,弟弟的突然离世又给父亲以沉重打击,从此更加消沉。母亲因为生阿青时难产差点丢命,从小就不喜欢阿青,只喜欢弟弟,阿青曾经嫉妒得咬弟弟的膀子。母亲弃他们而去之后,内心空落的阿青将爱转移到长相极像母亲的弟弟身上。阿青的感情如同浮在空中的一粒尘埃,没有落点,他想爱母亲,母亲不爱他;母亲走了,他想爱弟弟,弟弟却夭折。
吴敏没有家,从小母亲就离家出走,后来父亲坐了牢,因此他无比迷恋张先生那个家,他住在张先生家到处擦洗,收拾得一尘不染,最迷恋的是那个贴着天蓝色磁砖的洗澡间,他泡在里头,一直舍不得爬出来,泡得一身红通通。因为他与父亲租房子,从来没有一个洗澡间。后来张先生赶他出门,他提着一个破提包四顾茫然,竟割了自己手腕。就算这样,后来张先生生病,他还是去悉心照顾。
老鼠从小没有父母,跟哥哥一起长大,严酷的生存环境养成了哥哥怪戾的脾气,一不顺心就将老鼠揍得鼻青脸肿。可是当阿青问他既然哥哥那样打他,为何还不离开时,老鼠说:“我已经习惯了跟他在一起”。为了得到一丝庇护或者亲情,就算是经常挨打,也不算什么。
小玉的母亲是一个下等酒吧的吧女,小玉从出生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他还没出生亲生父亲就去了日本,一去不返,他只知道父亲的一个中国名字。小玉念念不忘就是他的“樱花梦”,他梦想着凭自己的努力到日本去寻找亲生父亲。当他终于费尽周折到了日本后,茫茫人海,寻父的希望是如此渺茫,他在小饭馆打杂,睡在狭小干货货仓里,被咸鱼等东西薰得香臭不分。
父与子,这原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一种血缘关系,然而在《孽子》中,却因为儿子使父亲“颜面尽失”,使原本最亲密的关系充满了伤痛。阿青的父亲摇摇晃晃地挥动着破枪,用颤抖嗄哑的声音喊:“畜生,畜生!”龙子的父亲将儿子放逐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悲愤地告诉儿子:“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傅老爷子的儿子阿卫是一名英姿勃发的优秀军人,却在二十五岁那年被发现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他苦苦得不到父亲原谅,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选择了结束大好年华。丧子之痛让傅老爷子猛然醒悟,他痛悔了大半生,如果他当时在儿子最无助的时候没有对他那样绝情,儿子可能就不会无路可走。
傅老爷子后来的大半生,都投入到救助与儿子一样的迷途少年之中去,还尽全力救助孤儿院里的伤残儿童。傅老爷子后来醒悟到,那些有同性倾向的孩子,绝大部分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成长环境息息相关,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在缺少亲情,更缺少母爱的环境长大。不管他们的同性倾向是与生俱来“血里带来的”,还是后天缺少爱的环境造成的,本质上终究不是他们的错。然而,他们却遭到家庭与社会的一致唾弃,只能躲入最深最黑处踽踽徬徨。
然而,他们疼痛,他们的父亲更疼痛。傅老爷子说:“你们父亲受的苦,绝不会在你们之下。这些年你们在外面受尽了折磨,但是你以为你的苦难只是你一个人的么?你愈痛,你们的父亲更痛!龙子走后,他父亲的头发不到半年就盖上了一层雪!”可是,即使父亲们痛不可耐,却不肯原谅和收容自己“叛逆”的儿子。也许他们内心已经愿意原谅,可是社会却不允许。他们就像伊卡洛斯的翅膀,在黑暗中也许还能残喘地扇动几下,一出来,强烈的光就会将他们灼伤、融化,然后毁灭。
白先勇有一支满含悲悯的笔,他也曾说过:“我写作是为了表达人类内心无言的忧伤,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文字”。他的其他作品,不论是“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台北人》,还是“寂寞梧桐庭院锁清秋“的《寂寞的十七岁》,他都用一支含着淡淡伤感却并不阴郁的笔来描画这一幕幕的浮世绘。读他的作品,不再感觉阅读是一种消遣,仿佛在那深邃之处,有一线光照在心里若隐若现。
作为抗日名将白崇禧的儿子,注定了他从小看尽繁华。然而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的仕途最高端时,年幼的白先勇却因为患“肺痨”而屡屡与死神擦肩而过。“肺痨”是烈性传染病,需要严格隔离,一边是车水马龙的声色繁华,一边是孤寂无比的童年。这样的特殊经历养成了他敏感、细腻而悲悯的气质。看他年轻时的照片,心中惊讶一个男士竟能长得如此俊逸清朗。即使步入古稀之年,依然淡定自若,笑容清浅。
他说,日子好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即使他声誉如雷,在台湾或在海外,他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到了古稀晚年,看到自己钟爱的昆曲日渐颓落,他想尽自己有生之力拯救这个剧种,才开始逐渐接受媒体的一些访问,因为昆曲需要媒体的宣传才能重焕生命力,他不忍心看到昆曲里美丽的烟波画船、雨丝风片就此消失。
像对昆曲充满悲悯之心一样,在《孽子》中,他也时时用一颗悲悯之心去看待这些孩子,让他们在黑暗角落之中,依然散发善良与人性的关辉。阿青在寒冬之夜,将呆傻的流浪孩子带回,给他吃给他喝为他换衣服,孩子丢失了他四处寻找;龙子在纽约曼哈顿高楼的阴影里,救助了一个个可怜的流浪儿,又想尽办法为小金宝的畸足做手术;傅老爷子离世,是他们这一群“叛逆”者细致妥贴地安排了后事。
这群青春鸟,他们的青春虽然背负了伊卡洛斯那不被光亮接受的翅膀,然而,青春毕竟还是青春,翅膀不能飞翔,善良的心却还能飞翔。
他们善良的光辉,像一轮月亮挂在湿煤似的夜空,虽然不甚明亮,却依然令人感动。
让蝴蝶从此不再流泪
文/纳兰泽芸
“奥斯威辛集中营”这几个字只配与“地狱”、“毒气室”、“焚尸炉”、“灭绝人性”相联。但是,能够将悚慄的罪恶与美丽联系在一起的,是集中营里那些幼小但美丽的灵魂——那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偷偷写诗的孩子们。
六十多年前的1940年,似乎时光并不是太遥远。“奥斯威辛”这四个字,在德国纳粹到来之前,只是波兰一个宁静而安详小镇的名字,蓝天白云,静静流淌的河流。但自从纳粹在这里建立了庞大的集中营之后,它就代表了一种“心灵不可承受之痛”的符号意义。美丽,从此与奥斯威辛绝缘,取代的,是血腥、是屠杀、是惨烈。
德国纳粹在奥斯威辛使用的“现代工业化”的方式屠杀人类,其惨烈程度震惊人寰。五年之间,这里屠杀了400万人!
或许,作为数字,400万是抽象的,但是,你可曾想过,这是一个个有呼吸、有心跳、有思想、有哭、有笑、有歌、有泪的人……
这400万里,有一部分就是天真浪漫的儿童。也许我们会天真的想,对于那些纯洁而无辜的儿童,纳粹应该会不忍残害吧。可是,我们错了,他们一样被推入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只在人生路上走过短短十年左右就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