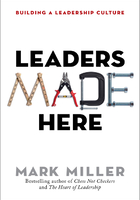我们从露营旅行一回到旧金山,加里的一位朋友就前来问候,她问我喜不喜欢露营。我觉得她在听到我热情洋溢地说我是多么喜欢露营时好像很惊讶——那是一项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十分吸引我的运动。
“啊,真的吗?”她的语调和肢体语言掩盖了她的真实反应。我能强烈地感受到她听到这些话一点都不高兴。她和加里以前曾经一起出去露营,而她似乎很愤恨我把他从她身边带走了。
她坚持要我们星期六,即第二天就出发,到尖峰石阵国家公园去过周末时,我们刚开始把露营装备搬进房子里。那是加里最喜爱的地方之一,按照苏菲派文献里对于上帝的称呼,那里平和、有灵性,且与他心中的挚爱相通。他想将自己的骨灰撒到那个地方去。
尽管从我们的露营归来经过长途驾车他已经非常疲惫了,加里还是含糊其辞地同意了。我们再一次上路,不过好在是他的朋友开车,而加里作为和我一样的乘客,坐在他自己车的后座上休息。加里的另一个好朋友杰里,同我们一起来了,他坐在前面。我很高兴能和加里独处一段时间。
通往尖峰石阵山顶的路不止一条。每一条都漫长而陡峭,而加里的选择是——和同杰里一起——走那条最难走的小路。如果想要在他们选择的路径上攀登,徒步者就必须从停车场开始就进入一片原始区域,穿越一个异常幽暗、巨石遍布的洞穴,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落脚,并且凭借一个好手电筒与石块儿们竭力周旋。有些石块儿是如此巨大而且相隔太远,我的腿没法从一块岩石够到另一块岩石上。有时候,加里会帮助我,他走在前面,然后再转过来拉我一把。必要的时候,他也会绕到我后面把我推上去,让我有足够的前进动力爬到下一块巨岩上。当我们四个终于穿过了山洞,加里那位咄咄逼人的女性朋友——就是要求我们到尖峰石阵来的那位——坚持要我和她走在后面。我对于要和她单独度过那一天而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在前一天我看到她对于我很喜欢和加里一起露营的反应之后。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而且想要回到停车场还有漫长的徒步路程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我问道:“除了穿过山洞的那条路以外,没有其他线路能到达停车的地方吗?”
没有。
当我们再次临近那个巨石遍布的山洞,徒步线路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毒蜘蛛,这令她很感兴趣,但我需要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她完成了对蜘蛛的观察之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加里病了,你能自己从这里走出去吗?”
“当然了。”我回答道。
“好吧,你现在知道他已经病了!”
那可真是好极了!我的膝盖开始颤抖,而且听到方才的这些话以后我变得呼吸急促。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那个山洞,没有加里的帮助与鼓励,我们必须得穿过去,才能到达停车场。我经受住了这一艰苦的考验,然而我的焦虑在飙升。
不,我不知道加里现在已经病了,我想要他立刻出现在我身边。他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生病的迹象,而且他也没对我说过什么。天色渐晚,我希望他能安全地回到平地上。暮色褪去,月亮已升了起来,还是看不到加里和杰里的影子。我异常焦虑而且担心得要死,因为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而痛苦的空虚感。仿佛他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并不是觉得他是死在了深山里。那是一种他在此之前就已经逝去的感觉,而我没有陪在他身边。我只是一定得让他回来,以那种注定的方式一同走完我们的人生。我很难去接受艾滋病正在把他从我身边夺走这一事实,而且我也难以想象人们是如何才能承受住因意外或外力而突然失去自己心爱之人的打击。
若不是有那晚那一轮圆月散发出的光芒,这两个男人就只能借助他们手电筒的一小束光亮在那危险而狭窄小径之中开路。然而在他们到来之前,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命令我在停车场等待,而她一路上山去寻找加里和杰里去了。我对她的行为举止感到很愤怒,我也非常关心加里的命运。就在她把我独自一人留在停车场之后不久,他们三个就回来了,而我急切地想要加里再次和我回到汽车的后座上。
在回旧金山的途中,加里把腿伸出来搭在我的腿上,他安抚着我的恐惧,而同时我也抚慰着他那劳累而疼痛的双腿。我们一回到他的家中,加里就舒适地躺在他的床上,我告诉他我所关心的事情——也许是在最不恰当的时间——当我颤抖着双腿,在刚刚得知他的病情之后,就不得不在山洞里的巨岩之间爬上爬下。
加里变得非常气愤。他说道:“我没病!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对你那么说。”
好吧,这是一种解脱。
“不过,”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病入膏肓或者变成痴呆,没法和任何人交流了,那也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让我依靠电视机度日。”
说话的时候,他伸出双手,掌心朝下,然后他缓缓抬起手就像是在托起他的灵魂。”放点好听的音乐,那种令人慰藉的,它们可以把我带起来。”
至少那一晚,我睡觉的时候知道我的儿子仍然和我在一起,而且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