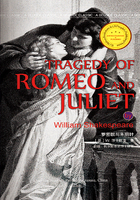1993年8月18日,北加州甲骨文用户组授予加里S·韦格曼一个证书,以表彰其通过最初研发优秀出版物以及娴熟运用专业资料在用户组方面对同行做出的突出贡献。
他为自己在工作中获得的荣誉感到非常自豪,我也一样。他也很高兴获得现金奖励。最初和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签署的两年合同续签了四次。后来他的主管告诉我他已获得了终身职位,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在这里工作很多年。
第二个月的假期我们去旧金山北部,进入丹尼小镇附近的森林里露营。在路上,加里和我感觉非常疲惫,于是我们铺开毯子进行短暂急需的休息。这时,加里对恢复性小睡的需求增加了,我也非常愿意在路途边停下来陪伴他。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是如此地宁静,九月的北加利福尼亚秋高气爽,好像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个世界。很快,我也睡熟了。当我睡醒时,加里给了我一些野生黑莓,那是在我熟睡时他去采的。如此简单的一个行为,但使我想起他一直是个多么充满爱心和慷慨大方的孩子。他一定记得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德克萨斯沿着铁轨采摘野生黑莓的时光。
我们继续前行到我们的露营地,营地下方是一条清澈透亮的溪流,我们开始搭帐篷。这是我第一次露营,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的经历。人类文明的唯一迹象是两个室外厕所以及一个水龙头。待到我们给睡垫充满了气,又到了加里的小睡时间了。他睡觉的时候,我在读《廊桥遗梦》(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每一次这样的时刻我都用阅读来打发时间,而且我享受这样的时光。整个世界一片万籁俱寂。
我们吃得心满意足。加里带了全熟和速冻的美食,我们出发前几天他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的确没有将就。
我急于想和他聊聊他的健康状况。没有电话或门铃会来打扰我们,尽管他向我保证我可以随便提问题,但我还是不忍心破坏我们在森林中营造出的这份令人愉快的气氛。他仍然没有主动提供任何信息。我只能用我的直觉和观察去监测他的的健康状况。
我想起几年之前,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母亲节,加里带我早早去吃了晚餐。后来,我们开车到休斯顿的其中一个大公园去,那里有一个宝塔样子的凉亭。斜靠在栏杆上,整个公园一览无遗,人们尽情享受着那个五月里美好的下午时光。我注意到一个男人,大概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旁边老夫人大概是他母亲。我回头对加里说:“看!那个人也在母亲节带他的母亲出来了。等我上了年纪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那样照顾我?”
“不,”他回答,“我还一直在想等我老了谁来照顾我呢。”
命运弄人。谁会知道他没有上了年纪的时候,而且每隔多久这个小插曲会以一种凄凉的暗示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在每一个母亲节。然而,他坚持保护我免受那可能的最终挑战所带来的伤害:我拥有自己亲生儿子提供的这些亲密关爱,到那时,都将是丰富的经历。
晚餐过后,我们坐在篝火旁挥舞着点燃的木棒,假装舞动着点点火光形成的旋转彩带。夜里,我开始意识到这睡垫有多么坚硬,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自己实际上直接躺在了地上,因为所有的空气都从睡垫里逃了出来。幸运的是,附带的有修理工具。
那天早上我们发现的另一件事情是,尽管我们在车里仔细打包了所有的食物,希望阻止不速之客比如大熊或者其他小动物的来访,但很明显我们还是没有打包得足够好。我们夜里就睡在旁边,但还是有一个访客来作案了。我们小小的野营地到处都是残留物,看起来似乎是前一天我们晚餐后的废弃物。我们只能推测什么动物发现了我们的残羹剩饭如此美味,但我们知道第二天晚上我们必须更加小心了。
十四年前的那次旅行,所有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因为每一次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时光都是我们感情时间轴上一个苦乐参半的印记。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