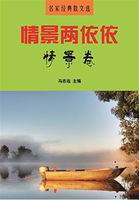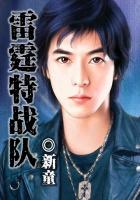每年春天,在休斯顿的一家豪华的酒店都有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以表彰这些被选出来的因其对于社区的出色志愿服务而获得市长奖的市民。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每一位获奖者都会被邀请到舞台上领取他们各种奖项所授予的奖品。我是作为杰克(Jack)的特邀嘉宾而去参加活动的,由于在艾滋社团中的工作他被授予1990的市长奖章。他作为志愿者1984年曾与我一起庆祝大型募捐活动的成功。仅仅参与其中对我来说已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晚会结束来宾散场后,我的获奖人转过来对我说:“你最好做好准备也来参加明天的活动。”
我还没有意识到,第二天晚上选择在另一家奢侈的酒店为艾滋基金会举行筹款晚宴,摩根·费尔切尔德(MorganFairchild)将作为嘉宾致辞。在那个场合,我的同伴正在和他认识的人打成一片,我去主办委员会的桌子前问我的座位在哪里。
“你和费尔切尔德女士一桌。”一位女士告诉我。
哇噢!我何等荣幸?事情很快水落石出,这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和被授予艾滋志愿者奖的人在一起,而他再次荣幸被安排和她一桌。
在鸡尾酒时间,由于我的同伴留下我自己,我就在酒店宽敞的大厅里闲逛。在那里遇到了乔,我生日照片的拍摄人,送他的情人蒂姆一台桌式收音机作为他永远的奖励。我相信今晚他是自封的摄影师,不过再次见到他真好。自我们在丹尼离世后的聚会上在对峙至今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那次聚会上乔指责我拒绝为一个空白文件公证。不需要言归于好,时间已经治愈了伤痛。另外,我已经忘记了那次不快,也许乔也忘记了。这并不重要,我们都忙着在这场运动中做更重要的事情去终结和艾滋的抗争,没必要人为制造第二个战场。
乔和我刚刚谈及自我们最后一次相见后各自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他突然打断我说道:“这位就是夫人了。”
说着,他站起来向这位尊贵的客人以及她的随行人员走了过去。
我们就坐后,我被介绍给摩根·费尔切尔德以及陪同她的家人。她非常漂亮高雅,用好莱坞内部消息取悦我们,说她从男同性恋那里学到很多化妆技巧。她显然对于待在艾滋社团里感觉很自在。开始向公众致辞时,她告诉我们她当初曾对进入医学领域很感兴趣,订阅很多杂志以了解这个行业的最新信息。她对艾滋病病毒以及艾滋病的最初了解就来自于那些杂志。
在演讲、音乐娱乐以及丰盛的晚宴结束之后,乔绕了好几圈并给所有想得到这个难忘夜晚的纪念品的人拍了快照,除以之外每位参与者的餐位上还附赠一小瓶香水。他为我和费尔切尔德女士拍了两张合影,第二天我上班时拿给理查德看。他说:“你看起来很不错,孩子。你旁边的这位甜心是谁?”
好吧,这可真是一种恭维!但当我告诉他这位“甜心”是谁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要了一张她亲笔签名的晚宴节目光盘给加里。她特别为他写道:“加里,很遗憾今晚没有见到你。爱你的摩根·费尔切尔德。”因为我几天后我将要和加里会面去墨西哥地中海俱乐部度过五天的假期,我期待把这条私人信息呈现给他。遗憾的是,他的反应与理查德如出一辙。尽管摩根·费尔切尔德是同性恋世界里的偶像,他并不认识她,或者,大概是因为他不看电视的缘故吧。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堪萨斯(KansasCity)的一个电话,通知我说,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死于艾滋并发症,我曾经和他在休斯顿度过很多个平安夜。我与他的恋人素昧平生,他好心地通过“小黑本”找到一些他知道必须通知到的朋友的电话号码。1972年,他搬到德克萨斯去工作,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做室内设计师,我们认识18年了。那是在艾滋出现的很久之前,那些年中我们有过数不清的快乐时光。他离开德克萨斯后,在两三个州待过,然后定居在了堪萨斯,我们彼此失去联络直到他被诊断为艾滋病。那个时候,他住在北卡罗莱纳(Carolina),打电话给我问了很多有关加里和艾滋的问题。他成为了位于达勒姆的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inDurham)一项研究项目的成员,经常去墨西哥旅行,在墨西哥能买到在他所居住的城市负担不起的药物。
我们随后的电话交谈回忆了很多我们去午夜弥撒前他为我和他的妈妈准备假期晚餐的事情,他是教堂里的手风琴演奏者。那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为教堂的仪式演奏手风琴,但有一个圣诞节他把他自己古钢琴搬到了教堂,这样他就可以演奏一些钢琴曲了。
接到堪萨斯悲伤来电的第二天,我和加里在图森(Tucson)机场碰面,一起飞往墨西哥的瓜伊马斯(Guaymas)。在机场,我们接受了几个我们认为他们是通过把旅行者从机场送到目的以此赚钱的一些当地人的建议坐上一辆小皮卡。回想起来,我真不能相信我们同意了这个可能是冒险的决定。我被安置在一个尊贵的位置,在车厢里,而加里和行李在皮卡的车斗里。我们疯了吗?显然没有。司机在沿途停下来,把一个和加里一起坐在后面的他的朋友放下以后,径直把我们送到了地中海俱乐部的前门,而且拒绝收取任何费用。我们的旅行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选择去地中海俱乐部是因为加里觉得可以满足自己想要好好放松一下的需求,这样就不用开车从一个汽车旅馆到另一个汽车旅馆了,也不用忍受在不同餐厅间穿梭。他清楚知道自己要慢下来并关注健康问题。他想要一个可以待在某一个地方的假期,远离旧金山的喧嚣以及他每天都要经过海湾大桥去伯克利的通勤过程。有时他乘坐湾区捷运(BART)1,但总要在车站寻找停车位,因此这次旅行正是他需要的。在酒店内,视线所及之处没有任何车辆。
食宿都非常好,有温馨的房间,山珍野味,永不间断的娱乐活动,白天努力工作的同样一群人也提供晚间娱乐活动以让顾客百分百的满意。每个夜晚,节目结束后,待我们这些被称为“文雅的客人”的人们回到各自的房间,这些职员还要排练第二天晚上的节目。我想象不出他们全部的精力都来自哪里,但他们都年轻、美丽而且热情。
我们的假期结束之前,加里参与潜水训练课程并拿到了证书。我们骑马,这对我来说既新鲜又令人兴奋。如此小心和谨慎,马儿们自己穿过一大片仙人掌沙地跑到了水边。我们沿着海岸飞驰,我不禁陶醉在和儿子分享这种经历的酣畅之中。我无从得知最后一次可能是什么时候。
我们在地中海俱乐部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加里的健康状况也不错。然而,当他在游泳池里割破了脚,他感觉自己必须得告诉为他治疗艾滋的医生,他担心这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但后来得知这没什么问题。
显然,这次旅行加里很疲惫。当我们在图森等候各自的转机航班——加里去旧金山,而我回家,在机场的长凳上他伸展全身,将睡眠眼罩放在眼睛上,睡着了。这是第一次,随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将会观察到很多次这样的小睡。
那个时候我对接下来的一个月将在肯恩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感觉自己陷入了迷宫之中。
1990
***
1BART,BayAreaRapidTransit,湾区捷运。旧金山的快速交通管理局经营的快速有轨公共交通系统,覆盖旧金山湾区的大部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