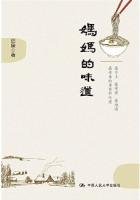虽然做治疗师的加里告诉过我他不想去做艾滋病病毒检查,但自从我认识他起,他看起来健康状况都还不错。但由于某些原因,我在1989年的夏天以后就没再和他见过面了。到了那年的12月,我知道自己需要心理健康干预了。那时,我失去工作已经超过一年了。所幸,我又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时间满足了加入公司团体保险计划的资格。我的工作是处理正式关闭的公司所需完成的所有职责程序(结果我又做了另外的15年),然而我在自己摇摇欲坠的生活中需要帮助。和一个建议我在9月份住院的精神病医生中断了短暂的联系之后,我在医疗保险计划的首选供应商手册上疯狂地搜寻着目标。
我决定找一个女性治疗师,因为我觉得另一位女性也许可以更好地体会到我的绝望。我选择了在手册找到的第一个人,我拨通了她的号码并抱着乐观的希望。我用了几分钟简单向她介绍了一下我一直以来的问题——如今已扩展成了我认为的爆炸性的危机——她建议我到她的诊所去,用她的话说:“让你再次高兴起来。”
我的本能反应是高兴?再次?这两个词都不在我的心理学词汇之中。如果“高兴”从未存在过,如何才能“再次”呢?
她的名字叫卡罗尔。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和我聊了超过20分钟——在她的领域这是非常不寻常的——而我足够有信心判断这是件好事。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会面,我给她带去了加里最新的诊断结果,并且告诉她在之前的六年里自己所做的一切准备。最开始,我的动机是想通过参与艾滋病志愿者工作来迎战敌人,但没过多久,我就被消耗殆尽了。我的儿子要么确实应付得不错,要么就是不告诉我疾病正如何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
自从加里单方面决定去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开始,我就感到自己的母亲角色已经从一个抚养孩子独立成人的养育者转变为了一个懂得何时应当祝福他在人生旅程中一路顺风的人。由于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以为他会住在家里并去一所当地的大学里读书。当他向我宣布“我想我会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时,我问道:“是什么让你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他回答说:“人生中总要有那么一个时刻要继续前进。”
那是一次简短但有力的交流,它令我想起了我曾读过的一个小小的隐喻。“如果一只鸟落在你的手掌上而你想要抓住它,它一定会飞走的。”我知道那是加里该飞走的时候了。
由于加里作为一个成年人行使了他的权利,我能感觉到如果他想要我知道什么,他就会说的。我真的不敢多问他,生怕他拒绝回答。我不得不掂量自己更愿意忍受哪一种苦恼:是不再像以往那样了解那么多我想知道的有关于他的事情,还是被拒绝的感受。
那是在1989年的冬天,加里在过去的六年里都很健康,于是我选择尊重他想要自己照顾自己的愿望,我知道如果他需要帮助的话就会通知我的。那既是一种巨大的负担,也是一种解脱,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有一种被拒绝的感受。毕竟,如果我看不到也听不到他的病痛,它就不存在。
在接下来的2月份里,就在我生日的前两天,肯恩打来电话通知我那个治疗师加里住院了。怎么可能呐?肯恩是怎么知道的?我要怎样才能确认这个消息?待到我激烈的反应平静下来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我应该给我们的朋友药剂师迈克尔打个电话,他对于所有人的事情都了如指掌。由于他当时正给城里的同性恋群体发放药物,他又怎会不知?到如今我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很多个迈克尔,而这个迈克尔告诉我说他们上次在药店里见面的时候那个治疗师加里看起来不太好。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呢?我感到头晕目眩;再一次,我感到自己似乎无法清晰地思考了。忽然,我变得难以置信地聪明,脱口而出:“我知道了。我要给医院打电话。”
然而,我对于接听电话的护士的回应还没有做好准备。我问道:“你们有没有一位叫做加里T的病人?”
依照事实,她回答:“我们有过,但他今天早上过世了。”
天哪,我甚至都哭不出来。我已超越了震惊与崩溃的状态。几个月前他还对我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在这儿。”如今他不在了!
现在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和卡罗尔说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正在考虑要如何度过剩下的一天。碰巧,到艺术博物馆去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黑暗的展室里我可以躲起来、沉思并感受。几天后我才得知那正是加里T的恋人工作的地方,于是我在孤独地进行悼念时不经意间又同他有了联系。
1989-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