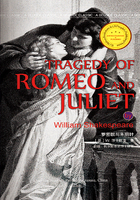进一步看,“山药蛋派”和“晋军”能够自觉地进行艺术革新与独创,客观上来自社会演进和文学发展的要求,但无疑主观因素最终决定并制约着其艺术革新与创造的展开方式和美学目标的。“山药蛋派”所以冷淡“欧化的”艺术,着眼于民间文艺形式的改造和群众口语的运用,致力于民族化、通俗化的探索,是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经历分不开的。“山药蛋派”都是土生土长,普遍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从小受到民间文艺熏陶,与农民群众感情深厚,参加革命工作后又做宣传鼓动工作,正是这些因素使“山药蛋派”自觉追求文学与群众的结合,创构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而“晋军”所以冷谈“山药蛋派”的通俗故事形式及使用群众口语创作、不多作心理描写等美学原则,致力于小说文本的深度的美学文化品味的创造,也是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经历分不开的。“晋军”中大部分文化程度较高,像韩石山、成一、王东满等都受过高等教育,而郑义、柯云路、李锐等人在京都长大受到良好的城市文化熏陶,这使他们普遍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和较高的审美品位。其中“晋军”内部的外来文化(按照卡西尔的观点,文化就是人并凝聚在人身上)带有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都的前沿性,郑义等人虽身在山西却与京都亲朋密切联系,因而势必给整个“晋军”更多的信息和冲击力。种种因素,使“晋军”有着更高的审美追求,更开放的文学观念,从而构成了“晋军”既具有乡土味又富有哲学层次的文化反思色彩的艺术风格。当然,无论对于“山药蛋派”还是“晋军”,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创造都是相对的大体上的把握,不仅他们与全国范围的其他作家们有重合相同之处,而且他们个人之间也又有互不相同的个性。但是它们二者分别作为文学群体,各自在艺术姿态上的共同性又是显然的。这种艺术的集团化效应无疑强化了二者的影响。
总之,正是社会的、文化的、艺术的、客观与主观的多方面合力的作用,造就了“山药蛋派”和“晋军”这两个高峰。而上述因素的相同与不同,也就带来两者的相同与不同。这一切都表明,文学的兴衰并不只是文学自身的事情,山西小说的下一步发展能否再出现高峰,仍然有赖于这样的一种合力。
1999年9月
又一道新的文学风景
区域文化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文学特色,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山西滞重朴实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山西的文学创作代代相承———凸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创作取向。从《诗经》中出自山西地界的“魏风”名篇《伐檀》《硕鼠》,到历代有影响的山西作家柳宗元、元好问、关汉卿等;从现当代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到80年代“晋军”创作的辉煌,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河一直流淌不息。比之其他地域的文学创作,晋域文学的质朴、写实、逼近生活,都是最显著的特色。这就使我们看到,继“晋军”之后在1990年代前后又一代山西青年作家群的崛起,作为20世纪末期北方内陆乡村现实的逼真写照,他们的创作既呈现出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创作色彩,又散发出一股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芬芳,并于今汇入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个发展趋势(指现实主义——引者注)”之中。
一
山西文学的这道新风景,是由30岁到40岁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作家群构筑起来的。最近由山西作家协会选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就是这个群体创作实绩的集中展现。诸如谭文峰的《乡殇》、王祥夫的《西牛界旧事》、房光的《莜麦谣》、张行健的《天边有颗老太阳》、常捍江的《古道崖》、曹乃谦的《佛的孤独》、宋剑洋和张晓枫的《童谣·白手帕红手帕》等等,都散发出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就全国文坛比较来看,这一年龄段固然有刘醒龙、张继以及河北“三驾马车”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显然这样那样的“新潮”颇多。如文坛上被谓之“私人化”小说的写家们,热衷于写个人一己的生活方式及感性体验,似在以“隐私”的坦露炫耀自我;如被称之为“新生代”的作家们,“都喜欢向读者诉说自己‘早年’的经历,于是乎匮乏的童年和少年成了小说无尽的资源”。对于这些作家来说,“现在进行时的生活,却被视为他人窗口的风景,一再受到冷淡”。而相反,山西的青年作家们恰恰密切关注着“现在进行时的生活”,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他们是那样熟悉而动情地描写着淳朴真实的农村生活、农民命运,显示出逼向现实真实的同情态度。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性文学现象。历来文学家的一个分野就在于对待现实的不同态度。是注视、贴近现实还是漠视、远离现实?是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情状还是只抒个人一己的悲欢哀怨?不同的选择表露着不同的价值向度,寄寓着不同的审美情愫。正是在这点上,山西青年作家群显示了自身鲜明的特点和群体性,即把关注与写照现实作为文学创作基本的美学原则。如以反映现实深刻见长而引起广泛瞩目的谭文峰就说:“关注现实,是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格”,“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使我和读者及编辑们之间感情沟通的,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深深渗入我的作品之中的,我的作品的灵魂:关注现实”。王祥夫也很动情地说:“我的小说始终是入世近俗,吃着五谷杂粮,便不能不想五谷杂粮的之所来。……如果我们现在连盛饭的饭碗都没有,那么,我们大可不必去发掘远古的陶罐。所以,我特别关注现实中的农村。”这些话率真地表达了山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取向——关注现实,可以说,这是他们第一要义的东西,是这个作家群创作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正是根基于此,才产生了谭文峰的《扶贫纪事》《走过乡村》《仲夏的秋》,王祥夫的《棉花》《雇工歌谣》《太阳下的村庄》,常捍江的《深蓝色的碑》《天皇地老》,房光的《没看见有雁飞向南方的秋天》《莜麦谣》等等。这些作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笔触直接伸展到了乡村现实的整体生态、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着古老大地上的贫困、滞重、落后,也展示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骚动、觉醒、变革,深刻揭示了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及转变过程中的艰难性、复杂性和严峻性,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力量。那么,耐人寻味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一种“新”旗林立、热衷“实验”的创作风潮下,山西青年作家群何以择取现实主义这一古朴而为文坛时尚所薄的美学原则?
山西的青年作家其实并非没有受到“新潮”的诱惑,新的观念、新的手法也肯定要影响到他们,但这种诱惑和影响恐怕只能是充实和丰富他们的艺术思维,而决定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和对待人生态度的,则还是积淀在其心理意识深处的文化精神。山西青年作家多是土生土长,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广袤的黄土地和质朴厚重的生活是孕育他们的肥沃土壤。如谭文峰还是八九岁的村娃时,便“挑两只硕大的木桶,在村河与窑洞之间的黄泥路上摇晃”,过早地体验了生活的艰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命运很早就给我压上一份生命的沉重。”而常捍江则出生于吕梁山深处的一个贫困山村,在那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多个寒暑,遍尝了滞重苦闷的生活。此外像房光、张行健、宋剑洋、曹乃谦以至生于小城却“无法摆脱农村”的王祥夫……这是深深植根于、困扰于土地的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位至今还是农村户口,有的虽然在城里有一只“泥饭碗”,但家依然安置在农村,经常奔波在城乡之间的阡陌小路上。正是这样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体验生活,使他们的情感心理与土地、与农村、与农民丝丝相连,使他们时时感受着乡村现实的生活律动、民众情绪的波荡起伏,并最终形成他们的情感质点和思维取向。而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既是百姓中一员又是百姓的代言人时,就更加关心百姓的生存现实。就如谭文峰坦言:“当我跳出原来的生活圈子,再回过头来观照我们所生活过的乡村时,我深深感觉到的,不再是个体生命的沉重,而是一种民众生存的艰难,群体生命的沉重。”亦如房光所说:“我很同情他们,因为我也同情自己。”这些话语鲜明地表现了这些青年作家的大众性、现实性的精神意向。
本来,审美活动、美感实质上都是一种社会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谈道: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物质生活的不同,是否参加劳动的不同,美和审美感也就不同。“普通人”关于美的概念所以不同于“社会上有教养的阶级”的概念,并非精神发展的程度不同,那完全是因为普通人和社会高等阶级中人对生活与人生幸福的了解不一样,从而他们对于人体美,对于外貌所表现的生活的丰富、满足、畅快也就不同。对于处在社会基层并与民众血脉联系的这群青年作家来说,眼前现实的滞重和朴实的审美感,便决定了他们关于美的概念和艺术追求的价值取向。那些超脱、潇洒、游戏似乎与他们无缘,他们思维心理上的现实性、沉重感、忧患意识,使他们无法像其他地域的一些同龄作家那样或者沉浮于故事的迷宫,编造扑朔迷离的情节,或者醉心于语言的雕刻,在词语的浪花中随波逐流,又或者听任想象的翅膀穿越现实的天空,翱翔于往事的原野……相反,倒是生活中种种生动真实的现实事物更能唤起他们爱与憎的审美感觉,激发他们的创作冲动。当他们拿起笔时,“首先关注的便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的生存现状”;他们要“以全身心的热情拥抱现实,准确地把握农民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同阶段中的生活命运和心路历程”。显然,在他们以为美的东西,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斗争和有着意义的东西。正是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文学创作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二
山西青年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因其强烈的写真性,为我们提供了北方内陆乡村现实的活生生景象。这里有雁北荒僻的“温家窑世界”种种原始、混沌、凄苦的人生情形(曹乃谦《温家窑风景》),也有雁北乡亲在改革触动下的波动、觉醒(房光《没看见有雁飞向南方的秋天》《莜麦谣》);有晋南地区平民百姓平淡、卑微而真纯的日常生活(张行健《山校》《平民的日子》),也有晋南乡镇工业文明的发展对农村惯常生活的冲击及人性的变异、觉醒(谭文峰《走过乡村》《仲夏的秋》);有吕梁山沉重、骚动的生活场面(常捍江《申村爷坐街》《天皇地老》),也有忻定平原失衡、演变的生活态势(宋剑洋《最后一顿夜草》)……总之,一方面是古老的、惰性的、素朴而贫困的农业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是生活的巨大变动和观念信仰的冲突。从山西青年作家群丰富多彩的艺术写照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一方面是山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延伸,但同时又表现出新的创造和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