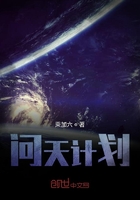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宗白华先生重新梳理了自己生命哲学的理论资源,谈到西洋画所表现境界的哲学基础时他指出,西洋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体现了“物与我中间一种紧张,一种分裂,不能忘怀尔我,浑化为一,而中国人对于这空间和生命的态度却不是正视的抗衡,紧张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中国诗中所常用的字眼如盘桓、周旋、徘徊、流连,哲学书如《周易》所常用的如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正描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不同于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在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中,主客体一直呈紧张的对立关系,“我”与“物”、“心”与“境”、“生命”与“自然”截然对立,二者的关系多是征服与臣服的关系,很难和谐相容,因此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一直就是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痼疾。而东方则不然,诚如宗先生所言:“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道,就是这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纶万物的生命本体。”在这里,正因为个体生命与宇宙相互贯通,弥纶无迹,从而具有了本体论意义。《周易·系辞上》所讲的“生生之谓易”、“生生之德”正是这一生命本体的最精练表述,“纵身大化,与物推移”的概念更是与庄子之道息息相关。陶渊明在《形影神赠答诗》提出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人生境界,则体现了早期古人对这一生命本体的自觉体认,其实,“纵浪大化”就是返回自然,随自然的节奏一起律动,让生命随大化流变的宇宙而周流不息,从而实现自我的超越。在《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一文中,宗先生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绘画所表现的这种真气弥满的生命精神,他说:“华贵而简,乃宇宙生命之表象。造化中形态万千,其生命之原理则一。故气象最华贵之午夜星天,亦最为清空高洁,以其灿烂中有秩序也。此宇宙生命中一以贯之之道,周流万汇,无往不在;而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老子名之为虚无;此虚无非真虚无,乃宇宙中混沌创化之原理;亦即图画中所谓生动之气韵。”正是基于对《周易》、老庄宇宙观的生命体认和弥纶贯通,最终他把“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同视为宇宙活力的律动,将“气韵生动”的“生命的节奏”与“宇宙活力”的契合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在此,宗先生复活了一套以《周易》和老庄哲学为源头、真气弥满而和谐圆融的生命哲学话语。
方东美先生的生命之思也是从柏格森起步的,他留美期间的硕士论文即是《柏格森生命哲学评述》,但相比柏格森,早年的方东美对尼采的审美形上学更是赞赏,认为它就是“生命的赞美歌”。他在《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对尼采的理解:“他重视希腊悲剧,因为雄奇的文字适足写象生命的高致,他崇拜希腊雕刻,因为造型艺术妙能描摹纯美的气象。盎然充实的生命就是力的扩张、美的表示。一切艺术创作使我们达所欲生,畅所欲为,以实践无穷的可能。生命正是艺术,艺术富有生命。美的创造为人生根本意义之所在,离却艺术,人生即无以耀露它的自由。美感是生命的节奏,诗人是生命的明灯,艺术有起死回生的伟力。”尼采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化遭遇困境的时期,尼采试图通过生命力的张扬来挽救日益颓败的西方文化,但饮恨而终。而年纪轻轻的方东美却清醒地看到了尼采所张扬生命力的无根性,认为彼时西方文化的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将人与自然劈成对立的两橛”,也就是宗白华所说的“物与我中间一种紧张”关系,倘若人与自然的这种紧张对立不消除,尼采所张扬的生命力也就无所依附,一切自会变得空洞无力。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之下,方东美转而诉诸《周易》,由《周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哲学本体建构起了他“生生之德”的生命哲学,即指宇宙大道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体现一种绵延不断、创造不息的生命精神。他认为,“生生之德”将“生”字重言所揭示的是:这种宇宙生命精神的创生,不是一度的程序,而是继续不停地创造,“生命”是宇宙万物的“原委”,可统摄、融合世间万有,并进而他还提出了“普遍生命”的本体概念。在《中国人生哲学》中,方东美明确赋予“普遍生命”及其所构成的宇宙以五种内涵: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方东美认为:“各物皆有其价值,是因为一切万物都参与在普遍生命之流中,与大化流衍一体并进,所以能够在继善成性、创造不息之中绵延长存,共同不朽。”他在《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认为,《周易》既是一套本体论,又是一套价值论,他称之为“价值中心观之本体论”。他说:“这个价值的来源何在?在《周易》中是把它集中在‘天’,就其作用来看,一切卦从‘乾’卦产生,而‘乾’最重要的质素是‘乾元’,然后文言传中马上就开始说:‘元者,善之长也’。‘乾元’是一个代表宇宙一切价值的总枢纽的基本符号,是一切卓越价值的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作为一切价值来源的“天”就是普遍生命,因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一切现象里面都藏有生命,“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正是这种普遍生命的存在,使人们“知生化之无已”,日臻和谐之境。在《中国人生哲学》中,方东美更是将老庄哲学中“天地之大美”的概念借助创造的活力与普遍生命联系起来,“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圣人原天地之美,也就在协和宇宙,使人天合一,相与浃而俱化,以显露同样的创造。换句话说,宇宙之美寄于生命,生命之美形于创造”。至此,方东美把永恒的本体界与变易的现象界统一起来,贯通中西,揭示一套动态的本体论以及超本体论的观念,从根源上赋予中国哲学以广大悉备的生命精神和无穷的超脱精神。
另外,方东美在《从宗教、哲学与哲学人性论看“人的疏离”》中将“普遍生命”的境界在纵向上分作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心灵世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宗教境界等六个层次,前三个层次属于形下境界,后三个层次则被划分为形上境界。物质世界的人只有维持生存的能力,而生命世界的人则有创造力,心理世界的人更是有理性规约能力,至于艺术境界则是进入形而上层次后的第一重境界,里面的人具有审美力,而道德境界的人则有至善的道德品质,宗教境界已是近乎先知的至善至美的神人。这六个层次和形下形上两种境界依循“双回向”运动模式循环往复,运动不止。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也划分了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艺术境界等六种境界。但相形之下,逻辑性匮乏,不如方东美对生命境界的理解圆融。而方东美将生命的各种境界完全打通,层层旋进,充满灵动与和谐,将生命机体的特征、状态、发展模式全副展现,是一个动态的立体的发展体系,这正是方东美独特的地方。
二 气韵生动的艺术之境
宗白华先生自觉地将生命哲学援入他的美学风景,始于1921年发表的《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其文写道:“‘自然’是无时无处不在‘动’中的。物即是动,动即是物,不能分离。这种‘动象’,积微成著,瞬息万变,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非是动;非是动者,即非自然。照相片于物象转变之中,摄取一角,强动象以为静象,已非物之真象了。况且动者是生命的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艺术家想借图画、雕刻等以表现自然之真,当然要表现动象,才能表现精神、表现生命。这种‘动象的表现’,是艺术最后的目的,也就是艺术与照片根本不同之处了。”而照片之所以缺乏艺术性,正在于其表现的是生命力匮乏的凝定物象而非真气弥满的流动物象。在这里,艺术性与真气弥满的生命力挂钩了。在1932年发表的《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一文中,宗先生进一步认为:艺术“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不沾不滞”正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的圆融生命状态之体现,唯有以本真的生命观照物象,才能体验到艺术的如此至美的境界。
在1934年发表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宗先生指出:“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伏羲画八卦,即是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示宇宙万相的变化节奏。后来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气韵生动”本是南齐谢赫《画品》里的概念,有魏晋遗风,宗先生借来作为最高艺术境界来标示,盖有深意焉。宗先生认为气韵生动之境的营造在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与“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的契合,唯有二者契合,物我无间,才能抵达生命深处,从而形成气韵流动的艺术境界。
在1944年发表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宗先生对这一过程阐释得尤为详细:“以宇宙的具体为对象,玩赏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为虚景,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在此文中,宗先生还谈到舞的境界是最高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是艺术家的独创,是艺术家从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他还说:“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宗先生认定有一种宇宙的生命律动,即所谓“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当人的心灵还原到虚静状态时,就会同这种宇宙生命一起律动,“李、杜境界的高、深、大,王维的静远空灵,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所有艺术都是根植于艺术家的活跃至动的心灵的,进而都与宇宙生命律动契合,宇宙之“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艺术不仅根源于圆融的生命状态,我们之所以被具有艺术境界的作品吸引也是由于它能表现“人类心灵最深最秘处的情调与律动”,从而使我们“借此返于‘失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得生命的中心”,这也正是艺术境界的价值所在。正是这一点让宗先生终生笃情于艺境之追求。
对于艺术之境与生命状态的关系,方东美与宗白华有着大体相同的理解,在《中国人生哲学》中他指出:“不论在创造活动或欣赏活动,若是要直透美的艺术精神,都必须先与生命的普遍流行浩然同流,据以展露相同的创造机趣,凡是中国的艺术品,不论他们是任何形式,都是充分表现这种盎然生命。”在这里,方先生将普遍生命原理与艺术精神妙合无垠地结合起来了,与宗白华先生的主张并无二致。但此后的阐释却呈现出不同维度的展开。
方先生立足中国传统文艺,依据普遍生命原理归纳了艺术境界的特点。首先指出的一点是在艺术中“玄学性重于科学性”,即“中国的艺术家尤善于驰骋玄思,在创作中宣畅气韵生动的宇宙机趣”,认为唯有运用形而上的玄学思维,才可以“直透灵魂深处”,“展现全体宇宙的真相及普遍生命之美”。相比之下,宗白华对此涉笔不多,因为相对于玄学思辨,宗白华明显更重视感性体悟。方先生指出的第二点特性是“从意味上讲,中国艺术是象征性的”,并阐发道:“因为中国艺术所关切的,主要是生命之美,及其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它所注重的,并不像希腊的静态雕刻一样,只是孤立的个人生命,而是注重全体生命之流所弥漫的灿然仁心与畅然生机”。在这里,方东美使用了宗白华惯用的“气韵生动”这一概念来指涉艺术作品的生命之美,与宗白华冥合神契。此外,对象征的凸现,也与宗白华反复陈述的“创形象以为象征”的艺境创造方法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