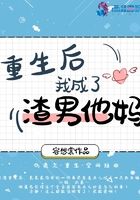任何媒介自诞生之始都必须面对受众,依存于受众,而媒介如何看待受众不但决定了媒介和受众的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媒介的编辑方针、内容特点、风格定位、运作模式和操作方法,甚至进一步决定了媒介的发展方向和它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媒介受众观的衍生变化伴随着媒介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两者相互作用,又互为因果。因此说,当代新闻媒介变革的每一步在一定意义上都取决于媒介受众观的革新变化。从这个方面上说,研究和探讨媒介受众观,维护受众的公民权,应当也必将成为新闻传媒尤其是当代中国新闻媒介改革的中心课题。
受众是谁?
明确的受众定义、概念和范围是现代大众传播学的产物。但实际上,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媒介自诞生之初便与各自的受众相依存,这是每个媒介主持人、传播者都明了的道理。但纵观新闻媒介所走过的历程,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媒介主持人和媒介传播者的受众观却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受众有着不同的身份,也正是依据这不同的身份,媒介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受众是学生。
在媒介面前,受众是受教育对象。媒介的内容如同课堂的教科书,要给受众以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媒介肩负教导受众之重任。媒介工作者的角色就像学校的教师,其职责是尽可能甚至是保证媒介内容是严肃的、负责的,媒介发表的每一句话最好都是富于教育意义的。虽然如同学校教育之教学相长的原理,媒介及其工作者也会倾听受众的意见和呼声,从而改进自身的工作,但这多少有自上而下的“俯就”意味,纵然先当学生、或暂时当一下学生,向受众求教,但做先生才是媒介及其工作者根本的目的。媒介和受众最终定位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
新闻传媒的确具备教育指导功能,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基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需要,这种教育引导功能可能还会变得凸现出来,尤其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媒介为启迪民智的工具,这一点中外皆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自王韬办《循环日报》始,无论是维新变法时期,还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活动,直至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处于社会变革甚至是激烈的社会革命时期,改革者和革命者往往侧重于报刊的教育启蒙功能,以宣传先进的、革命的理念,宣传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指导大众为己任,以报刊为“国民教育之大机关”(《浙江潮》第4期),“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直至认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必须承认,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特定的历史需要,媒介的这种受众观有其不可否认的内在合理性。事实也证明,在许多情况下,媒介工作者成功充当了教师媒介甚至起到了社会“灯塔”的作用。
但媒介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的耳目,是社会信息交流沟通的工具,更多时候它首先是“探照灯”,告知社会的最新变幻。因此,教育是其附属的不是第一位的更不是全部的功能,这就决定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媒介不能永远也不能只把受众当作学生,只有在特定时期,承担特殊使命的媒介方才适用。
受众是被领导者、被指导者。
在这里,报纸甚至所有的传媒俨然是不见面的指导员,甚至不见面的司令员。报纸的内容就是指示、命令,媒介上的内容不只是生硬,有时简直就是杀气腾腾,受众已不仅是应声而倒的靶子,甚至成了无知的“阿斗”,必须确信媒介上字字句句是“真理”。受众被剥夺了最起码的自尊,遑论自由和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念,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掌握的媒介工具及其实践,都是这种受众观的印证,而人们也从这种媒介受众观的痛苦教训中获得觉悟,把它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受众是消费者。
这是一切商业性媒介最容易接受也最愿意信奉的受众观。在这里,媒介等同于企业,执行利润最大化原则。对于媒介,一如对于企业,高扬消费者至上的旗帜,满足受众需要,捍卫受众权利与满足消费者需要,保障消费者权益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争取消费者、受众,争取广告,获取最终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两次买卖和消费,受众不仅消费了媒介产品,同时也自愿或不自愿地消费了媒介刊登(播发)的广告;媒介表面上是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受众,实际是把受众卖给了广告商,并使其成为广告商品现实或未来潜在的消费者。至于受众,无论其是否了解这个特殊的两重甚至是三重消费的过程,其消费者的角色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尽管媒介有时甚或常常像是谦恭的服务员,但实质永远是经营者、企业家、中间商。媒介的直接目的是出售媒介产品,最终目的则是出售广告。
受众是公民。
这是迄今不少国有或者公共所有制的媒介所禀持的受众观。媒介和受众地位相对较为平等,媒介尊重受众的独立人格,捍卫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需求,首先在于视他们为公民。媒介的编辑方针和内容特点必须符合现代民主社会机制下公民的需要。媒介更多体现公共事业性,较少商业色彩。
受众这四种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他们面向不同性质和特点的媒介;媒介这四种不同的受众观也决定了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发展方针。应当说,迄今的媒介发展历程和现状,都证明这四种情况在许多时候,在不同国家、地区都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从现当代传媒业发展现状出发,受众的公民与消费者角色之争,两者的角色互换和转移,是斑驳陆离的当代传媒变革中最富代表性的变化,而这两种受众观的转化也将在相当意义上决定未来世界乃至中国媒介的走向。
从受众到公民
受众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只是表明他作为媒介信息接受者的特性。他的权利和自由及其范围和享有的程度,必须基于他的身份定位。公民,在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基于维护个人权利和人民民主原则的现代宪政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公民理念结束了封建时代不平等的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转而以国家(政府)与公民相替代。“公民”意味着他取得了与国家、政府相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有维护公民基本自由与权利的义务,公民则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国家秩序。“公民的权利就是国家的义务,国家的权利就是公民的义务”。
把公民概念引入媒介受众观(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把受众当作公民以维护公民权为媒介责任和运营基础,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市场经济内在运作机制在媒介观上的折射和反映。在西方媒介史上把受众当作公民,在理论上集中体现为社会责任论的出现,在媒介运作模式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欧美各国中的公共广播电视业,在法律上则突出表现为现代知情权(知晓权)在观念上的提出和法律上的确认。
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社会责任论是西方媒介观上原则,体制的限制使其以盈利为目的的消费观无法转向公益性质的公民观。
结果是社会责任论最大的成果是在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在实际媒介机制和操作环节上的影响则十分有限。
有意思的是,与报刊不同,西方广播电视业尽管是公私并存的体制,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报刊相比,它更具备公众性。在广播电视诞生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电波频率是一种很稀缺的自然资源,因而广播频道就具有公共资源属性,不能私有,广播电视事业也就不同于印刷媒介,成为承担公共义务的特殊许可性事业。国家、政府为维护公众利益,有义务、有权利对之实行相应严格的管理,甚至直接建立国有或公有的广播电视业以确保公众利益、公民权利在广电传播中的保障和实现。这一点在以英国广播公司(BBC)、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以及日本广播协会(NHK)这类西方公共广播机构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加拿大广播公司经理比尔·米尼曾在一次演讲中阐述公共广播电视业的建立“是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创造者和执行者提供一个表达他们自己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允许加拿大公民接近最优秀的创造、最优秀的思想观念、最优秀的传统和理念价值,在此,我们将讨论戏剧、文学、音乐、舞蹈、科学、技术、经济以及事务和政治事务”。正是这种理念使广播电视业特别是公共广电业避免了商业化媒介追求信息刺激,扩充消费的盈利观,把受众当作公民,而不是消费者,以服务于公众利益为宗旨,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节目编辑方针,以严肃、健康的新闻时事、社会教育为主,兼顾娱乐,减少、避免庸俗和低级趣味的不良影响。
然而,公营广播电视业虽然在某些国家占据显著的地位(尤其是西欧各国)有较大影响,但就媒介整体而言,它毕竟不是绝对主体,它的理念也很难转化为媒介整体的主导受众观,它的规定也很难作为媒介整体的管理性原则。特别是在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整个社会机制面前,还是必须依赖于市场内在要求,配合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将公民权利提升为普遍性的法定形式,才能具备真正的、整体性的约束力,不管这种提升是直接的,还是隐蔽、曲折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知情权概念的提出和它在法律上的体现。知情权在新闻传播领域,特指受众通过媒介获取有关公共生活信息的权利。1945年,美国记者库柏首次明确提出“知晓权”概念,逐步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获得广泛的认同。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进程深入,人们通过反思媒介发展历程与专制主义斗争的历史,深刻地意识到没有知情权作为基础,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正常的社会民主生活都会成为空谈,特别是公民权利中的政治权利。如果不“知”,也就无从表达,无法参与,批评、建议乃至选举权都会成为无源之水。知的权利应是公民一项基本人权,更是公民正确地、正当地行使其他民主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权利行使中带有“前置性”。媒介作为公民了解信息的主渠道,依附于公民权,同时也应获得和享有知情权,为公民了解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提供参考信息。只有获得了“知”的权利,公民和媒介的表达自由才有意义。知情权是媒介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基础。这一概念是对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媒介还是公民,豁然开朗,仿佛找到了一把开启自由之门真正的钥匙。基于这种认识,知情权概念开始普及,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法律中,尤其是各国制定颁行的以行政公开化原则为基础的行政程序法中。这是知情权在公法领域最多和最直接的体现。1990年意大利《行政程序法》、1993年日本《行政程序法》、1966年美国《信息自由法》,均贯彻行政公开原则。1976年美国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不仅规定记者可以依法要求查阅政府记录(除极少例外应当包括政府活动的所有记录),而且要求联邦、州及当地政府部门公开办理业务。迄今,美国各州都有知情权的条文,并多从媒介权回归到公民权。人们逐渐认识到知情权不是媒介特权而是人民的权利,受众作为公民,拥有通过媒介了解公共信息的权利。知情权实质在于维护公民权。从而,也强化了专门从事社会信息整合和传播的新闻媒介的新闻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