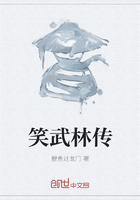管老侠、吉安平、夜部调一走出店外,夏侯天也跟了出去。
行出三里多路,便到了刘家庄,不容进庄,夜部调直嚷口渴。
管老侠见天色尚早,道:“那边有一家酒店,我们到那里喝两杯如何。”管老侠一说完,夜部调连连道:“中中中。”说着三人直向酒店而去。
夏侯天看在眼中,还是不紧不慢的远远跟着。
管老侠、吉安平、夜部调刚走到店前,不容入内,只听一人道:“那不是吉安平哥哥吗?”吉安平但听有人有人呼他,转过身去,只见他身后立着三人。
当中那人生的一脸横肉,正是赵一杰,赵一杰左边之人脖子极长,正是李校茗,赵一杰右边之人生的脑满肠肥,正是郑金山。
赵一杰、李校铭、郑金山这三人号称青石镇三雄。
夏侯天刚喝了一杯酒,但见管老侠、吉安平、夜部调、赵一杰、李校铭、郑金山六人鱼贯而入。
这六人一走进店内,一人道:“那不是管老侠管兄弟吗?”
管老侠但听这声音,连忙道:“顾二哥,你也来了。”一边说着一边顺着话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窗户旁坐有一人,那人脑袋扁平,老鼠眼,下颌留有一指长的胡须。
被管老侠称为顾二哥的是顾广旷。
顾广旷道:“兄弟你带得人可真不少哇。”
管老侠道:“二哥见笑了,若不是街面上有吉安平、夜部调二人看得起我,我和你还不是一样单枪匹吗。”管老侠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过来。
顾广矿道:“我瞧那些人都有些身手,不知都是些什么人?”管老侠道:“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吉安平等人见管老侠和顾广矿交谈起来,不由都侧耳倾听着,但听管老侠如此说,一起站起身来走了过去。
管老侠道:“这位是我二哥,顾广旷。”吉安平等人连忙向顾广旷行了一礼,接着赵一杰和吉安平等人各自报了姓名。
众人报罢了姓名,赵一杰道:“我们三人是碰巧和管老侠管老英雄相遇的。”说着用手指了指李校铭和郑金山二人。
管老侠道:“大哥请你我二人,说是和那年轻人一会,不知那年轻人是什么来头?”顾广旷道:“我看那年轻人来头不小,否则也不会让你我二人出马了。”
夏侯天听顾广旷和管老侠议论起那年轻人,自思到:“他们所说的那年轻人是谁,莫非是我二弟。”想到此暗暗倾听起来。
夜部调道:“那年轻人不生事便罢,否则,我兄弟三人让他来的去不得。”顾广旷道:“我看此事没那么容易。”
管老侠道:“反正我们到了刘家庄,到时大哥会向我们说明一切的。”二人正想接着往下说,只见他们所说的引起了大多数人的注意,二人声音不由低了起来。
顾广矿和管老侠又说了一会话,看看喝的差不多了,悄悄向店外而去,吉安平等人自也随管老侠而去。
顾广矿和管老侠等人一走出酒店,夏侯天正想跟出,突想到:“天色未暗,不如等天黑了在作打算。”想到此又自饮了起来。
突听一人道:“什么青石镇三雄,我看是青石镇三恶。”声音从柜台旁传出。
只见两人相向而坐,一人肚大腰圆,身材极是魁梧,三十来岁的样子,正是齐曾,另一人膀大腰宽,太阳穴微微隆起,竟是高艾。
高艾道:“哥哥怎会说出如此话来,莫非青石镇三雄得罪了哥哥不成。”一人道:“青石镇三雄那敢得罪齐曾大哥,否则齐大哥见了青石镇三雄岂能善罢干休,齐大哥我说的对吗?”
马太保身旁一人奇道:“明明是青石镇三雄怎么成了青石三恶了?”
马太保道:“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去年我在青石镇见赵一杰、郑金三、李校铭三人欺负一个外乡人,当时齐曾路见不平正想拔刀相助,就在那时,王胖子叫走了青石三恶,齐曾老哥只好做罢。”说到这里,转向齐曾道:“我说的对吧。”齐曾点了点头。
高艾道:“什么管老侠、顾广旷,也不过如此,和青石三恶相交的人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
齐曾道:“李校铭、赵一杰、郑金山我虽不知,那管老侠和顾广旷却好生了得,年轻时游荡江湖,在江湖中也是颇有名气之人。”
夏侯天听到这里,无意中只见窗户旁坐着五个人,那五个人一个胖子、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两个年青人、一个中年人。
五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说些闲话,胖子不经意向窗外望了一眼,突“咦”了一声道:“老刑,那不是洞江双煞吗?”
原来五十多岁的人正是老刑,胖子是肖哗,中年人是胡刑,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刑困、一个是刑本。
老刑但听肖哗言语,连忙抬起头来向窗外望去,只见东面走来俩人,二人青一色的服装,神情严峻,一个是石图,一个是尤深。
石图生的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尤深三十来岁,太阳穴微微隆起。
老刑不由应道:“不错,正是他二人。”胡刑道:“这二人怎么也来光顾这小地方来了,难道他二人也是为那朵大红花而来,这下可惨了,今年不知又会打伤多少人。”
肖哗道:“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他二人一较长短。”胡刑道:“这小场面,他二人怎能看的上,也许是偶然路过罢。”老刑道:“但愿如此。”
刑困道:“洞江双煞是何许人也?”胡刑道:“洞江双煞乃是邪派中人,不知为何,这四、五年来二人突然销声匿迹了,想不到又在此出现了。”
刑本见胡刑说洞江双煞如此了得,心中极是不服,道:“也许是徒有虚名吧,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
老刑道:“井底之娃也敢大放厥词,你懂什么,你见过什么天什么地,洞江双煞可是吹胡瞪眼便要杀人,这二人杀人时连眼也不眨一下。”
肖哗道:“这洞江双煞乃是极毒极邪之人,黑白两道无人敢惹。”
胡刑道:“往年都是我们这些未入流的舞舞枪、耍耍棒、伸伸拳脚,今年是怎么搞的,怎么洞江双煞也来了,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五人正说着,洞江双煞推门而入,老刑但见洞江双煞走进店来,连忙“嘘”了一声,胡刑等人见状早已会意,出声不得。
尤深、石图一走入店内,齐曾、马太保、高艾等人一起望了过去,马太保但见尤深、石图的面貌,马太保的脸色苍白了起来,怕的要死。
齐曾、高艾等人但见马太保的神色都沉默了起来,一时间,酒店中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只听尤深道:“小二,来两坛酒五斤牛肉,十个馒头,在拿两个碗来。”小二连连应承,不大一会用一个托盘端了出来,一一放在桌上,又给二人各倒了一碗酒。
石图端起酒碗,一饮而尽,道:“痛快,痛快。”说着停了停,又道:“这些天来都快憋出病来,若不是见公子今天心情好的很,我们哪能出来透透气。”话声一落又一碗酒进肚了。
尤深左右环视了一眼,奇道:“小二,你们这里是什么规矩,怎么人人都带刀带枪。”小二连忙道:“客官你有所不知,我们这里明天将召开“以武会友”大会,所以连日来江湖客极多。”
尤深但听“以武会友”四字,喝了一碗酒道:““以武会友”,不知都邀请了些什么人?”小二道:“都是附近十里八村之人,来的人都爱舞枪弄棒。”说着便走了下去。
尤深和石图碰了一碗,道:“老石,真没想到如此小的地方也有此事,你我二人来此一遭也不枉此行,我们不妨在此稍稍逗留,瞧上一眼可好?”石图道:“好是好,莫要被公子知道了。”夏侯天但听尤深、石图的话声,不由倾听了起来。
尤深道:“不会吧,公子深居简出,消息极是闭塞,他怎会知道呢?”
石图道:“如此热闹的场面,那能不惊动公子,我们得想个办法莫要让公子知道的好。”
尤深无奈道:“公子也真是的,最爱救死扶伤、排忧解难,“以武会友”就得动刀动枪,哪能不伤人,若被公子知道了,少不了一番救治,不知要费多少功夫,花费多少时间,救死扶伤、排忧解难我不反对,就怕到时莫遇见了迎菊。”
尤深道:“你说的极是,我们得想一个办法,还是莫要让公子知道的好。”石图道:“好不容易出来透透气,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呢?真是使人费心劳神。”
尤深道:“不如我们明日让那以武会友大会散了,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夏侯天听石图和尤深有如此一说,暗暗奇了,不知他们所说的那位公子是什么来头?
尤深和石图计议了一番,二人又吃喝起来,酒足饭饱,二人算了帐,扬长而去。
尤深、石图一走远,老刑看了看同来之人一眼,低声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歇息,养足精神,明天早早去看那“以武会友”大会,一饱眼福,也不虚来此一遭。”说着算还了酒饭钱,五人一前一后也向店外而去。
就在那时,高艾道:“马兄,你怎么一见那二人像是怕的要死?”马太保道:“你若知道那二人是谁,就不会在有此一问了。”
高艾道:“那二人是谁?”马太保一字字道:“尤深、石图。”
高艾等人但听“尤深、石图”这四字,一时间又闭息凝气沉默了起来。
角落里有一人身穿灰色僧衣,头上九个戒疤犹红如血,一看便知新烫不久,那僧人和别的僧人不同,僧人一向只吃素,这和尚却大碗吃酒,大快吃肉。
那僧人身材极是高大,双眼炯炯有神,眉宇间时隐时现一股暴戾之气,这僧人的法号是净空。
众人正说着,高艾突“咦”了一声。
齐曾不由道:“怎么了。”高艾道:“你们看那是什么?”众人不由向高艾手指处望去,一人道:“有什么稀奇的,只不过是一个和尚而已。”
马太保道:“这年月可真稀奇,道士不像道士,为了一朵大红花什么杂七杂八的人都来了。”
夏侯天听在耳中吃了一惊,暗暗想到:“你看见和尚说什么道士,你这不是指桑骂槐吗,那和尚不生气才怪呢?”果然,夏侯天刚想到此,那净空和尚抬起头来狠狠瞪了马太保一眼,神色间,凶光暴射。
马太保被净空和尚瞪了一眼,浑身上下极不舒服,忍不住道:“这年月和尚不是和尚,出家人六大皆空,他是大碗喝酒,大快吃肉,我看他是六根未尽。”
净空听在耳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你是在说我吗?”马太保道:“我在说和尚呢?你是和尚吗?”
净空道:“兀那贼人,嘴角放干净些。”说着便将走出,突然净空目光一闪,似想起了什么,突坐了下去,嘴中不停的念起佛经来:“什么无痴无垢无颠无怒,什么无憎无色无爱无颠,——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嘴里不停念叨,左手却在桌上抠起五道长长的指痕来。可见那净空是一忍在忍。
那五道长长的指痕夏侯天看在眼中暗暗吃惊,心中道:“此人不过三十多岁,内功却如此了得,他是怎么修炼的。”马太保看在眼中,神色为之一变,暗暗道:“好厉害的功夫。”说着转过身去,不言不语了。
刹那间,酒店静寂无声,就在这时,酒店中走进一个黄衣僧人来,向众人问了一声讯,道:“诸位施主,可曾看见一个僧人。”
只见这僧人额头极宽,身穿一件灰色的僧袍,法号净惠。
净惠站在门口发问,那曾瞧见净空,净惠虽看不见净空,净空却看见了净惠。
净空一见净惠,神色不由一变,只见那碗中、盘中、碟中还有些酒肉未尽。
净空垂下头去,不声不响嘴一张,那碗中、盘中、碟中剩余的食物竟被一下吸进嘴里,点滴不剩,连一滴油滴也看不见,比水洗的还干净,同时拿起桌上的一个馒头慢慢地吃了起来。
只听一人道:“那不是和尚吗?”说着朝净空指了指,净惠顺着那人手指处望去。
一刹那间,净惠高喧了一声佛号道:“师弟,好悠闲,一人在此吃喝。”
净空还了一声佛号道:“师兄,连日来只顾赶路,我肚子空的很,一路上连个化缘的地方也没有,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有饭吃的地方,我要了四、五个馒头还没吃两个,你便来了。”
净惠“哼”了一声道:“说的到好听,我看你是又犯了戒规吧。”净空道:“阿弥陀佛,我自从净身投入沙门,寺中的戒规从未破过。”
净惠道:“你真没破戒吗?”净空道:“我说的可都是实话,你若不信。”说着嘴大张道:“你闻,我嘴里呼出的全是清新之气,决没有半丁点酒气、肉气。”
“唉,还真是的。”夏侯天奇了,暗暗到:“平常人若是喝那么一丁一点酒气便会长存口中,我明明见这僧人刚才足足喝了七碗多酒,怎么这僧人嘴中却无半毫酒气,这僧人是怎么做到的?”
只听净空道:“你怎么也来了?”净惠道:“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方丈放心不下,所以便命我来了,也幸亏我来了,我若不来怎能见到了尘师叔一人坐在树下,又怎能知道你跑在此处大吃大喝。”
净空道:“你误会了,自从了尘师父奉了方丈之命,了尘师父便带我一起去宝珠寺讲经说法,途中,我和师父用尽了所带的干粮,连日来两、三天半滴米也不曾进肚。我见师父极是辛苦,便让师父在路边休息,我前去化缘,看看能不能找些吃的。虽知我两个馒头还未吃完你便来了。”
净惠瞧了瞧净空,道:“还不快走,你师父正等着着急呢。”
净空但听“你师父正等着着急呢。”急和净惠匆匆而去。
众人但见净空走出店外,不由同时“嘘”了一声,不知多久,马太保等人觉的没趣,也向店外而去。
夜已中天,夏侯天出现在刘家锺庄院旁,看看四处无人,纵身一跃,向院墙飞去,在一纵飞向了屋顶。
只见东边一间房屋的灯还亮着,夏侯天轻身功夫使出直向灯光而去。
约莫走出五间房屋,来到灯光处,夏侯天俯下身去,揭开一块脊瓦,脊瓦一揭起自露出一个小洞,夏侯天顺着小洞望去。
只见屋中有一张大桌子,刘家锺、顾广旷、管老侠三人环桌而坐,顾广旷道:“大哥,明天“以武会友”大会不知你是怎么安排的?”
就在这时,只听顾广旷和管老侠二人“啊”了一声道:“怎会这样?”“大哥,有什么事不能直说,还要弄此玄虚,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二人。”
刘家锺咳了一声,道:“二位兄弟先莫出声,先听我说,一个月前,我听说失传了三百多年的秘籍重现江湖,我不知是真是假,便想邀二位兄弟一同前去打探。只是此事极是重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又怕信上走漏消息,故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