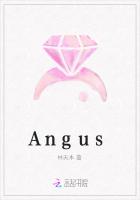此处看似无路却又能过得去,远见这种路约百步之距,林嵩在缝隙中手脚并用,到最窄处不足两尺宽,林嵩只好放下谭峭扶着他侧行。
三人走出这条路时都是衣衫划破,手腿磨伤。阿孟带着林嵩右转又入另一洞中,只觉此洞里阴风阵阵,寒冷无此,洞窟外头可见崖壁,洞内蝙蝠乱飞,好不怪异。
再走过一段石廊入一石洞,见有岔路,阿孟带林嵩不知怎么便绕出了岩洞,突然眼前霍然开朗,远见又一巨石在黑夜里立如屏障。阿孟带林嵩速入密林,走了许久,林嵩再也支撑不住,倒地喘息,谭峭经方才洞风一吹,山泉湿体,不住的哆嗦。
阿孟得意:“阿姐的主意好,这里洞洞相连,幽暗难行,山泉遮住脚步声,叫他们在洞里绕来绕去吧,等会儿到了溪边,就再也寻不到了。”
林嵩方悟:“难怪方才你自信能甩开他们,只是这种路莫说走过,想都不曾想过。”
林嵩说归说,仍不敢大歇,负起谭峭要走,谭峭见他累脱了形,便要自己走。林嵩摸他身体发烫,照旧背起他前行。
前行间听闻虎啸阵阵,林嵩大惊,阿孟笑道:“风声尔,儿当初也被吓住。”林嵩诧异不信。
此处山中仍无路,但较之洞中路好走了太多。
阿孟见谭峭醒着,以为他大有好转,笑道:“童子尿真这么灵?”
谭峭不懂:“什么?”
阿孟偷笑不答。
林嵩叹气:“他中的毒或非一种,先前他抽搐昏厥,是风毒之状,最是致命,由于处置妥当,躲过了此劫。眼下他面色青紫,身体发烫,是火毒之状,毒已入血,若不假药石,不知将会如何。此时不能多动,否则毒性发作的更快。”
?“呀!“阿孟不言语。谭峭听着暗地里叹口气。
林嵩此时累得忍不住,干脆念起了文章鼓劲:“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林嵩念着念着喘不上气,谭峭接着念:“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谭峭念着,林嵩听着走着,心里气宇激荡,似乎又有了些力气。
“本朝臣子某最敬“文贞公”(魏征)。当年某在长安做《王者之道如龙首赋》,无非也是想劝天子重自身的品行。天子是天下主,便如龙之首,百官虽多如鳞,无首也不能行。如今龙下中天,群蛇乱舞,正应了某的话。”林嵩说罢一声叹息。
阿孟惊奇:”你去过长安?那里是神仙地么?“
林嵩大笑:”高楼广厦帝王都,鱼龙混杂市井处,怎能是神仙地?你这是听谁说的?“
”阿娘的诗里讲的啊,‘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卢照邻《长安古意》)“阿孟摇着头念道。
林嵩笑着打断:”阿娘教你的?“
”是啊,她什么都懂的。“
”这阿娘何许人,懂医又懂文?“林嵩心里一阵思量。
谭峭忍不住插话:”岂不闻‘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黄巢《菊花》)’如今长安哪里还有香车啼花。大唐气数已尽,就是来一百个魏征,没有贞观之主又有何用?“
林嵩不悦:”你这孩儿怎能言此大逆不道?若是别人定不能饶你。这反诗哪里比得了‘元和公’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就算无明君,但君臣大义仍在,也需知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必违天地之道。“
谭峭来了劲头,忘了浑身发抖伤口疼痛:”不过是个’张生‘尔。(《莺莺传》)“
林嵩心里奇道”这少年什么书都读过?“嘴上却带怒意:”元和公人才诗才,身担宰辅,是天下读书人的表率,岂能由你说三道四?你虽然肚子里装了些书本,可你这是要学黄巢么?“
“谁要做那断头人,某寻的是天下之道,并非贬低先辈,而是读书人为何不能洒脱,脱出凡尘求天道,存身云霓永为仙。”
“虚妄!范蠡、张良、李靖才是真仙。”
“那伏羲女娲、黄老张葛,不是得道仙人么?”
“这些人吾等不曾见也不曾知,某来问你,你小小年纪就怕死不成,就要求仙?“林嵩竟真的和谭峭争论起来。
”某若成仙就使法术去托个明君下凡,也算是为了百姓吧?不违天道吧?总比跟着昏君谄媚,被人贬来贬去的好!“
林嵩听着猛的大乐:”果然还是个孩子。天之道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阴阳激驳,若能天定明君,之前的神仙不会定?“
”那是因为神仙都已看破天道,怎会执着于人间事。“
”什么是天道?难道人间不由人道,从何天道?“
?谭峭被问住了,他搜刮肚中所学不假思索,顺口念道:”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礼记.天地之道》)”他突然停住,发觉背错了书。
?“哈哈~”林嵩大笑:“这是求仙的道么?不过这确实是天地之道啊,教化万民,治理天下。某只听说过自己得道的仙,不曾闻教化万民得道的仙。”
?“某未得真经真丹,未知没有渡民的仙。”谭峭嘴上仍不服。
?“普度众生不是佛门的心愿么?你这道又求到佛祖哪里去了。好,某看将来你能得什么道,成为什么仙?”林嵩见谭峭扯得更远了,不住的好笑。
?谭峭暂时想不到言辞对答。林嵩忽然问道:“照你的想法,莫非你和闾山道士真有何瓜葛?”
?谭峭突然听闻此言心里一惊,便想要吐露实情,又觉得和林嵩正投缘,对林嵩的见地人品十分倾佩,生怕说了自己掘坟怀经的事令他厌恶,被林嵩瞧不起,心中矛盾嘴上打结,正犹豫不定。
阿孟安静听他俩论了许久,虽然不懂,但一直没作声,此刻不知是夜里什么时辰,她突然阻断道:“莫出声,听得到水声么?”
林嵩放下谭峭,竖起耳朵聆听,听见远处传来流水之声,阿孟也听见了,大喜:“快到了!”
不久,三人出密林到了溪边,眼前猛然一片开阔。只见有一条大溪流淌,四面再无遮拦。此时天洒轻雨,漆黑夜仍可见溪两岸奇峰相叠、山峦交错的模糊影像。林嵩赞叹:“此地若是在晴天白日,必是美妙景致!”
阿孟在这大溪的浅滩边上寻找,从一矮树丛间拖出一筏置于水上。此间水平流缓,阿孟稳稳站在竹筏上,再将谭峭接上竹筏。林嵩见是六根粗竹制成的筏子,迈脚欲上,阿孟拿起扣在筏上的竹杆,将他拦在岸上。林嵩呆望着她不懂是何意。
阿孟面带愧色道:“儿觉得你是个好人,可阿姐嘱咐吾等有规矩,只能和你到此,不可将余路带你走。”
林嵩“啊”一声,指谭峭问道:“你一人能照看他?”
阿孟点头,林嵩不言语。
谭峭急了:“他绝非歹人,如何将其丢在此处?”
阿孟对林嵩道:“请赎儿罪。阿姐叫你顺溪北上,到溪头有个村子,她们在那里等你,将那小和尚交还。你千万小心啊,跟着水声便不会走失。”她说罢竹竿一点,也不再看林嵩,也不问谭峭,便驾竹筏离岸漂去。
林嵩累极了,望着谭峭的双眼点点头,坐地下休息,心道“这阿姐心思好细腻、好周全”,他见谭峭总算是得人救助去了,此番努力也算事成,欣然目送竹筏消失于夜色中。
谭峭心中则顿时难受,方才还和林嵩谈天论道,得他一路救命大恩,自己连实话都未向他吐出一句,不由分说就此离别,也不知林嵩所谓的刺史去哪里赴任,可能从此再不相见,谈何他日报恩。
谭峭此刻望着林嵩为救自己一身污泥,衣衫破烂,孤坐在岸边雨中,心中万分感激。只是他如傻了一般,只举着手似要挥舞却不动,光见他张嘴却道不出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