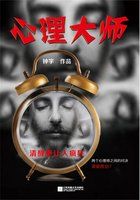院长说,看你,说着说着咋硬走呀!院长过来,把雨伞遮在他头上,雨伞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发出呼呼啦啦的声响。
白帆指了指手术室那边说,老头儿。
院长说,啥老头儿?
白帆说,他吊在树上了。白帆的话还没有说完,手术室那边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哭叫声。那哭声仿佛空中的雨水,哗哗啦啦地引来了更多的观看者。
院长说,真吊在树上了?
白帆说,那还有假,我亲眼看见的。
院长说,怕是没救了。那样吧,我找人去处理,你跟我过来,说正事儿。院长拉着白帆来到走廊里,然后把雨伞合上。院长说,孙书记和王镇长,昨天晚上就来了,我派人去找你,咋找都找不到。
白帆说,我去乡下了。
院长说,乡下也去人了。
白帆说,我又回来了。
院长说,回来上哪儿啦?
白帆说,我在手术室里。
院长说,你在手术室里干啥?
白帆说,睡觉。
院长生气了,说,你看你,书记镇长摆一桌子酒席,一直等到十点。
白帆有些受宠若惊,他说,有事儿?
院长说,镇里计划生育开始了。你知道这事儿的重要性吗?搞不好,到换届的时候一票否决。书记和镇长都急的要命,你却在手术室里睡觉。
白帆说,我咋会知道呢。
院长说,算了,今天结扎,你去准备准备吧,人一会儿就到。今天三个行政村,二十六个人。
白帆看了院长一眼,院长的面孔在潮湿的空气里仿佛一张灰纸。一些房屋和树在渐渐稠密起来的雨水里晃来晃去如同长了腿在雨中奔跑。那个男人的哭嚎声从手术室后边传过来,湿漉漉的越来越近,最终,中年人在一群人的拥挤下出现在白帆和院长的视线里。中年人背着他的老爹和从外边进来的一群人擦肩而过。那群人被那个男人的哭嚎声和他肩上的死者所吸引,他们立在雨中仔细观看。那群人披着雨衣,或打着雨伞,由于雨水的缘故,使得白帆看不清他们的面孔。那群好奇的人一直看着中年人在雨中渐行渐远,其中一个人说,这不是柳庄的柳毛吗,他爹咋了?
另一个人说,鸡巴硬。七八十了,鸡巴还硬,下都下不去,自己觉得没脸见人,就上吊了。那人说完,一群人就哈哈地大笑起来。正笑着,有两个身披雨衣的人看到了黄院长。于是他们就走过来,其中一个矮子说,院长,俺的人来了,啥时候开始?
院长说,齐了就开始。他对身边的白帆说,开始吧,早开始早结束。
那群人就过来,拥着白帆在雨水里往手术室走。在手术室门口,麻醉师拦住了那帮人。麻醉师说,都过去咋办?乱糟糟的!
披雨衣的矮子说,去,都到门诊室里等着。说完他挥了一下手,又说,叫着谁谁来!
来到更衣室里,麻醉师对白帆说,你昨天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
白帆说,又是你去的?说完他把褂子挂在衣架上,或许是他心不在焉,衣服没挂好掉在了地上。白帆拾起来,抖了抖,没想一张折叠的纸从衣兜里掉了出来,在空中像小鸟一样拽了两下滑落在了麻醉师的脚下。麻醉师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张纸,说,这是啥?
白帆说,不知道。白帆已经记不起来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了。
麻醉师说,给谁的情书?
白帆笑了,他说,你。
麻醉师说,给我写的情书?那我就看了。他一边说一边展开那张纸,他看了一眼就笑了。他说,这个婊子养的!他把那张纸还给白帆说,你被人当猴耍了。
白帆接过那张纸,看到那是院长让他填的表格。外科大夫迷惑地看着麻醉师,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麻醉师说,这表格谁让你填的?
白帆说,院长。
麻醉师说,院长对你说,表格就这一张,特地为你争取过来的,是不是?
白帆说,你怎么知道?
麻醉师不理他,继续问道,他还不让你告诉别人,对不对?白帆怔怔地看着他。麻醉师又说,因为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婊子养的!昨天晚上我往县里打电话,我表弟告诉我,咱县的科技拔尖人才已经定了,你说咱院里是谁?
白帆说,谁?
麻醉师咬牙切齿地说,黄文斌!
白帆感到意外,他自己?
麻醉师笑了一下说,这下你明白了吧?他们正说着,院长走了进来。麻醉师一看是院长,转身走进了手术室。由于院长的到来,白帆手中的那张表格再次滑落在地。院长看了白帆一眼,弯腰从地上拾起那张纸,院长的脸色变得如同屋里的光线一样暗淡。他用手指弹了弹那张纸,那张有些潮湿的纸片在空中发出了一种近似风吹枯叶的声音。然后,他叠了叠,装进了衣兜里。院长说,你这人,真是,咋给你说的?
随后院长用命令的口气说,开始吧,这可是政治任务!
白帆就糊里糊涂地上了手术台。手术台上的无影灯把他照得满头大汗,站在夜里他躺过的手术台前,一直给那些从乡下赶来的男人们作输精管结扎手术。麻醉师一次又一次地给那些身带泥土气息,双腿间散发着汗腥味的乡间男人刮去阴毛,清洗会阴部位,往阴茎上注射麻醉药液。白帆一次次地切断那些壮汉们的输精管,然后扎住。上午晚些时候,突然上来了一位女人,女人的结扎手术要比男扎复杂得多,这要切开女人的小腹。麻醉师疲倦地伸了一下懒腰,他嘴里嘟囔了一句,这个婊子养的。那天上午,麻醉师的话使白帆再次想起了院长。在沙沙的秋雨里,外科大夫的肚子突然有些发胀,他感到肚子里有东西一直在往下坠。可是面对刚刚切开的女人的肚子,他又没法离开,他的肚里越来越沉,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一泡稀屎就拉在了裤裆里。那泡稀屎的热臭气息,片刻就布满了整个手术室的空间。在那臭气里,外科大夫感到双腿都在打颤。在无影灯下,外科大夫大汗淋漓,器械护士掏出手帕,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擦汗,白帆就那样站着,直到他为那个女人缝完最后一针。
那天上午,白帆清洗完自己身上的脏物换了一条裤子之后,感到自己的骨头就要散架了,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想躺下来休息的愿望。当人们离去之后,他就在堆满手术衣的长椅上躺下来,那些布满血迹的手术衣在渐渐沉睡下来的白帆身下散发着血腥气。手术室里慢慢地沉静下来,只有白帆微弱的呼吸声像一只秋后的蚊子在无力地飞行。窗外的秋雨在他的睡梦里没完没了地下着,那天他睡着之后,梦见了那个阴茎充血的老人。白帆看到他赤条条地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握着自己的生殖器。白帆说,你不是走了吗?
老头儿说,我上哪儿去?你看它一直不下去,我胀得难受。一群女护士站在他的身后指着老头儿嘻嘻地发笑,白帆回过头来对她们说,这有什么好笑?他只不过是得了一种病。
老头儿在白帆的面前跪了下来说,大夫,求求你,给我作了吧,我真的没脸见人了。白帆说,那好吧。白帆说完,就领着那个老头儿走进了手术室。在他的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那走廊好像没有尽头,白帆一直沿着长长的走廊行走,他走得好累好累,却怎么也走不到头。走廊的两边没有窗子,自然的风光和季节的变换离他十分遥远,在灰红的灯光里,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在一块镜子面前,他看到自己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他赤身裸体,他的阴茎在他的双腿之间不停地膨胀,那阴茎越来越大,最后充满了长长的走廊。
五
白帆在睡梦里感到耳朵发疼,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妻子柳鹅。柳鹅一边拧着他的耳朵一边指着他的脸说,好呀,你个鳖孙,家也不要了,躲到这儿来睡了!
白帆说,放开手。
放开手?你光想哩,走! 柳鹅拧着白帆的耳朵,拉着他就往外走。
外边的雨不知道啥时候停了,医院里的许多人在那个空气潮湿的上午,都看到了瘦弱的外科大夫被他肥胖的妻子拧着耳朵拉着往外走,白帆弯着腰,小跑着跟在柳鹅的屁股后面,他一边用手护着自己的耳朵一边说,放开我,放开我……
柳鹅不理他,只管拧着他的耳朵在众目睽睽之下往外走。这时,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拦住了她,说,放开他,有啥事不好说?
柳鹅说,放开他?没那么便宜。家里的房子漏得哗哗淌,他管都不管,躺在这里睡大觉。说完,拉着又走。这时院长走过来,院长说,放开他,下午还有工作。
工作?柳鹅说,有工作看着俺了,有好处咋没有看着俺?说完,拉着又走。
院长又要拦,柳鹅说,谁拦我,我日他娘!院长的脸一红,就让开了。柳鹅拉着白帆又走。就这样,她拎着白帆的耳朵穿过镇子回到家里。柳鹅咚地一下上了门,抱起白帆,把他丢到床上。
白帆一手捂着耳朵一边看着屋顶说,哪儿漏了?
柳鹅说,哪也不漏,恁老娘的裤裆漏了!说完过来,三下两下就剥了白帆的衣服,接着,她那一身白白的肥肉就压上去。白帆可怜巴巴地躺在她的身下,任她怎样摆弄也强壮不起来。白帆颤抖着说,我不中了,我不中了……
柳鹅说,鳖孙,啥不中了?你来。说着,就把他的手拉到她的腿间,另一只胳膊揽住他的头,把一个乳头摁到他嘴里。白帆像个婴儿缩在柳鹅的怀里,用手用嘴侍候着她,片刻,她的身子就扭成一团,嘴里不停地哼叫着。她的哼叫声像针一样刺着白帆的心,这让他无比的痛苦,外科大夫突然像个孩子坐在那里哭泣起来。他的哭泣声,把她从快乐里拖出来,她一个耳光扇在白帆的脸上,说,哭,好好的哭个啥?
白帆不但没有停住,他哭得更伤心,他哭得泪水涟涟。这下可把柳鹅给吓住了,她搂着白帆说,你看你,不是给你玩的吗,你哭啥哭?跟死了老娘似的。
白帆说,柳鹅……
柳鹅说,弄啥,你说?
白帆一边擦着鼻涕一边说,我不中了……
柳鹅说,这是啥话,好好的,咋不中了?
白帆说,硬不起来了。
柳鹅笑了,她说,笨蛋!我想啥事呢,年轻轻的,多吃些东西,多睡几觉,就过来了。你别伤心,往后我不找别人还不中?柳鹅一边给他穿衣服一边说,看你,真像个孩子。起来,好好吃饭,我给你弄肉,好好地吃一顿,休息休息就过来了。
柳鹅说着,就从柜子里端出来一盘猪杂碎,她说,吃吧,吃了就好了。
白帆看着那些油汪汪的猪杂碎,突然想起了袁屠户。他说,这肉从哪儿弄的?
柳鹅说,你问从哪儿弄的干啥?是肉就香。说着,自己倒先拿起半个猪耳朵吃起来。这时,袁屠户劈猪头的声音从窗子外边传进来,嚓--嚓--油亮的砍刀把带血丝的骨头劈得四处飞溅。柳鹅拿起一块肉塞到白帆手里,她一边嚼着一边说,吃吧,吃了就好了。
白帆闻到猪肉的香气就想呕吐,可是柳鹅却把一块猪肉塞进他嘴里,柳鹅一边塞一边骂道,鳖孙,吃呀,不吃啥时候会好?
猪肉的香味像一只手塞到白帆的胃里去,这使白帆感到恶心,有一股热酸的东西从他的嘴里喷射出来,他蹲在地上,想把胃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外科大夫呕吐着,脑海里却奇怪地闪现出一些人体的器官来,他时常要把那些器官切开。肌肉,大肠,盲肠,胃,头颅,等等。那些东西现在仿佛变成一筐子煮熟的食物放在他的面前,呼呼地冒着热气。这种想象使他感到更加恶心,他不停地呕吐,连胆汁都快给吐出来了,他吐得面色蜡黄,像一个接近死亡的人。
这个时候,后墙上的窗子突然被拉开了,他听到袁屠户说,咋啦?
柳鹅说,吐哩,一吃肉就吐。
屠户嘲笑道,不能吃肉,还算个男人?
白帆猛地站起来,由于头晕他险些跌倒,他争扎着抬起手指着屠户的脸说,滚!他转身端起那盘猪杂碎朝袁屠户砸去,可惜他没有力气,那盘东西没有飞到窗前,就掉在了床上。柳鹅一边叫着一边爬上床,把肉捡起来,她指着白帆的鼻子说,你不想叫老娘吃了是不是?有本事你给我钱!
面前的情景使白帆感到绝望,他又蹲在地上哭泣起来,他的哭泣声像一株在寒风里摇摆的柳树,他难受的样子,使柳鹅都动了心,她把他抱起来,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柳鹅说,哭啥哭,真不像男人。白帆的身子在她的怀里缩成一团,白帆说,我怕。
柳鹅说,在自己家里,你怕个啥?
白帆指着窗子说,我怕他夜里掂着刀子过来……
柳鹅说,他反哩!说着,她自己的后背也有些凉飕飕的。
白帆哀求着说,咱把窗子堵上吧?
柳鹅说,堵上就不怕了?
白帆说,好一点。
好一点咱就堵。柳鹅说,说实话,我也有点怕。
白帆说,你怕个啥?
柳鹅说,屠户的鸡巴上有个疙瘩,还淌脓,我怕他有病。要不,你先给我看看吧。说着,她就脱下裤子让白帆看。在她的双腿间,白帆闻到了一股子腥臭。白帆说,你染上病了。
柳鹅一脸的恐惧,她叫道,你得赶紧给我治呀。
白帆说,治病好说,咱得先把窗子堵上。
柳鹅说,堵窗子容易。她站起来,三下五去二就把屋子收拾了,接着她出去喊了两个泥水匠,两个小时没过,就把窗子给堵上了。晚上白帆回来,给她弄了几包中药,放在药罐里熬,然后连喝带洗,一连七天,才除去那里的腥臭。到了第八天夜里,在柳鹅的引诱下,白帆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自己更像一个男人。他哭着对她说,我不中了,我一点都硬不起来了。柳鹅说,这咋弄?都年轻轻的,这事儿跟吃饭干活一样,不能干这事儿,人活着还有啥意思?
白帆擦一把眼泪说,你不就是想快活吗,我叫你快活就是了。于是,他就使尽了全身的解数,想法使她快活。一到晚上,柳鹅就躺在那里对他叫。一到那个时候,白帆就想扑过去一下子掐死她,可他没那个勇气,他真的像一条狗,在她的生活里走来走去。有一天,他痴呆地坐在门诊室里望着外边的阳光发呆,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他想,要是太阳永远不落那该有多好呀,他开始惧怕黑夜的来临。他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太阳不落,那该有多好呀。
年轻的女器械护士停下手中的毛线活儿说,那不可能,天总会黑的。
白帆说,要是不黑有多好,那样我就可以不回家了。
多情的女护士看他一眼说,你不想回家?
白帆说,我不想回家。白帆惧怕黑夜的降临,就是惧怕回家。一到天黑他就会忍不住哆嗦起来。他喃喃自语地说,我不想回家。
女护士错误地认为这是年轻有为的外科大夫对她的暗示,或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她激动地把打了半截的毛衣搭在白帆身上量着大小。她说,这样的颜色你喜欢吗?
白帆握着她的手,像一个孩子看着她说,我真的不想回家。
女护士说,不想回家还不容易,医院里的住宅楼不是盖好了吧,你去要一套,不就有自己的家了吗?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女护士的话提醒了外科大夫,随后,白帆找到了院长。那个时候,院长正躺在沙发上挖耳屎,他一看是白帆,脸色就变得一片阴暗。院长说,我正要找人去叫你。
白帆说,有事吗?
院长说,我问你,俺娘那事儿,你都给谁说了?
白帆说,啥事?
院长说,你忘了?那事就你跟麻醉师知道。
白帆还是想不起来院长说的是啥事,那些日子闯进他脑海里的事儿实在太多了。看白帆不明白,院长又提醒到,你给俺娘做手术的事儿。
白帆这才想起来,但在他的感觉里,那事儿似乎离他已经十分遥远,他恍惚地记得,有过这么一个手术。在这期间,他已经做过大量的手术,大量的手术把他的记忆给搅乱了。白帆说,那咋了?
院长生气地说,你都给谁说了?
白帆说,没有呀,谁也没有。
院长说,没说?没说外边的人咋都知道了?传得满城风雨,让我都没脸出门了。
白帆想了想又说,我真的没给谁说过。
院长说,你再仔细想想,比如你老婆?
白帆摇摇头说,没有。
没有?院长不相信,仍用审问的口气逼问道,你知道这事儿是谁讲的?
白帆说,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