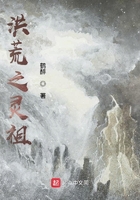她显得很不耐烦,告诉我到二〇一,我仓皇上楼。结果二〇一的门关着,门口有个罗盘状的标志,分为几格。吃饭,巡诊,离开。指针放在“离开”一格。我知道如果现在去问护士医生的手机号,只会碰一鼻子灰。陈秘书常来看凤成泽,一定有这边医生的联系方式。
陈秘书已经不再是秘书,她说自己现在是人事部的副部长。她对人的记忆力很好,我一报自己的名字,她便换上熟络的口吻。其实我302们只见过两次,都在五年前。一次是我受到胁迫之后跑去赖威的写字楼质问凤成泽,另一次则是我被秦拓硬拖去他们公司的多少周年酒会。
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她给蒋海峰写信,让他针对三〇七病房的病人做研究。
她的愕然不像是装出来的。蒋海峰是谁?她问我。
我一时间尴尬起来,只好说,我去看过你们凤总。
她轻叹一声,你倒是有心。我自己现在去得也不多了。工作和家里都是一堆事。
我这才影影绰绰地想起,秦拓说过,Linda陈是凤成泽的情人。
我不太记得她的相貌,只记得她高而瘦,在酒会上穿着高跟鞋,显得更加笔挺,像竹。
追忆那场酒会,不免想到秦拓。我把难受劲儿压下去,问她:对了,你负责人事,我想大概知道,你们公司负责喜梦项目的人是哪一位?
我以为她可能回避这个问题,没想到她说:怎么,你不知道?是秦拓。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她的声音柔和:他在我们这边做顾问,报社的人其实都知道的。
但我早就不是报社的人。我勉强说道:是吗?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想了想:一开始就是他。〇三年初吧。
我谢过她,挂了电话。让我发懵的不在于秦拓的身兼二职,而是〇三年初这个时间点。何琴找蒋海峰做出月光酒,是在二〇〇三年的夏天。为什么喜梦的项目更在那之前?
然而能够回答这一疑问的人已经不在了。
当天夜里,我在一家相熟的咖啡馆吃饭。等咖喱饭上来的时候,我给蒋海峰打了个电话。我对他说,给他写信的人恐怕是赖威的,难怪他之前寄去的解药没了回音。我没提秦拓的名字。现在回想,秦拓第一次见到他,就言之凿凿地说起解药云云。
“人家都有解药了,你之前带着数据躲起来,实在没必要,”我说,“对了,你的电脑拿回来没有啊?”
“老耿还给我了,”他在电话那头说,“我现在觉得,相比之下,赖威没什么可怕的。”
我猜他的意思是,可怕的是那种酶。或者蛊。早已存在、又被他呼唤出来的怪物。不,是被我。
“问个问题,你以前说,任何生命体都有意志力。你觉得那东西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隔了片刻又说:“塔玛对我说过,她身上有世世代代的白洁,包括何琴……”
“你真相信那种酶会传递记忆?”我当然记得在黑暗中的对话。何琴说,借着月光花,记忆轮转不休。
他不答反问:“你听过格萨尔王的传唱人吗?记忆有时候会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传承。”
和科学家说话就这点讨厌。他的思路不断围绕一根轴线振荡,感觉像和橡皮筋对话。你扯过来,他弹回去。
我不知怎的有点气,也许是气他的专注。他有研究,得以忘却一切,把所有情绪藏起来。而我只能背负痛楚和纷繁记忆。我忍不住说:
“那我如果吃了皎粉,我也会有何琴的记忆,还有她之前的什么白洁的记忆?”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他审慎地说。
我挂了电话。
咖喱饭送上来,我大口大口地吃完,然后往沙发一倒,抬头看天花板。
这家咖啡馆的天花板是何琴画的。他家的咖啡和饭菜都一般,也许我是为了看画才经常来。看了那么多次,我不用仰望也知道那上面画了什么。
两个女孩。
方形的对角线两端是两个女孩的侧影,肩部以下被鲜花簇拥。她们一个蓝发蓝眼,一个棕发黑眼。这一幅算不上何琴的佳作。有一次我和她在这里吃饭,老板听到我们谈论墙绘,半凑热闹地请她画画。
这家老板是个小气的老男人,压价厉害。何琴倒不是那种会因为报酬少而敷衍了事的人,她在画完后对我说,画天花板比墙累多啦,发挥不好。
隔了许久再看到天花板上的画,我发现暗绿色的天花板多少有点褪色,一角甚至有少许剥落。该找人来修补一下。那些装饰性的花朵也显得暗淡无光。也许是心理作用,我觉得花丛中的白花很像是月光花。以前一直没注意。我数了数花瓣,是四瓣。我再从头打量看过无数次的天花板,女孩的侧脸,花。
一个细节从不再鲜艳的颜料中浮现出来。只有一边的女孩周围有月光花。棕发的那个。花丛中有片我一直以为是枯叶的东西,在我这么仰着脖子使劲看的过程中变得清晰。那是她的手。
植物中间是她枯叶模样的指尖。她正在变成植株。凋零颓败的。
我太过震惊,以至于低下头,开始咳嗽。咖啡馆的女孩匆匆走来,在我旁边放下一杯水。我拿起桌上的纸巾压着嘴。一件往事袭上心头,也许是因为头顶的画,或因为白天目睹的凤成泽。
那是在何琴把我从杭州找回来后不久的某一天。
刚熬夜写完一篇稿子,我感到饥肠辘辘。环顾四周,我才发现本来躺在沙发看碟的何琴不见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我们为看碟的事有过几句争执。我说我要写稿,你能不能声音轻点。她显得有些诧异,说你以前从来不介意旁边有声音的。我说那我现在介意了,请你静音。
305她咬着嘴唇,按下静音键。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恶声恶气。是因为秦拓。秦拓以前也关心何琴,可最近有些变本加厉。我心里不觉打了个结,各种阴暗情绪在那个结里往复流窜。我甚至在心里对何琴说:也不想想你来上海是靠的谁。我这样待你,你呢?
现在稿子写完了,我心情一松,开始自我厌恶。人真是矛盾。我总是尽量不以何琴的恩人自居,可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泛起尖酸的念头。
电视屏幕已经回到初始的影碟选单画面。持续着静音。我猜何琴大概在洗手间。
我起身往厨房走,想去找点吃的。经过洗手间门口,正好撞见何琴从里面出来,她手上有个装着液体的可乐瓶。
一阵难言的厌恶涌上我的心头,刚缓和的情绪又绷紧了。我听见自己尖声说:“你这是躲起来喝酒哪?用不着,我当没看见。只是请你待会儿别撒酒疯。”
她神色恍惚,像是没听见我的话。我在心里叹了口气。看来,何琴喝的不是一般的酒,而是该死的月光酒。对她来说,那玩意儿十足像毒品。纵然对她有种种的不满,可我很难和一个连起码的自控都缺乏的艺术女青年计较。我伸手夺过可乐瓶,另一只手扶住她的肩,劝慰地说:“别喝了,回去躺下。”
何琴的眼珠微微转动,仿佛对焦不准,好半天才转过来朝着我看。
我不由得暗自吃惊。她的眸子清澈得像假的,那其中缺乏情绪,我几乎能从里面照见我自己。
她开口说话,声音沙哑。“大头,你饿了吧?我给你煮碗面?”
我看她不像有事,点头说好。她顺手拿过可乐瓶,去了厨房。
肚子越来越饿,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去厨房张望。锅在煤气灶上发出沸腾声,何琴却不在灶台前,她面朝水槽站着。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下一秒,她忽然用脑袋撞一侧的墙。是真撞。咚,咚咚。何琴把整个脑袋往墙上用力撞去,声势之大,足以让邻居投诉。
我冲过去揪住她。“你疯了!大半夜的!”
她像是忽然失去了全身的力气,顺着墙往下滑,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人十足的醉态,脸上露出一丝奇异的微笑。“我没事。”
我拖着她站起来。她浑身绵软,硬是甩开我,走回煤气炉边,关掉火。我叹服地想,喝醉了还不忘煤气安全啊。紧接着却见何琴劈手把一锅煮好的面全倒了。我愕然盯着她看。
她毫无歉意地说:“面煮坏了,你重新弄吧。”
说完她就走出去了。我无奈地动手烧水煮面,一边想,她如果再不戒酒,这日子没法过了。何琴装酒的可乐瓶敞着口搁在一边,想到她很有可能边喝边煮面,我更加来气。按往常的性子,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酒统统倒掉。我拎起瓶子,酒味儿混合着腐败的气味钻入鼻孔,使我猝不及防地想起夜色中的月光花。那些幽微泛白的花朵。
还有何琴画在墙上的花,以及她在昏暗中发光的脸和手。
伴随着各种印象浮现的是她清醒时的脸。既远又近的少年时光。
紧接着,之前对她和秦拓的猜疑重新梗在心上。像一支难言的毒刺。
如果我是秦拓,大概也会对这个酗酒的女人心存莫名的怜惜吧。
她的才华和自弃,她的飞扬和失落,混合在一起,形成不算鲜烈却隐约泛光的吸引力。
如同那些带着邪恶又显得凄清的白色花朵。
我倒要看看你会走到什么境地。你和你的酒。
我在不熟悉的恨意的驱使下,把可乐瓶的盖子重新拧好,塞回冰箱。
几天后,秦拓带我去参加赖威的年度酒会。
我说我不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秦拓笑起来,说你不至于这么小心眼,赖威那边我去谈过,人家把擅自找人威胁你的那个经理给处分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说,一码是一码。我不为他们威胁我的事,我只为他们的种种恶行。赖威根本不关心可持续发展,就因为他们收购一种树皮,现在但凡长那种树的地方,树皮都被人剥光了,眼看着那种树就要绝种。
秦拓说,这只能说明当地人利欲熏心。
我说,还有,他们在江苏搞的某工厂,影响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湖泊。这总不能怪当地人了吧?
秦拓继续辩解:当地和赖威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该注意排污的条款,这件事双方都有责任。
我有点气:你是收了赖威的好处还是怎么的?总帮他们说话。
秦拓语重心长:我们做媒体的,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赖威也算我们广告部的大客户,你别这么拧巴。凤成泽人不错的,你上次冲上去骂人,他都没在意。这次我给你正式引见一下。别人还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呢。
我气极反笑:是吗,我还就该巴结他?他就那么稀罕!
秦拓说:你知道,赖威在中国除了不做毒品和军火,什么都做。这样的公司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算十分少见。而赖威的今天,和凤成泽脱不开关系。你还年轻,气盛也是理所当然。不过凡事还是该谦虚点,多看看多学学,多认识人,总没错。
我感到心头有根弦被拨了一下,呆呆地听着。秦拓以为说服了我,高兴地一笑:下班回家换身裙子,别这么休闲。
鬼使神差地,我把何琴放在冰箱里的酒带到赖威的酒会。我拿了一只装化妆水的旅行小喷雾瓶,倒入散发着轻微腐味的透明液体。
我依然不明白何琴为什么迷恋这种古怪的饮料,她曾经严词禁止我碰她的酒。仙人谷的所谓仙酒就是这玩意儿吗?我盯着小瓶子看了半天。
那天我做了一件傻气的事。在酒会上,我把何琴的酒放入伏特加兑橙汁的酒杯,又把那杯酒送到凤成泽的手边。我穿着自己惟一一条正式场合的小黑裙,在秦拓身旁像个淑女似的微笑。我心怀恶意地想:
除了毒品和军火什么都做的凤总啊,请你尝尝这个类毒品的酒。
这就像抛硬币的赌局。结果要么为正,要么为反。如果何琴的酒真有什么诡异,那就让凤成泽体验一把。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搞出这样一件近乎孩子气的闹剧。要是被人看到,说不定会以为我给凤某下毒。幸运的是酒会闹哄哄的,无人发现我的小动作。之后,我看着他啜饮那杯酒,隐约带着期待。
凤成泽似乎有短暂的恍惚,但他很快恢复了谈笑风生,让我以为刚才只是自己的错觉。酒会上没发生任何异常,除了一名女记者大概和我一样不习惯穿正装,凄惨地崴了穿高跟鞋的脚。
当我发现喜梦的究竟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会不会和我当年那个拙劣的恶作剧有关?但我每每转念,把不安的火苗掐灭。伴随着一路的追寻,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类似后悔的情绪始终噬咬着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