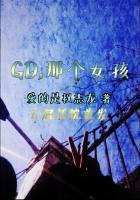那就只有躲。本以为宁县够偏的,讲出去都没几个人知道的地方,债主竟然追上门了。她嫌家里气氛沉闷,白天都出门去同学家,也不讲自己去了哪里。有一天傍晚回到家,小妹站在门边等她,一看到她就哭:姐被他们带走了!
何棋吓得不轻,问小妹,小妹哭着讲不清。她觉得血往上涌,冲进家里。爸坐在堂屋抽烟,妈躲在厢房抹眼泪,说话都没了章法。她没办法,只能问几年不交谈的爸:我姐呢?
爸说:她带着讨债的去西山了。何棋再怎么问,也就是这一句回答。她叫起来,说要去找派出所。爸瞪她一眼:不许去!先等等,先等等……说到后来,他像是疯魔了似的。何棋开始害怕。她一个人走出家门,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就在村口的土路上来回地走。刚下过雨的红泥地,一走一脚泥。她恨这些泥。她也恨那栋她长大的房子。她恨妈这么多年惯着爸,惯得不成样子。她恨自己还没工作,没有自立。小妹也和她不亲,只有大姐是她不恨的。想到大姐,她想哭,更有种想要尖叫的冲动,但她能做的只有在那里来回走。偶尔有村里人经过,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她两眼,不打招呼就进村了。他们大概已经听说老何家欠了赌债回来。现在谁也不敢沾他们家的人。
近处大路的路灯亮了。远处公路的路灯也亮了。何棋来回走得精疲力尽,原地蹲下。附近一户人家的二楼亮过灯又熄了。她蹲在漆黑的村口。田里的蛤蟆在叫。她想,要是找派出所,是不是第一个被关起来的是爸?她的眼睛闭上又睁开,睁开又闭上。迷迷糊糊之间,她看见几点荧光朝这边接近。是鬼火。不对,鬼火应该是绿幽幽的,那些光点是白的。她强迫自己站起来,睁大眼睛。光点离她越来越近,她想跑,想喊。光点那头有人说:吓死人了,你做什么黑灯瞎火站在这里?
是姐。她一阵欣喜,忘了刚才莫名的惧意,她扯住姐问:你没事?
那些人呢?爸说你把他们带走了……姐说:人走了。没事了。
姐出去打工那几年,先是何棋睡姐以前的阁楼,等何棋也出去念书,阁楼成了小妹的房间。这些天三个姑娘都在家,妈把两个小的以前住的小间收拾出来,让何琴何棋睡一个屋。
何棋和姐回到家才发现,那些发白光的东西是一把连根带土的花,到了屋里在灯下,看着就是普通的白花。姐的脸色惨淡,却有些亢奋。
爸问起,她也只是说,人走了,没事了。就这么一句话。
当晚,她和姐洗完脚准备睡了,爸来敲门。爸也不进来,站在门口说:你是我家姑娘,你要真有事,我……我找他们拼命。你跟我讲实话……何棋这才朦胧地意识到,姐不会是被人占了便宜吧……她的心一紧。
姐站在门边说:我没事。你放心好了,那两个人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对了,他们家人知道他们来宁县吗?
爸说:他们也是在外打工的,去哪里也忙不赢和家人讲吧。
姐说:那就好。
很久以后,何棋才从妈的嘴里一点点问出事情的经过。上门讨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债主,一个是帮衬的,都是四川人。他们来了以后,看看这个家,也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两个人的眼睛四处瞄了一圈,又往何琴身上看。一个说:太瘦。另一个说:也太黑,你说这个长得怎么就不像老何。第一个又说:小的那个倒好,不过还是个娃娃。念初中的何书一听,吓得躲进阁楼不肯下来。何琴若无其事,在家摆了一桌酒菜请他们吃喝。爸面色讪讪的,在旁作陪。酒喝到半酣,何琴拿出一只银镯,递给那两个人。是一只老银镯,嵌着翠玉。两个人的眼睛亮了,不知是因为玉光照眼,还是喝了酒的缘故。债主说:镯子倒是不错。帮衬的说:不过这哪够啊?何琴说:我在一个山洞里捡的,那地方很隐蔽,别人不晓得。洞里有死人骨头,还有其他首饰。就看你们敢不敢跟着我去。
妈讲述的时候掉了泪:她一个姑娘家带人进山,我死活拦不住,你爸只会在旁边闷头抽烟。谁想到,最后她自己回来了……那两个人,那,那恐怕是出事了。你爸是这个样子。你跟何书还小。你姐是我惟一的靠头。可现在……妈再没往下讲。那之后没几天,姐离开云南,去了上海。爸又待了几天才走,走之前,他把两个姑娘叫到跟前,用力叮嘱:要有人问你姐在哪里,就说不晓得。记住了?
说完这段经过,何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我知道,她这口气淤积多年,如鲠在喉。
“其实,我这些年常做噩梦。梦见警察把我姐带走了。现在她一点音信没有,我心里发慌。但如果真是当年的事发了,我应该能听到消息。”
我说:“我心里有数,你告诉我的事,就到我这里为止。我会尽量想办法找她,你别太担心。不过,那个银镯是怎么回事?”
“是我姐在古城收的,本想转手卖出去。”
最后一丝疑惑消失,我心头雪亮。何琴当然是把人骗到了仙人谷。
她无力替父还债,对方又来者不善,所以她想到这条下策。那两人竟会跟去,也真是财迷心窍。可能他们觉得两个大男人不至于对付不了她吧。可是,那鬼地方究竟在哪里呢?我记得自己以徒劳告终的搜寻。
秘道以及我们进山时走的路都试过了,底下只有妙谷。
所以她来上海的时候带着月光花。可笑我当时没有半点疑惑,还以为是她多年前从谷里带出来的。她什么都没说,她再次去仙人谷的事,还有债主的事。我回想起〇三年夏天的何琴,心头黯然。
何棋邀我吃饭,我说不了,有朋友在等我。她一直把我送到警局门口。她走在身旁我才发现,这个妹妹比何琴高,也多了些丰满。她的步伐带着年轻的韵律,尽管前一刻她刚吐露过家中的悲哀秘密,光看走路的样子,你会觉得她的生活单纯又明快。
窄街被正午的阳光烤干了,昨晚的大雨显得不像真的。街边走过一拨拨的游客,他们端着相机,见到什么都大惊小怪地拍摄一番。
何棋和我告别,回身进了大门。我再一次感到饥肠辘辘,刚迈步就听到有人喊我。我一看,马路对面站着秦拓。他身穿翻领黑T恤和牛仔长裤,斜背一只牛皮小方包,墨镜遮住了他的表情。我的心扑通一跳,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还有一个我羞于承认的疙瘩——他当然看见何棋了。
我穿过马路走到秦拓面前。他张开手,似乎想给我一个拥抱,最终只伸手揉一下我的头发。
“你啊。”他叹了一声。
我嘿嘿笑,和他并肩走起来。秦拓问:“刚才陪你出来的人是?……”
“何琴的妹妹。”
“哦,案子报下了?”
他问得漫不经心,他站在这里等我,自然是从泉那里听说的。
“没正式报下。蒋海峰还在人家手上。警察最多上门问一声,如果他本人不肯走,就没办法。”
秦拓摘下墨镜拿在手里,偏过头看我的脸。
“我听说,那个叫塔玛的女人是卖喜梦的。随便扣人,这不成了传销!”
我苦笑:“她比传销厉害多了。我饿死了,先去吃饭吧。泉还在客栈?”
他愣了一下才说:“哦,在饭店等着呢。”他显得有些恍惚,不像平时。我明知故问:“在想什么?”
他迅速地回答:“没什么。”停了片刻又说:“刚才那个女孩子太像何琴,吓我一跳。”
“亲姐妹嘛。不过一说话就不像了。”
我们这时已经转到人民路,顺着坡往下走。两旁大多是咖啡馆和饭店,除了游客,还有若干穿民族服装的女人背着麻袋,或走或歇。
一个眼角皱纹如蛛网的女人过来问我要不要银首饰。她在问的时候就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眼睛和声音透着漠然。我摇头,心想,何琴的银镯就是来自这些二道贩子吧。
街景似乎没映在秦拓的眼中,他忙着教训我:“你从前天晚上不回我电话,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你啊,下回再也别这么冒失,搞什么明察暗访,你这次逃出来真是运气好。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你的下落,对不对?你现在去哪里也不和我说,神神秘秘的。”
我捉摸不清,他究竟是因为我没有随时和他联系而不满,还是在气我的冒失。我乖乖地一声不吭,再说也没力气回嘴。
秦拓自己先软下来。“我知道,我没资格要求你汇报行踪……可我担心你。”
我停了片刻才说:“我知道。”
“还有啊,”他又开始絮叨,“深圳那个,叫什么泉,这不是真名吧?你也说过他是开酒吧和赌场的。和这种人一起,你别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还帮人数钱?”
他闭上嘴,大概觉得和我讲话太浪费精神。他往右一转,带着我进了一家饭馆。辣椒在油锅里爆香的气味千回百转地钻进鼻孔,我顿觉腿软。穿过走道,里面是个摆满桌椅的大院子,每张桌前都坐了人,四周的厢房似乎是包厢。桌椅一直摆到了走廊,泉坐在东厢房门口的走廊上,正在吃喝。
等我们走近,泉停了筷子,眼中闪过一丝戏谑。
“没成吧?”他指的是报案。
“没成。”
“你还不如学我,直接来吃饭。”
我坐下,拿起筷子。“要都像你,坏人岂不是得意死了。”
他挥手驱赶苍蝇。“哎,云南的餐馆都有这么多苍蝇吗?”
我没再接他的茬,大口吃饭,几乎是狼吞虎咽。秦拓帮我夹菜添茶,不时轻轻说一句:“你慢点吃。”一碗米饭下肚,我往椅背一靠,满足地叹道:“人是铁饭是钢啊。”
“说得好像就你一个人从昨天到现在没吃东西。”泉又和我抬杠。
我回敬:“你可以吃药扛着,我不行。”
泉微微变色,这次总算没继续斗嘴。我说要喝啤酒,秦拓喊服务员,端盘子的小伙在桌间穿梭,遥遥冲我们喊:“自己到前台拿!”秦拓刚走,泉再度开口:“你说有朋友来,我没想到是他,报社的秦主任。
一来就给我一张名片。”他从鼻子笑了一声。
“你知道秦拓?”
“你的EX嘛。何琴说他配不上你。我一看,说得挺对。”
何琴的评价让我意外。泉又说:“你们复合了?他好像是担心你专程赶来的。”
“别那么八卦好不好?我和他是朋友。”
他哼了一声。“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女怕上错床。这人看着不大正派。”
笑话。我心想,秦拓看着不正派?难道你看着正派?不过现在不是就此辩论的时候,我问:“对了,蒋海峰的包——”
秦拓拎着啤酒回来,我怕他听到话题又来一顿批评,暂时闭了嘴。
两个男人彼此瞧不上,却是有说有笑。秦拓说他差点就在深圳工作。
泉说,下次来深圳打个招呼,我带你去南头吃海鲜。他们这种貌合神离的外交谈话是我永远学不来的,我只管努力吃喝。
秦拓主动去买单的空当,泉接过隔了许久的半截问句。“我问过青旅前台,他的包寄在那里,昨天被人拿走了。是你我都认识的一个人。”
“阿魁?问题是前台怎么会交给他?”
“你想不到他是什么人吧?那小子是下关市的警察,做着公职,开着客栈,真是爽死了。”
我很难想象穿人字拖的阿魁换上警服的模样。不过老同学当中也有不像警察的警察。宏平当年是最胆小和拘谨的一个,他和小六选择跟着大队走,没参与我们那次采标本的历险。他如今长成一个好酒量粗嗓门的男人,酒局上就数他话多。
泉接着说:“快中午的时候,你的EX到了,我把大致情况一讲,他马上急着去找你。他前脚刚走,阿魁后脚来了青旅,披了一身警察的皮。”
“你刚才怎么不说?”
“我要说了你还会好好吃饭?你别急,阿魁让我给你带个话,说是有朋友在金花客栈等你。他自己跑去下关上班了。”
我站起身,正好秦拓走回来。他背后是缀满红艳艳花朵的石榴树和狼藉的餐桌,阳光洒下来,苍蝇在盘旋。穿件不张扬的巴宝莉的秦拓和这一切莫名的不协调。
“我们走吧。”我对秦拓说。
“和我回上海?”他的口吻半真半假,我知道,他也知道,表面的戏谑往往是为了讲出真心话。
“好啊,不过要先去一个地方。”
我感觉到秦拓的震惊,也许是因为我说了“好”。其实我自己同样一惊。直到说出口我才意识到,我必须去一趟仙人谷,不论是否能找到那地方。
11.终点也是起点
泉在饭店门口说,他一会儿不和我们过去了,他回青旅,然后回深圳。看样子,他甚至不打算回金花客栈拿他的背包。我把他拉到一旁,轻声问:“你还好吧?”
他目不转睛地看我。“这么温柔不像你啊,我还以为你会发火。”
“我发火做什么?”
“我没陪你接着找何琴,不够朋友。”
“谁说我要接着找何琴了?我去趟金花客栈,见完人说完话,拿上行李走人。我也该回上海正经找份工作了。”
泉从鼻子里笑了一声。“你骗鬼啊。”
“你真没事?”我又问他。
“如果你指在塔玛那里被灌了药……我没事,虽然当时的感觉很怪。和我平时自己吃喜梦看到的幻觉不一样,”他停下来思索,“就好像,脑子里有别人的记忆。”
“塔玛说他们一起吃喜梦是‘分享’。也许是你和那伙人产生了共同的幻觉,一起吸大麻的人有时也会看到相似的幻觉。”
他不置可否,眼神有点远。“程妙,你从来就没有害怕的时候吗?”
“当然有。你应该注意到了,我怕黑。”
“我不是指那个。你好像一点也不怕喜梦,还有你说过的那个浓度更高的药……”
“皎粉。”
“我是真的怕了,见过塔玛之后。科学家也怕。你看不出来吗?他怕得要死,而且我觉得,他怕的还不是什么催眠之类的表象,是更深层次的。我都不愿细想那会是什么。回去以后,我一定要尽量说服井,让他从这档买卖收手。这不是我们可以碰的。”
我边听边想,也许我是无知者无畏,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泉体验过的幻觉尚未光顾我的大脑。“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吃喜梦?你之前明明在那方面吃过苦头。”
“其实我是在何琴走后开始吃的。我知道不能碰那东西,可我心里憋闷,一方面也是和井赌气。那是最开始,至于后来——”他顿一顿,“你知道,喜梦会让人看到从前。有几次,我看到了那个死老头。他也有不那么坏的时候。”
我过了一会儿才想起,他说的是把他卖掉的赌鬼父亲。
走到青旅门口的时候,泉和我们说再见,我说:“哦,对了,房钱——”
“我来付啦,”他露出早先那个万人迷的微笑,“反正就一间房。”
我知道他这话是说给秦拓听的,只能无奈地横他一眼。没想到他还没个够,亲热地附在我耳边说:“保重啊。”我正要推开这个故作亲昵的家伙,又听他说:“替我说声对不起。”
我呆在当场,他翩然转身。秦拓绅士风度地走开几步站着,我不知该恼谁。
其后,我带着秦拓拐进通往金花客栈的巷子。他探询地说:“你之前说要去一个地方。”
“先陪我见个人。”
“见谁?”
“我也不知道。”
说话间,我们进了客栈。院子里的遮阳伞下坐着个男人,正在用石桌上的茶具泡茶。他闻声转头,看见我们,似乎有些愕然,随即一笑:
“听说是大城市的记者,我本来还紧张呢,原来是老程家的姑娘。”
我讶异道:“你认识我爸?”我走过去在他的左手斜角落座。秦拓也在我的一侧坐了。
“哟,你小时候,我把你架在肩膀上到处耍,你不记得了?”男人叹了口气。他身上套件醒目的橙色T恤,外凸的啤酒肚像只长错了地方的硕大橘子。高原常见的黝黑脸膛坑洼斑驳,又像久经日晒的橘皮。
橘皮脸男人把两只斟了浓茶的茶杯放在我和秦拓跟前。“布朗山的生普,喝喝看。”
我没拿茶杯,盯着他看。这个自称认识我爸和我的人到底是谁啊?
他毫不避讳地迎着我的视线:“我姓耿,耿马的耿。八八年大地震的耿马。你有印象了吗?”
我摇头。
他的肥厚下巴一颤。“小姑娘贵人多忘事啊。不过我不是耿马人,是巍山人。你朋友不是云南人吧?那我有必要讲一下,巍山也有座古城,比大理古城古朴多了,好多人说那里是南诏故都,这是瞎传!南诏建都的城哪里留得到现在?大理段氏你们知道吧?金庸大侠写过的。早在元朝那会儿,段氏就在巍山建过土城,到了明朝,朱家皇帝在巍山开设蒙化卫,现在还能看到的巍山北城楼就是明代的,有六百多年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