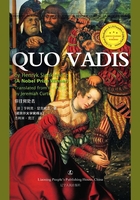海生去团县委上班之前,在西关村租了一个房子,将自己上学的两个儿子安排住了进去。一个是他的亲儿子仁国举,一个是当年知青高建敏的儿子罗大华。只说这大华,原本跟着二女在家上学,该说是因为遗传,不仅嗓音好,且一般的歌曲,只听一两遍便能准确地唱出来。他在家翻出了海生当年的一个笛子,没出一周,竟然吹出曲子来。惊得海生只得感叹着说: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也!一次海生回家,孩子直接了当地问他,我的妈妈呢?自从孩子懂事起,已知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曾被二杠接回去一段,由于二杠已有了新婚还生了儿子,其后娘和家人待娃便不热不冷,娃便跑了过来和海生的孩子同上学。接下来,学校老师,见了海生也多次赞叹孩子的音乐天赋。海生灵机一动,和二女商量,将其也带到县上上学,他的目的是,一来可以为孩子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来也可减轻二女的负担。他觉得二女在家又管孩子又干活实在是太辛苦了。眼下工作调动,又是进县委到大楼去办公,还是两个人一个宿舍,他只得在外边租一个房子。日每下班,立马回去给孩子做饭。说是做饭,其实早上是咸菜夹馍,中午一碗面条,下午稀饭。馍馍大多是二女做好从家里带,不足了买点,饭是海生做。他将在机关灶上的伙食费全省下来,给娃们买菜。尽管他想尽千方百计把生活办得好点,由于娃们不是这个买笔,就是那个买本子,加上学校的一些活动,他的工资除过保证孩子学习,保证老人的零花钱,到了生活上确实所剩无几。工作之余,他常因盖房而煎熬时,雅琦打电话让他上山去拉椽。
海生驱车赶到南牌乡时,上午十点已过,雅琦在大门口专门等他。他一下车,安排通讯员招呼司机喝水洗脸,便带着海生进了自己房。自从来南牌工作后,雅琦大都与干部在餐厅用饭,她可以和大伙又说又谝,包括谝那些又酸又黄的段子;即就是下乡,也经常草帽一摘屁股下一坐,在田头和老百姓一谝就是大半天,可她的闺房或者叫卧室,从不欢迎任何人进,即就是有干部敲开她的门说有事汇报,她也会将其堵在门外说:等会去办公室吧!随手便关了门,至于下班后或晚上,她的门便很少有人叫开。对海生她却领着他越过办公室,直直去了卧室。
她的举动让乡政府机关的许多人都投来猜疑而又惊又愕的目光。有人有意从窗下过,想偷偷看一眼。当他们的目光被早已严严地拉上的窗帘挡回时,那一双耳朵狠不得一下子伸进房里去。少说也过了一个小时,开饭的呼叫声,才将雅琦从房内叫了出来,看着她似要手舞足蹈的神态,轻盈的如水上漂的步子,红润鲜和,激情难忍的面容儿,大伙觉得似换了个人一般。她一出门,早已等候在一侧的通讯员立马迎上去问:何书记,饭端过来还是去餐厅吃,她却手一扬说:将司机管好,这儿就不用管了。说着话,亲自去厨房先打了饭,再打了菜,又拿了馒头,还特意在菜碟一侧夹了一圪瘩油泼辣子,于是分三次一次又一次兴致勃勃地端回房去。吃饭时,人们还意外的看见,她的儿子很快用完饭后,一直在院里玩。大约在下午两点多钟,她与海生一块从房内出来,肩并着肩在办公室叫上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司机,驱车出了门。
椽在槐花沟。槐花沟是南牌乡主要林区之一,在瓦苗山的一个沟岔里。正是槐花开放的季节,几里地之外便有一股淡雅却又略带甜味的清香迎面扑来,到了沟梁上向下一看,那绿浪中挂满的乳白色的花串儿,那满山架岭嗡嘤飞动的繁忙的蜜蜂,那山沟里在绿海与白花中已变了色的阳光和那似乎一眼能看到山背后的视觉和清新得让人觉出异样的舒坦和甜蜜的空气,使海生一下子便想起了欧阳修的: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句子。此时,已脱去外衣,上身只穿枣红色毛衣,露出长长的雪白的脖颈的雅琦和已在雅琦房中换上一件深蓝色毛料西服,白衬衫的海生,并肩站在山岔之中,如同泛舟在花海绿波之中一般。海生说:真想不到!雅琦说:是吗!世上想不到的事多哩,你以为这儿全是穷山恶水!海生说:谁说呢!雅琦说:我不在说嘛!海生你给远点看。雅琦手指远处。海生说:除过槐花,还是槐花呀!雅琦说:你再向远处看!海生便踮起脚尖远眺,却终没看到特别的什么,一双眼即看着雅琦,用目光说:啥也没有,你让我看啥呢!我知道你看不远!雅琦显然是戏弄了他之后满足而戏谑的口气。我看见了,我看见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了!海生显然已明白了她的意图。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不见得到这一步。雅琦说。洋槐花不是能蒸圪瘩嘛!海生有意岔开话题。哟!还能吃呀!我真不知道呢!雅琦故做惊讶地回话。我这一说不就知道了!海生与其绕舌。那还要看这儿管林的人让不让采呢!雅琦竟然卖起关子来。护林员竟管书记了!海生用话逗她。这倒是真的,如果一个人什么约束都没了,说不定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呢!雅琦说完看了海生一眼。其实,人人都想做管人的人,没有人愿去做被管的人!海生说。这就要看会管不会管,敢管不敢管!俩人就这般逗着嘴皮子。司机从驾驶室伸出头,重重的咳嗽了两声,才打住了他们的对话。
此时,从山梁上驶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到大车旁停住,从车箱上跳下七八个满脸灰尘的山民,被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带着,来到雅琦面前说:何书记,开始吧!雅琦转身与来人一一握手,那些从未握过女干部手的山民,在惊诧之中,个个都显得慌乱而又笨拙。雅琦向他们介绍了海生,说是在团县委工作,是她当年的同学。介绍中海生也与来人一一握了手。雅琦安排那位干部模样的人将她的的兜背过来,拿出一条金丝猴香烟让海生给每人发一盒(当时的金丝猴是比较高档的香烟),那些人虽都说不要,却是一个个伸手接着,急急地塞进衣兜里。椽是去冬伐好的刺槐,堆放在沟下边,须一根一根从那羊肠小道上扛上来。那些人在那位干部的吩咐下,一溜儿说说笑笑下沟去。司机也跟上下沟去了,说是去看看,沟梁上只剩下海生和雅琦。沿路的树稍上几只麻雀在叫,头上一只老鹰在盘旋。有山兔从枯叶中串出,一双贼溜溜的眼看着他们,又赤溜一声钻了进去。海生欲随司机一同下沟,雅琪一把挡住说:大可不必!海生收住脚,一双眼静静地看着雅琦;显然在用目光问,不去扛椽干啥呢?雅琦立即说:有没有雅兴在这山林里转转?海生说:客从主便!他有意将话说得轻佻,雅琦则伸手拧住他一只耳朵说:跟我走!海生便如同一个俘虏一般被牵着沿公路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沿公路走百余米,路另一侧是槐花沟的另一部分,同样是满沟的刺槐,满沟的花香。树丛中一条似路非路的小道,雅琦先钻了进去,海生跟在她的身后。浓浓的树叶似一把伞盖在头上,路是之字形,只拐一个弯,身后的公路使没了影。槐花香味似乎因了鼻子的适应已没了扑鼻的鲜劲,浓荫中树叶腐烂的霉湿味却一下子冲上头顶,霎时有了进入深山老林的感觉。其实,自从那次雅琦去家里看父亲,父亲专门找他谈话和日前父亲专门找到县上叫他回去顶砖之后,他心中全然明白,他和雅琦的事,父亲和家人是根本不会同意的。这一次雅琦叫他上山拉椽,于其说是为他盖房帮忙,不如说是催他尽快和二女办离婚手续。所在在出发之前,他心中反复地想,到底去还是不去!不去,自食其言不要说,等于向雅琦表示要断绝来往;去又觉得面对家庭的反对,特别是父亲的坚决反对,自己又束手无策,这不是在骗人吗?他反复地想,最后还是决定去。他心中已暗下决心,就是到了五十、六十岁,必须走和雅琦结合的路,他也就心中无愧地上了路。
俩人步到一个树间的稍平的空地,雅琦摘下草帽坐在山坡上,海生自觉地坐到她一侧。木料够了吧!雅琦问,雅琦知他已去秦岭山拉回了圆木,包括门窗木料,包括檩条,包括这次弄的椽。她有意问海生。椽是咋样算的?海生听出了她的言下之意,有意将话岔开。这个不用你管,全当我送你的,我问的是木料够了吗?雅琦逼上问。够了,绰绰有余!海生怯怯地回话。砖瓦也烧下了?雅琦接上问。烧下了!海生觉出她似在审罪犯一般。那还差啥呢?雅琦提高声音,话语全然变成质问的口气。不是——海生已不知了该如何回她的话。不是,啥不是!今日你给我说真话,你心里是咋想的?雅琦显然已委屈得似要落下泪来。不是把椽还没拉回去嘛!海生终于找到了辩解的借口。那你为啥没催我要椽,为啥从来就没给我谈过你盖房子的设想,安排。你把我当什么了!你说,这是为啥?说话期间雅琦的泪水从眼角滚出来,也不去擦,一张泪脸,满含愤怒死死地盯着海生。对不起,我确实经济很紧张,我这不是在一步一步实施嘛!海生从侧面向她表态。海生,我也不是七岁十岁了,你这不是在睁着眼睛说慌嘛!你应该清楚经济困难和人的态度完全是两码事,有了好的态度,没有经济,可以想办法,可以转化;没有好的态度,没有主动的精神,就是有钱放着,也不顶用呀!雅琦越说越严肃,越说越激动。听你之言,我已成了意识问题了!雅琦呀!苍天在上,槐树作证,我可以向你发誓,我的一切都朝着我向你的承诺而努力,我五十多元的工资,我管着三个孩子,我还有老人,我还要搞建设,你知道我有多难呀!雅琦刚才之言,显然激怒了海生。他只得以誓愿表白自己的心迹。
不必,大可不必,这种话我不是没听过,我要看事实,我要看进度,我只要你今日明确地告诉我,盖房你啥时动工?雅琦逼着问,显然她早已做好准备。你以为有了砖瓦,有了木料,有了椽,这房就能动工了,圆木要不要干一干,门要不要木工来做,还有白灰,沙子,水泥,动工还要吃粮食,还有匠人的工钱,这一切都需要钱下场。可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唉,不说了,不说了,你说是态度问题就是态度问题!海生表现出的委屈比雅琦更大。我只想这啥都有了,还这么复杂的!雅琦已觉出自己出言过分,口气软了下来。对不起,我不否认我有态度问题,我的祖上在过日子上给我留下的就是有多大的肚子吃多大个馍!人得靠自己的力量过日子。要我做啥事都大刀阔斧,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海生话说得很慢,却说一句想一下,再说。你别再往下说了,其实,事情如何发展,我心里很清楚。咱们相处了二十年了,谁还不知谁的啥呢!可是我不由我,不由我呀!刚才说您的话,您全当没听见,我也全当没说,您大可不必为难,人这一辈子,谁让我的心眼就这般的死呀!说到此雅琦不只成了个泪人儿,她的周身似乎要僵了,她的眼神似乎已呆了,她的脚手似乎已麻木得不知了放在那儿好,她一身子倒在山坡上,她的四肢摊放开来。她已经到了欲哭无泪的境地。
海生偎上去伸出臂,欲伸到她的头下边,将她搂抱起来,她却生硬地将他的手臂豁到一边去。他只痴痴地坐在她身边看着她如痴如呆地躺着。我这算干了一场啥事哟!雅琦心中只说这一句话,越想越悲,泪水终又如泉般涌出来。我该咋办嘛?海生心中却只说这一句话。想着想着,便在心中发誓般说:我这房不盖了,我一回去就和二女离婚;可这一句话刚刚闪现,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娃咋办呢?二女咋办呢?世人咋看呢?还有父亲让他顶砖的前前后后,至于莘子,他更不敢去面对她。还有,若还一下子将此事公开,机关的人会怎么看,不说别人,团县委的书记肯定会说:我怎么搞的,咋调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色胆包天的男人,一个作风如此败坏之人,到了县委的机关。想到此他便不敢想了。何书记——!路上的呼叫声清清楚楚地传来,雅琦一身子坐起,海生欲张口回话,被雅琦抬手止住,海生明白了她的意思,俩人同时站起身来,相互检掉身上的树叶,反复拭去脸上的泪痕,并用长长的呼吸反复调节着情绪,然后慢慢地向上爬。
当俩人都站身公路上时,雅琦才有意将声音提得高高的,没话找话地说着话。那位干部模样的人终于随声音找过来。恭恭敬敬地对她说:何书记,车装好了!雅琦回话说:嗬,这么快,我这同学要到那边去看一看咱们槐花沟,这条沟转了还不到一半,就听见你在叫,好好好,谢谢!雅琦的话语与刚才全然成了俩个人,她的随机应变,她的热情,她的气魄,让海生开始怀疑,她是不是雅琦。海生急忙上前向那人敬上烟,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三人一同来到车前。拉椽的大车没再去乡上。雅琦与那一伙山民坐上手扶拖拉机和他挥手再见。看着她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一双恋恋不舍的满含泪水的无奈的目光,海生心碎了。他从驾驶室伸出半个身子,挥手示意她先走;她却站身手扶机车箱上,指挥他上路,如此反复几次,还是海生先发动了车。走出去老远了,从车头一侧的镜里,他看见一位上身只穿枣红毛衣的雅琦不时向他挥手,她那毛衣倏然似化成一团火一般在他心内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