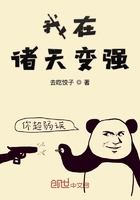第十八章出事
我敢说,这是我在这个秋季,不或者是在整个漫长的人生中听到和见到最美的故事,不仅仅是他们的故事打动着我,还有人本身就已经打动了我,让我无地自容,我紧扣十指,坐在火炉旁,父亲看着我,我时而看看他和母亲,因为又要着离别。母亲声音颤抖道:“你要走就走!”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是呆呆的坐着,父亲也附和道:“你的路,必须你自己走,我们替你走不来!”
母亲替我收拾着行李,眼圈红肿,我知道她有哭了,我心如刀绞,真不该让他们为我流泪,我最怕流泪,特别是在父母面前,一来是怕他们看见,二来是怕自己犹豫不决。
我登上了回深圳的路,前一段还是那位师傅,我们已经熟稔,一路酣畅淋漓的畅谈,使得我们成了挚友,他说她的妻子最喜欢《夜行人》这本小说,但他意外的,竟然不知的是作者就在他的身边,这也是多年后让他们惊讶和格外高兴的一件事。
他还是那么专注的开着汽车,我知道这是他和她的寄托,也是他和她的约定,这种约定是灵魂的交织和触碰,让人无法直视,让人不忍心去触碰。离开是深秋了,但广州的秋天还是那样暖和,让人觉得舒畅倘然,曾可儿去了圣西宾利亚大学,空落落的房子,安静的让人不敢呼吸,放好行李,直奔苏荷酒吧,那里永远是那么的富丽堂皇,雍容奢华,热闹非凡。
“嘿,你好!好久不见!”我向小彤打着招呼。她满脸的惊讶,说不出一个字,我说:“来一杯哥顿金酒”。她才换回一副极具专业的笑容加上熟稔的调酒动作,看起来倒是别有一番韵味,这倒是出乎我意料的事。她把就递给我,笑道:“好久没有看到你来过这里!”我轻嘬着酒,听她说起这酒吧里上演的所有故事。似乎她就是主角一般,讲得生动极了,我想她是一个及会讲故事的人,这样的人是可爱的,惹人喜欢的,这也是我的镇痛,就是不会讲故事,记得在上学那会儿,同学每个人要讲故事,一轮到我,就卡壳了,惹了许多不愉快,也使得我愈来愈喜欢独自去看故事,我恨极了它们,但又及其喜欢,就像你明知道有些事是不该知道,但你还是想破头脑也想知道,这也忒让我腻烦。
我们聊了很久,相互作别,我作别除了酒吧,出到酒吧。
已经是夜幕渐沉,华灯初上,夜幕如同鬼魅,霓虹灯照耀下,更显的妖媚极了,迷茫感顿生,人来人往,而我形同陌路,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落在这座城市,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哪里才能让我心安理得。
“你好!”甜美的声音,让人觉得眩晕。
“你好,请问你是?”我尽量让自己镇定,不显示出任何的紧张。“您是莫先生吗?”声音不缓不急,声音柔美。我说:“是!”原来是出版社,我约的第二本书的出版社,明天是定稿出版日,要开发布会。我急匆匆赶回家,准备妥当一切,出发到深圳,这是我此刻的想法,唯一的想法。
灯影涣散,点点斑斑是灯光透过树叶的眼睛,煞是美丽,火车站人很少,寥寥数人,买好票,进了站台,一刻钟时间列车即将开启,我用手摸摸自己的脸,这是习惯性动作。倦怠的身子只是随着脚步移动,心疲惫到了极点,车厢里,人很少,我选了一处没有人的位置,安静地坐下,静待火车轮子压扎着铁轨的哐当声响起,心就慢慢平静下来,看着坐蔸里准备的杂志,笔直的模特赫然在扉页,整整一个版面,我是及其讨厌这种杂志,你不知道他究竟是让你在吸收怎样的东西,我发誓,那些冠冕堂皇的语言恶心死我了,放回杂志。索性拉起衣领,饱饱睡一觉,这是我认为此时此刻唯一一件值得做得事。
潜意识里,火车听过三次,有稀稀落落的人上下,人少的可怜,就近有一对恋人,交头接耳,亲热极了,像是蜜糖一般,粘在一起,也不在乎车上其他人的目光。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发情的老虎也是温柔的,失掉往日的凶残”我想不能这样看待他们,他们就像一对鸟,相互啄着对方的脖颈的羽毛,不时发出格格笑声,像是在逗乐,也像是在调情。
眼睛疲惫的似睡非睡,渐渐笑声与一切消散在脑海远处,没有丝毫的声响,只记得一个人,一个宽大的手,敲打着我的肩膀,我眯谢着眼,想看看是谁,列车员满脸笑意道:“先生,终点站到了!”我满脸歉意,起身拿起行李,与那列车员道别。深圳的深秋,凉意顿生,我一直不明白,只是一市之隔的广州和深圳竟有如此大的差别。紧一紧衣服,接待处,有写着我名字的牌子,是个女孩,身材修长,白皙的皮肤,披肩的头发,一双黑旺旺的大眼睛,眼睛下稍微坚挺的鼻子,显得恰到好处,嘴唇似动非动,我站在她面前,看着她,她及其惊讶的道:“你就是莫辰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我笑道。
她略显尴尬,随即道:“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以为莫先生年龄稍大?”说这话时,她脸微微红,“不想先生却是这般年轻”。
签售仪式在深圳书城进行,当天来的人很多,大多是书的粉丝,我从来不说粉丝,但在这里我必须这样说,应他们的要求,我想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呕心沥血,我的作者都是人生的鉴别师,他们有时候比我高明多了,我常常为他们的疑问感到高兴。
《次元爱情》,在不同的次元里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相互弥补,带着这样的宗旨和价值,每一次元的人都需要自己的次元空间,每一种次元的相遇都是次元世界的一段缘来缘往。我想大多数读者喜欢这本书不是喜欢我本人,或者这本书,他们是沉迷在他们自己的次元世界里,活在自己的次元世界里。
我延着书城,避过人群,邀了朋友驾车去巽寮湾,他们从不爽约,沙滩与海水相互亲吻,我约了船家,说是出海,他们劝我不要出海,我极力为之,万里晴空,蔚蓝天空,船家将船租给我,我独自驾着船,向海的远处飘去,远处有巡逻的海警,他们驾着快艇,所过之处一条长长的白链,拖着长长尾巴,向远方荡漾。
激荡的海水如同汹涌的海兽倒弄着船只,只觉穿着东晃西摇,眩晕的感觉一拥而上,接着是海面一阵波涛汹涌,来势凶猛,我掌舵回旋,但来不及,只觉船身飘摇不定,我也随着飘摇,心中不免丝丝恐惧。我模糊看到有白练一样的东西在靠近我的船,我只觉全身冰冷,下药挣扎,但无济于事,我半睁着眼,紧闭着嘴,昏迷不醒。
我醒来的时,周围站满了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最后走来护士,我才知道我身处何处!我强撑着身子,酸疼的肌肉,从脊梁骨冒出,脑袋一阵眩晕。我强行出了院,我告诉他们我健硕的体魄这点打击还是能够应付。拖着疲惫的身躯,迎着阳光,沐浴着阳光,心情豁然开朗。
母亲来电话,焦急的声音出卖了她此时的境况,心中满是自责,我告诉母亲,我没事,不用为我担心,她一再嘱咐我,要注意安全,这样的事不要在发生。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鲁莽给我的母亲,我的家人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我却是心安理得,这样的罪孽我怎么能够犯下呢?心中暗暗责备自己的冲动和图自己的喜好!
其实这次出事让我明白许多问题,我开始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倘若我死了,最悲伤的就是我的父母,那是我便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罪孽深重的人,我明白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牵动着他们的心。回到广州,收到曾可儿的来信,说她在大学种种事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她要一直走下去。最后提到我出事,字里行间透着酸楚了无尽的关怀,她告诉我,让我出国走走,或许能够缓减这种生活。
我抽出一支烟,在黑暗燃烧灼,嘶嘶声想起,整个房间顿时烟雾缭绕,我身处其中,一动不动,静默代替了一切,只有忽明忽暗的眼点缀着漆黑的屋子。脑海中浮现着一幕幕景象,那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我想,我应该知道要去哪里,我记得季羡林先生的自传里的德国,那是我向往的地方,我要到那里去。蜿蜒的多瑙河,富饶的土地,严谨的民族,这些都是我向往的。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踏上了去往德国的路,离开了中国,这个国度让我千言万语都无法来描摹,她是如此的美丽,又是如此的让人感到伤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