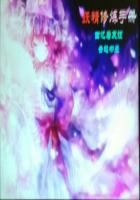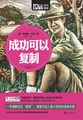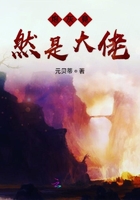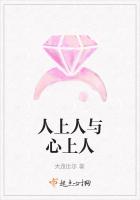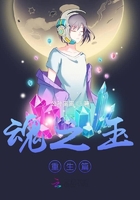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决定了五四小说在情感表现上的特殊性,即这些作品中的所谓主观情感,其实并非是对人物整个复杂心灵世界的揭示,而是带着强烈情绪色彩的人生观、宇宙观的抒发,是他们对现实态度的表露。他们不是以揭示人物内心各种复杂隐秘为创作上的,而大多是片断式的议论和感叹。这种抒情事实上包含肴更多的理性因素甚至说教意味。大段大段的议论,打断了叙事文学应有的情节事件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但它同时又避免了叙事文学可能出现的弊病:个人琐碎情感的喋喋不休的发泄,把艺术的价值推向纯粹个人化的俩死境地。这种关注现实,思考阔家、民族命运的精神,将他们那些纷乱的情感因素统·起来,使他们的小说尽管形象模糊,结构散乱,却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气息。历史地分析和评价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在今大看来程度不同地缺乏艺术件的议论,对于五四时代的读者,有着我们甚至难以想象到的感染力,它们可以说是真诚的“说教”,充满激情的单调。
五四小说作者在表现个人、抒发主观情感中透露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表现了他们作为自己时代的讴歌者的真诚态度。这对我们今天处于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的作家,在调解和处理创作个性的发挥与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之间的关系时,不是一个重要的、发人深思的启示吗?我以为,研究五四小说创作的得失,探讨作家对这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的优劣,比那种纠缠于理论主张与创作方法的归属,在所谓积极与消极之间寻找最佳比例的无休止的争论,或许更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五四小说:超越流派的艺术创新
五四小说以主观情感为主要表现对象,并努力通过个人透视社会和时代精神的创作倾向,使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方法及艺术风格呈现出复杂多样、革故鼎新的面貌。
关于五四小说的创作方法,评论界一致认定:以“为人生”为创作上的的文学研究会,辑于现实主义;以“为艺术而艺术”为主张的创造社,则属浪漫主义。从理论术语出发到作品中寻找相应的例证,往往产生片面化、简单化的弊病。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人物茅盾一再声称,文学研究会的成、不是因为有了一致的文学理论要宣扬鼓吹”,“这个集团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就各成员来讲,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热衷与偏爱,似乎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里明确说明,他们“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偏袒”。即使在理论阐述上,也并未见得多么坚决,同在这篇“宣言”中申明写实主义文学最近已近衰竭之象,就世界观之立点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上之,则写实主义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尝有一二,故闻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主义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人,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可见他们是持着进化论的观点看待文学,把现实主义当做其中一个必要阶段而提倡这一创作方法的。
在文学研究会作家当中,很少有人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谈论文学,他们大多是从人生观、社会观出发,探讨文学的社会作用及其功能。他们只是在“为人生”这一口号下相一致,至于如何表现人生,却并不求统一,在创作实践上,他们的确自始至终坚持写实的原则,但“写实”二字的含意却是很笼统的、很模糊的。在大多数作者那里,都经历了从“问题小说”到“探索”人生是什么的过程。这一转折,使“写实”的含义,由写所见、所闻到写所感、所想;由对生活现象的写真到抒发主观情感之真。冰心小说越来越浓的烦闷气氛,庐隐小说自诉式的心灵独白,叶圣陶对心灵寂寞的描绘和对母爱的赞美,王统照小说的神秘氛围和许地山作品中的异域风光与宗教色彩,都使他们的小说带上了浓郁的浪漫去:义色彩。当然,考察这些作者的创作动机,我们并不能充分证明这一变化在作家创作追求中的自觉性,他们的确始终坚持写实的原则。如果我们承认“问题小说”尽管很不成熟,但毕竟不失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的话,那么,探索“人生是什么?”的小说则是在这一道路上的继续追求。他们不满足囿于生活之一隅做表面描写,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引起更加广泛的共鸣,所以才从描写客观的外部生活,转向了对个人内心情感世界的挖掘。结果倒是这样: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反增加了浪漫主义色彩。这种近乎奇特的现象,正是动荡时代在他们灵魂深处激荡的结果,是他们在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应有的艺术素养的情形下,对社会、人生及其前景努力做出表示的结果。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渴望、焦灼和苦闷,他们还不能够也不屑于用委婉的笔致,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甚至运用象征手法将这些情愫渗透、暗示其中,而只怀着一种“真”的态度从事创作。这一“真”字的内涵,已由开始时的对生活的写真,增添了更多抒发内心的情感的真,使其含义变成了真诚、真切、真率、真挚。重要的是,作者自己并不以为这样做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相违背。情感之“真”被他们视为文学灵魂,也成了他们小说的生命和骨髄。
创造社历来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文学团体,人们往往把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口号对立起来。笔者认为,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作社作家的小说创作不能笼而统之地称其为浪漫主义流派,这其中有着较大的复杂性。
郁达夫“艺术品都是作家自叙传”一语,成为人们认定他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倾向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因为“自叙传”就意味宥表现自我,表规自我就等于浪漫主义,俏在郁达夫本人那里,“自叙传”说却另有解释。他曾明确说过:“艺术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一句话,致惹起了许多误解,想在这里辨一一辨证。我在那里所说的意思,是说作家要重经验。没有经验,而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除非是有大天才的作家,才能做得成功,想在作品电表现出一点力最来,总要离不开实地的经验,不违背Realism的原则才可以。这是我的真义,这我想也是谁也应该承认的一个原则。不难看出,郁达夫的解释不怛没有浪漫主义的味道,反倒将其“自叙传”的主张联系于现实主义(Realism)。他的所谓自叙,是为了使作品表现的内容更加真实,避免向壁虚造。
当然,考察郁达夫小说,我们认为,浪漫电义依旧是他小说中最主要的创作方法。这是因为,郁达夫所强调的经验,是指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他同时强调诗的实质,全在情感”,“小说的表现,重在情感。”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地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他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重写感情,力求在创作中酿造出一种气氛和情调,成为他创作的至高要求和目的。这种倾向也是创造社其他作者的共同见解。郭沫若、成仿吾等对创作的认识与理解与郁达夫基本相同。
在这些作者的作品中,形成了以情感世界表现为主,又不乏生活细节描写的特征。情感流动是其小说的情节主线,人物行动等生活细节是为表达情感出现的副线,由此形成他们创作方法上以浪漫主义为主、以现实主义为辅的特色。浪漫主义是其精神,现实主义在更多情形下是技巧。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他们的创作中是纯属被动的,它之所以能够与浪漫主义共存,根本上在于这些作者在情感倾向上,总是选择人物内心当中由对社会人生的关切引起的感触、对现实社会的态度等方面的内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较之冰心等文研会作家,创造社的作家很少描写现实生活以外的理想世界,在人物命运的结局处理上,也从不带上虚幻的灵光圈或给予宗教式的超脱。他们笔下的人物无论多么痛苦,也不曾将思想引向超出现世的极乐世界。冰心笔下的人物,大都借母爱与童真从死的欲念中挣脱;叶圣陶《阿凤》中的童养媳阿凤,孤独寂寞中,在动物身上找到了慰藉伊不但忘了诅咒,手箅和劳苦,伊连自己都忘了。世界的梢魂若是‘爱’、‘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许地山《命命鸟》中的男女主人公,因失恋而轻生,但他们却为此感到快乐。郁达夫小说中也写到了死,但《沉沦》中的“他”临死时喊出的足切盼祖国兴盛、强大的口号,较之文研会作家的“美”和“爱”埋想,哽加族撼人心。即使同样表现对“爱”的向往和追求,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赞美肴锌遍的人类之爱,而郁达夫、郭沫若等则赤棵裸地扪露出自己对异性爱情的渴望及求之不得的痛苦。
由此可见,人多数作者的创作中,都不是严格地遵循、间守着某一创作方法,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上时并存的。显然,他们往往还不能把者完美地融合于一体,而多呈现为一种杂糅相间的现象,在部分作者的作品当中,还兼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这一事实证明:五四时期,大多数作者的创作并未表现出对某一创作方法的自觉追求。他们是“本着自己的内心要求”从事创作的,他们真正注重的是寻找抒发自己内心感受的表现方式。他们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不是出于对时髦形式的崇拜和模仿,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产生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他们并不痛苦地抛弃了这种情调,向扎实、凝重的现实主义发展。在文研会作者那里,浪漫主义的色彩是伴随着他们曾经信奉的空虚理想的幻灭而消退的。正如王统照所说:“虽然并没有几年间隔,而对人生痛苦的尖刺愈来愈觉得锋利,对解决社会困难的希求也愈来愈迫切”,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从理想中祈求慰安”了他从(湖畔儿语》开始,不再描写那种虚幻不实的理想,对现实人生苦难的写真取代了带有神秘色彩的“写意”氛围。冰心也从五四后期开始逐渐减少直至抛弃了对人生哲学的玄想和母爱理想的赞美。
创作于1931年的《分》标志着她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成熟。叶绍钧的“母爱”题材从《潘先生在难中》(1925年)以后不再出现。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预示着他小说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比重的转化。
创作方法上的这种转变,是作家的描写领域和表现对象由主观到客观,由个人情感到现实生活转变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从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转变在文学领域引起的必然影响。五四小说的经验证明:“浪漫主义不是一种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的严整的理论,它也不是一种创作理论”,“浪漫主义乃是一种情绪,它其实是复杂地而且始终多少模糊地反映出笼罩着过渡时代社会的一切感觉和情绪的色彩”。文学史的发展同时证明,现实主义是小说创作中最优越、最长久的创作方法。五四小说家不是从文学教科书而是从自己创作实践的曲折历程中得出这一结论的。
题材和内容的更新,必然导致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变革,艺术技巧的选择和运用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素材的评价方式和处理方式。由于五四小说内容上的主情倾向,致使这一时期小说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也有着区别于其他时期小说的共同的“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是一个新与旧相冲突、抗衡的变革时代,它的首要任务是摧毁一切旧的樊篱,破除传统的规范,强调和讴歌行为和思想的自由。不是也不可能立刻推出并就范于某一种新的规范。表现在这时期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上,他们努力破除旧文学的僵硬格式的束缚,要求创作上的绝对自由,因此,他们常常表现出轻视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倾向。最典型的如郁达夫在谈及自己创作《沉沦》时所说:“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情感上是一点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觉得只能照那么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传统小说艺术的比较中,探寻五四小说技巧运用的特点及其贡献。
首先,出上达情感的需要,作品的叙事角度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小说受说朽艺术的影响,以故事情节的叙述为主要表现形式,作者纯然置身物外,以全知全能视角表现对象。五四时期,则大量出现以“我”为叙事角度的小说,这种叙事人同时也是作品主人公的“独特的无名性,使得这些作品在表现主观情感上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和直接性。鲁迅的《狂人日记》、《一件小事》、《故乡》、《祝福》、《孤独者》等,都是以“我”为叙述视角展开情节的:》叶绍钧的(隔膜》、《晓行》、《苦菜》,郭沫若的《牧羊哀话》等,都以“我”为中心,郁达夫小说中那些“他”、“伊”、“质夫”、“文朴”,其实本质上是带着作者自我影子的“我”。作者把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绪全部寄托到人物身上去了。
与作品叙述角度变化相伴随的,是小说体裁的革新和灵活多样,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出现。这些体式为作者自由地抒发情感提供了便利条件。1918年鲁迅写下了上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庐隐的《丽人的日记》、冰心的《疯人上记》、淦女士的《卷葹》等,都采用了日记体和书信体形式。有些作品则在情节叙述过程中夹带大量书信,借以直抒情怀,冰心和庐隐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还有一些作品,则采用人物心灵独白的方式,郁达夫的(茑萝行》、鲁迅的《伤逝》均以主人公对自我灵魂的解剖为叙述主线,使作品情感更加真切感人。
五四小说这种以“我”为中心,以主观情感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特征,决定了这些作品在悄节的组织、安排,也即结构方式上的特殊性。可以说,除鲁迅、叶圣陶等少数作者外,大多数五四小说作者都不很重视作品的结构。郭沫若、郁达夫、庐隐、王以仁等的作品,程度不同地暴露出缺乏必要的组织和节制的缺憾。作品情节从何汗始,到何处终止,都没有必要的交待。这自然与他们肖身思想认识的混乱、繁杂相关,同时也是要求创作自由的结果,因此,明缺乏控制的五四小说的结构,同时也可说是一种开放式的结构。虽然显得“开”有余而“收”不足,但对于传统小说以偶然冲突始,以“大闭圆”为终的呆板模式,无疑具有重大的突破作用。以人物的“情绪史”为小说的结构主线,注重人物内心某一方面的情绪活动的揭示,使这些作品尽管显得支离破碎甚或散乱庞杂,却依然托出一种特有的氛闱和意境。也许正是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特殊表现方式,使这一时朗的小说常常与散文接近甚至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