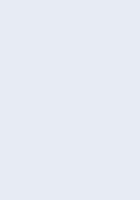吸大烟的人来了瘾,
时而热,时而冷,
鼻涕流,泪纷纷,浑身骨头疼。
父母恨,兄弟分,
卖女儿,青年亡,脚头妻子跟别人。
--顺口溜
林田数马匆忙离开酒桌回到宪兵队,是接到报告,逮到一个胡子,水野大尉亲手逮到的,宪兵队长特别重视,才从白罂粟烟馆庆典酒桌上离开,他听宪兵这样说:“他可能是天狗的人。”
天狗,林田数马像抽足大烟一样兴奋,急忙带翻译徐梦人回来。
“招了没有?”林田数马问。
“臭糜子!”水野大尉恨骂道,“只说自己是种地的,可是他骗不了我。”
特高课工作多年的水野大尉,在他面前蒙混过关难,胡子横行子就没在他面前走掉。
亮子里的几家布店情况摸清,容易得手的两家敞门脸布店规模小,所存的货不多,即使得手,也不够做两百套衣服。
“去永庆号绸缎庄。”徐秀云说。
永庆号绸缎庄店铺恢宏,光摆在柜台上的布匹足够弟兄们做衣裳。问题是店铺离警察局太近,很难得手。
“看起来,直接劫店不成。”徐秀云对横行子说,“我们回山,琢磨半路设伏打劫绸缎庄的进货车,把握大一些。”
“什么时候走?”
“明天头晌(上午)。”徐秀云说。
动身之前的头天下午,徐秀云买回一捆黄裱纸,说:“淑慧姐,我给德龙上坟。”
“我跟你去。”丁淑慧说。
“我俩一起去。”
丁淑慧用铁印子打印纸钱儿,恋恋不舍地说:“怎么说走就走,再呆几天。”
“这一气出来工夫不短,七八天啦。”徐秀云理由道,“家也不能老扔着,该回啦。”
“要走走吧,告诉大哥一声没?”丁淑慧问。
“他近日心情不好,没对他说。”
“唉,心情能好吗?”丁淑慧打印完纸钱儿,开始折叠,“梦人当了宪兵队的翻译官。”
“呃?”
“三哥跟小鬼子打仗死的,小闯子偏偏为小鬼子干事,你说说这是什么事啊?”丁淑慧说。她不清楚徐德成诈死这件事,徐家没几个人知晓实情,“报应吗?”
“哪有什么报应,好人没长寿,坏人活不够。”徐秀云感触地说,她的亲人一个一个地死去,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现在已经分不清,分清了又有什么意义。
“也给你家叔婶送点钱(烧纸)。”丁淑慧说。
“到哪儿烧去呀,他们连个坟骨(坟头)都没留下。”徐秀云凄然道。赌徒父亲徐大肚子死后警察收的尸,按无主处理,不知胡乱埋在哪里,母亲上吊自杀是父亲埋的,没对她说。
“在十字路口送钱,他们能收到。”丁淑慧迷信道。
徐家祖坟地葬着几辈人,徐德龙坟前的碑最大,上面刻满文字,徐德富亲自撰的碑文,将一个赌徒的生死记述之。
“德龙,我和淑慧姐来看你。”徐秀云边烧纸边叨咕道。
丁淑慧各给老辈的坟墓烧些纸,在徐德成的坟前,她说:“三哥你也别怪罪小闯子,人总得找点事做呀……
纸钱在徐秀云的手滞了,听清了丁淑慧说什么,宪兵队当翻译不一定就和日本鬼子一条心,做好事做坏事,要看尾后。
徐秀云同横行子出城门很顺利,伪满军没怎么细盘查他们,骑在毛驴上的徐秀云怎么看也是走亲戚的小媳妇。
“横行子,前边草深你站一下,摆柳(小便)。”徐秀云说。
横行子四处望望,通向白狼山的路上没人,他们已经来到山脚下,再往前走算进山了。
吁!横行子拉住驴,说:“在这儿吧!”
徐秀云下驴钻入路旁林子,茂密的树毛子(灌木枝)掩盖了她,横行子牵驴往前走几步,在前边路旁等她。
哒哒的马蹄声在身后响起,只见几个日军骑马过来,横行子把驴拉到路边让开道眼,让他们过去。
水野大尉带宪兵进山去,他探知天狗绺子藏在白狼山,可是偌大的白狼山,们具体藏在哪里啊?几个日军从横行子身边走过去,有一匹马鼻子喷出的热气落在他的脖子上。
本来日军已经走过去,出人意料的毛驴犯浑,挣脱掉缰绳,嘎嘎地叫着追赶日军,横行子愣怔在哪儿。
“巴嘎!”骑青骒(雌)马的宪兵举枪对着毛驴开了一枪,毛驴倒地毙命。
“我的毛驴!”横行子禁不住大喊一声。
事情就怕凑巧,宪兵骑的青骒马刚从农民手里夺来的,它正发情,毛驴追它遭枪的;横行子见驴倒地,忍不住大喊一声,这一声喊带出老奤味儿,因此暴露。
“他的不是本地人。”水野大尉说,“抓住他!”
日军骑马回身过来,横行子跑已来不及,跑等于对宪兵说我心里有鬼。水野大尉跳下马,同几个端枪的宪兵走近他。
“你的什么干活?”水野大尉问。
“太君,我地里的干活。”横行子尽量装出不惊不慌,“种地!”
水野大尉伸手摘下横行子的帽子,摸了摸,大笑道:“前奔儿娄后勺子,你不是东北人,带走!”
“太君,我是本分庄稼人……”
“带回队部!”水野大尉命令道。
俗语:南勺子,北邦子。本来老奤算不得南方人,行子也没勺子,水野大尉偏这么说,总之要抓人。
仅凭说话的口音确定此人是胡子,林田数马不信,他说:“怎么断定他是胡子,还与天狗扯上。”
“队长,开始我见他双腿站立姿势呈马步,怀疑他是胡子。”水野大尉得意道,“天助我们啊!我带回来的路上,遇到警察局的王科长,他见过此人。”
“嗯?”一个警察科长怎么会见过胡子,又确定是天狗绺子的人。
“天狗绺子假投降期间,改编后的特混骑兵队在本镇,王科长见过他。”水野大尉说。
“确定无疑?”
“是。”
“幺西!看好他。”林田数马说。
“二哥,我听你安排。”徐德成终于吐口道。
两天两夜的说劝,结果令徐德中欣慰,三弟同意接受改编,天狗绺子到此寿终正寝,即不是易帜,也不是改号,徐德中说:
“你们全称三江抗日游击队。”
“四梁八柱的职务咋安排?”
“按新编的队伍设置,下辖两个中队”,徐德中按事先抗联的计划安排,“每个中队下设两个小队,两级队长由你原来的四梁八柱担任。”
“我是队长,二当家的副队长……”徐德成按绺子原先座次分配了职务,“二哥,你说抗联派人来,给他一个什么官儿?”
“来的人是党代表。”
党代表的官有多大徐德成不清楚,问:“职务比不比我大?”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准确,徐德中明白三弟心想什么,他要这支队伍的领导权力,他迟疑不决恰恰是这个权力问题,为使他向前走一步,必须退一步,他说:“你是队长你说了算,遇大事尽量与党代表商量。”
“这还差不离,要是这样,叫党代表来吧。”徐德成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回去向组织汇报,派谁来定下来通知你,到时候你们接党代表上山。”徐德中说,这个话题只能谈这么多,组织决定人选后,直白地说到这只队伍上后,有大量的艰难工作需要做。
“改编后队伍拉走?”徐德成问。
徐德中告诉他留在白狼山,山高林密适于打游击,与三江的日伪势力作长期斗争。
“近期我们干什么?”徐德成跃跃欲试道。
“等待上级组织的命令。”徐德中说目前练兵,游击队今后有的是仗打,“取消你们去亮子里的打劫计划。”
“秀云还没回来……不下山,弟兄们换季的叶子?”徐德成顺口溜出胡子黑话道。
“三弟,你现在是游击队长,不要张口闭口土匪黑话。”徐德中批评道,“叫你的部下,以后不要说黑话。”
“嗯哪!”徐德成接受批评,说,“不下山弄衣服,夏天就得当冬天过。”
徐德中答应他回去向上级组织汇报,帮助他们解决换季的单衣服,近期就解决。
“德成”,队伍的事谈到此,徐德中说,“大哥很惦念你,叫我带话给你,呆在山里别动,怕你遭宪兵祸害。”
“大哥为了这个家操劳啊!我们这辈人不算,还有四凤、梦人。”徐德成的疤瘌脸看不到表情,但声音喑哑,“大哥他好吧?”
“身体可以,心里憋屈。”
“药店……”
“日本鬼子逼他种大烟,他极不情愿。”徐德中介绍长兄近况道,“四百垧祖田是他的命根子啊!”
“不种不行?”
“咱家的祖田在无人区内,撂荒几年,种大烟宪兵队作为条件,不同意,地就让开拓团来种。”徐德中说,“大哥咋舍得呀!三江县内种一千垧大烟,你不种,还有人种。”
“小鬼子种那些大烟干什么?”
“还不是祸害咱中国人。”徐德中对三弟讲了日本鬼子的阴谋,最后说,“迹象表三江可能成为东北鸦片的集散地。”
“二哥是说小鬼子把大烟运到三江加工、储藏,再运到各地去。”
“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不能叫他们消停整,铲平大烟地。”徐德成说。
罂粟种遍东北,铲平得了?徐德中心中有想法,与日本鬼子开展一场大烟战,具体计划要回密营制定,将来要靠三弟这支队伍。
“四凤咋样?”徐德成知道陶奎元已死,他经常想起苦命的女儿。
“她搬回家里去住了……”徐德中告诉他四凤开一家烟馆。
“啥,烟馆?”徐德成惊愕道。
“这有什么不妥?”
“大烟馆是干啥的,卖大烟啊,坑人嘛!”徐德成埋怨道,“这孩子怎么想的。”
徐德中说四凤想得没错。
“二哥你没挡她?”
“挡,支持还支持不过来呢!”
“二哥你……”
“听我说三弟”,徐德中讲了当下种烟禁烟的形势,四凤不开,还有人开,“官办烟馆,又不是她见利忘义……”
徐德成平静下来,自嘲道:“咱家有种大烟的,还有卖大烟的,只差有人抽大烟,成一条龙啦。”
“你只说了一半,还有毁的。”徐德中意味长地说。
“毁?”徐德成茫然道。
“毁!”徐德中说得肯定。
徐德成吧嗒(品味)二哥的话,幡然道:“哦,是这码事。”
往下说徐梦人,徐德成说:“他跟着大板儿过,两口子为他操了不少心。”
说四凤和说徐梦人,徐德中从夏天陡然掉到冬,目光冷峻起来,他说:“梦人交了个日本女朋友。”
“啊!日本鬼子女朋友?”徐德成惊诧道。
“满铁副会长三牧政雄的独生女儿,叫茶花贞子。”徐德中说。
“贞子,啥子都够呛,日本鬼子的后代还有好玩意儿啊!二哥,你又支持?”徐德成气囊囊地责问。
“错啦,没挡住。”徐德中觉得三弟太偏激,日本人不能说一个好人都没有,三牧政雄怎样先莫论,他的女儿茶花贞子毕竟是个学生,梦人和她交朋友道理上讲没什么错,只是一旦发展成婚姻关系,民族感情上通不过,大部分徐家人不能接受,“老百姓对鬼子恨之入骨,梦人真的娶了日本媳妇,难逃众人唾骂。”
“我就不信拦不住他们……大不了权当我没梦人这个儿子。”徐德成说得恶狠狠,让人听来脊背发冷,“认贼作父不行。”
“三弟啊,梦人毕竟小还不懂事,我们慢慢想辙,不是快刀斩乱麻的事。”徐德中担心三弟莽撞,嫉恶如仇容易行为过激。他的忧虑并非无道理,德成和日本人结下的仇怨冰冻很深,这辈子化解不了。
“跟日本鬼子……我杀了他!”徐德成说,这句恨话当时可当气话说,再后来它是一种誓言,父亲血刃儿子。灭亲的决心几次下定,使故事的发展有了新的情节,徐家人对徐德成的杀子行为褒贬了一个世纪。
现在话赶话当成说说而已,徐德中认为三弟不至于怒杀亲儿子,简单地劝劝,话题转向四凤,问:“四凤知不知道你……”
“大哥没告诉她。”
“永远隐瞒下去?”徐德中问。
日本鬼子到处找天狗绺子,还是不露出真面目,徐德成想得更多的是家人安全,自己当土匪必然牵连亲人。他想念两个孩子,见一见他们,亲情、天伦离自己是那样的遥远啊!
“大当家的,”徐秀云闯进来,慌张道,“我们背累(遭难),横行子掉脚(被捉)了。”
“咋回事?”徐德成说。
“二哥,三哥。”徐秀云才发现屋子没有别人,改用家庭成员间的说话方式,“头晌(上午)我们出城,到了山根儿前,遇到日本宪兵把横行子抓走,我逃了回来。”
横行子给日本宪兵抓去生死未卜,肯定要对他审问,宪兵队的酷刑一般人挺不过去。徐德中问这个人有没有挺头?这涉及到宿营地的安全。
“横行子很有钢条(坚强劲儿),啥也不会说。”徐德成相信谢荣,此人的一家人都给日本鬼子刺刀挑了,即使日本宪兵杀了他,也不会招供的。
“德成,进山的路布双岗。”徐德中说。
“喝了吧,泄火汤。”徐郑氏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