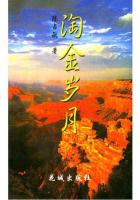徐德富上了股火,满嘴大泡,尹红为他配制一副药,夫人端给他。像遭秋霜袭击的庄稼一样,他一下蔫萎,火是上大了。民间有套说上火的嗑儿:睡不着觉,嘴起泡,尿黄尿!他现在所有症状都有。
“先喝了顶一顶,德中回来再好好扎痼。”徐郑氏继续劝。
“扎痼啥,我没病。”徐德富拒绝服药,说。
“没病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徐郑氏揭老底道,“梦人当翻译官你上股火,细想想,你多余。”
“瞎说。”徐德富斥打夫人,唠叨道,“你说这梦人走下道,找个日本女朋友也就罢了,这又给宪兵队当翻译,你说说!”
“孩大不由爷,他想干啥你挡得了啊?”
“咋挡不了?德成把孩子交给咱们,眼瞅着往泥坑里走?”徐德富责任感地道,“梦人是咱徐家的后代,又不是两旁世人(路人),不沾亲不挂拐,谁找闲心操。”
“你们打拨拉拐(起反作用)好使吗?顶事吗?”徐郑氏忽想出办法,说,“告送(诉)德成,他来管吧!”
“净出左巴俫(没有用)道儿,你呀!”徐德富说,德成诈死的秘密,关乎他的生命及家人的安全。日本鬼子恨他咬牙根直,警察也恨他,左右毁了容没人认出他来,“德成死活不能暴露。”
“梦人的事,将来我们还不落埋怨啊?”
“唉,落埋怨也没办法。”徐德富挣扎坐起来,说,“你把腿带子给我找出来。”
“你扎腿带子做啥?”她以为他要上厕所。
“下地,出门。”徐德富掀开被子朝炕沿边儿挪动,“明天开刀割浆,我得去看看。”
“瞧你病成这样……”徐郑氏把蓝布腿带子扔给他,“谢管家领着割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种了一春零八夏,收获全在割浆这一刀。”徐德富缠好腿绑,下地时头晕有些站不稳。
“直门散脚,你还要下地。”
“没事儿,没事儿。”徐德富刚强地出屋,在院子里碰见正要出去的二嫂。
“大哥,好点儿没有?”她问。
“见轻,见轻。”徐德富说,“我下地看看。”
“让大板儿套车送你去吧!”二嫂转身冲屋子喊,“娟儿他爹,你赶快出来!”
“哎!”佟大板儿答应着走出屋,先和徐德富打招呼,“哥。”
“大哥要去獾子洞,你送大哥去吧!”二嫂说。
佟大板儿便去套车。
“烟馆人客不少,四凤忙不过来,叫我过去帮她。”二嫂急着出去,和徐德富说完便出了院子。
徐家两挂大车,一辆谢时仿赶走,家里还有两匹马,佟大板儿套上它们,大车在秋天干硬的碱土路上行走。
“好像有汽车印儿。”佟大板儿低头瞅车辙,“胎花像。”
“准是去咱家地的。”徐德富推测是日本宪兵的汽车,送装大烟浆的瓷缸,林田数马和徐德富谈过大烟浆的处理问题,割下后过秤,装入宪兵提供的专用瓷缸,拉回宪兵队部。
大烟浆初加工成大烟膏并不复杂,割下的大烟浆就地用火烤或太阳曝晒都可,林田数马基于安全考虑,将大烟浆拉回宪兵队,再慢慢加工。
“大烟户都这么交烟奶子(浆)?”
“是吧。”
“宪兵队部搁得下?”
徐德富估计暂存在宪兵队部,怕谁抢夺去,最后还要运走。
“白狼山修建的像仓库,说不定就使它装大烟。”佟大板儿被抓去充当勤劳奉公队,在工地干活儿,“小鼻子这是整多少大烟啊!”
“海(极多)啦!你算算,一三江县就种一千垧,全四平省是多少,还有其他各省种的烟。”徐德富笨寻思,恐怕要成汽车往白狼山拉鸦片,他问起另一件事,“梦人当翻译,你两口子知道不?”
“才听说”,佟大板儿嘟哝道,“烦啥让你摊上啥,这不是从这话上来吗?偏偏梦人给宪兵队当翻译。”
徐德富沉默起来,对日本鬼子旧恨的疤给猛然捅了一下,有点儿疼,当年日本鬼子搞集家并屯,徐家百年祖屋拆毁,四百垧田地被逼种上大烟,四弟给角山荣杀害,三弟有家不能回……宗宗件件,都是日本鬼子坑害的。
“日后免不了遭人骂呀!”佟大板儿说,身上有块伤疤隐隐作痛,白狼山工地抬石头时走得慢了,被一个监工的宪兵刺刀戳了个口子,“整日同牲口们在一起,我怕梦人学坏。”
担心徐梦人变坏的不止一人两人,还有徐德富、徐德中、徐德成、二……东北民间有句俗语,徐德富经常挂在嘴边儿上:守啥人学啥人,守着萨满跳大神。那么守着日本宪兵学什么呢?杀人放火?
“打开家谱,我们老徐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人。”徐德富感慨道,往上找几辈,大恶之人还没出过,到了德字辈,四弟德龙算最不学好的,赌耍不成人,但死时也算壮烈,一俊遮百丑,“这辈人说不定就是梦人啦。”
“也说不上这孩子咋就和小鼻子近边(亲近)上的,邪门啦。”佟大板儿惑然,“我琢磨着和那个小鼻子闺女有关,准是她帮梦人找的差事,翻译官一般人当不上。”
“准是,他二伯说他两句,对二伯劲儿劲儿的,连家门都不进了。”徐德富有些伤心,梦人来家时才几岁,由于特殊--徐德成和齐寡妇生下的原因,二嫂成了他的亲娘,家人汤一碗水一碗地伺候大,盼他出息,送他到四平街读书,结果呢,事与愿违,学了日本话竟为日本人做事,即使做事也成,到宪兵队当翻译,做事变了味儿,与帮凶、走狗,直至后来的难听字眼儿汉奸近了,甚至在一般人眼里徐梦人就是汉奸,还是铁杆的,“捡了个遭众人骂的屎盔子,扣在自己脑袋上。”
佟大板看得更严重,说:“哪一天满洲国台子,他小命……悬哪!”
佟大板儿说到一个敏感的话题:满洲国倒台子。赶车的老板儿走南闯北听的多了,见的广了。一次在老山沟里听唱戏,有几句戏词儿他还记得:
别着忙,老乡们,
日本鬼子到中国,
光死没有活;
准有那么一天,
来几个死几个。
“有那么一天,谁也救不了他,是福是祸看命啦。”徐德富对侄子梦人失望到家,昨晚突然想开,不再管他了,任他去吧。
“大哥,你可别放大眼汤(撒手不管)啊!”佟大板儿真怕当家的不管徐梦人,“有一点缝儿,还是说劝他。”
“劝皮儿劝不了瓤,他自己要倒泚尿(自己害自己),你有啥辙?”徐德富说。
二嫂一迈进白罂粟烟馆,徐梦人扑过来。
“妈!”他拱进二嫂怀里,像小时候一样。
“小闯子!”二嫂还亲切叫他小名,十几年叫惯了,“妈想你。”
“我也想妈。”徐梦人这时不像令人生畏的宪兵队翻译官,倒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二嫂的手抚爱地摸摸儿子的肩膀,肉乎乎的茁壮使做娘的骄傲和幸福,她说:“都到镇上了,咋不回家?”
“妈。”徐梦人头没离开温暖的怀抱,曾几何时,这里给他珍贵的母爱,泪水在这里流淌,在这里止住,“我想回去,怕大伯、二伯他们……”
“竟说傻话,大家都是你的亲人啊!”二嫂动情地说。
一旁望着他们亲近的四凤悄悄地躲开了,肩头有些发冷,母亲拥抱就是温暖,亲人抱感觉真好。
四凤回到经理室,俯在桌子上流起泪来,蓦然想起儿子双龙,拥抱他软乎乎的像拥抱毛绒绒的出壳儿的小鸡。
“双龙,你在哪里?”
四凤心里默默呼唤儿子的名字,近来想念异常强烈,离去的亲人一个个地想,死在日军飞机轰炸下的母亲和妹妹小凡,丢失的儿子,最后想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梦人,你来一趟。”她对着话筒说。
“有事吗,姐。”电话这头徐梦人问,他在宪兵队的翻译室里。
“姐想你。”
“我过去。”徐梦人撂下电话,在宪兵队门前叫了辆人力车,来到白罂粟烟馆。
水果在古镇是稀罕玩意,四凤洗了盘苹果,稍稍有些酸,她让道:“吃一个苹果。”
姐姐的苹果吃到嘴里滋味特别,她看着他吃,父亲的影子叠入弟弟的身躯,他长的很像父亲。
两天前四凤在心里极矛盾的情况下,对他说,“梦人,我不是你堂姐,是你亲姐。”
“我知道,妈对我说过。”
“你长相很像爹。”她说。
“是吗,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爹没的早,那时你小。”四凤可不是随便说起爹的,她有目的提起爹的死,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诈死说在锦州一带和日军作战战死,她有意让他记住爹是怎么死的。对弟弟旁敲侧击或者说委婉教育,绝非突发奇想。烟馆开业典礼上,大伯徐德富的表情,她窥到他的内心,给宪兵队当翻译,他不满意,更多的是忧虑,他忧虑什么呢?别帮狗吃食儿……她要找弟弟谈谈,直截了当不成,效果不会好,动番脑筋之后,才有了提到爹的细节,“日军的飞机差不多炸飞了爹……祖坟地是座衣冠冢。”
徐梦人马马喳喳(影影绰绰)记得爹和一匹马,徐德成用马驮他到徐家大院,以后再没见到他。
“记得四叔吗?”她问。
“咋不记得,他给我做会叫的风车,跟我玩掷骰子,他有副铜骰子。”
“你记性真好。”四凤朝深里引,问,“他又是怎么死的?”
“大伯说跟角山荣掷骰子,赢了宪兵队长的军刀,被杀死”徐梦人回答姐姐的问话,没去想她有什么目的。
“梦人,咱爹咱叔都死在日本人手下……”四凤向弟弟传达足够日本鬼子害死徐家人的信息,下面就是她要表达的了,“你在宪兵队做事,时时处处记着死去的爹和叔啊。”
徐梦人似乎懂了姐姐说的这些是提醒自己,对日本人一时恨不起来,茶花贞子是日本人,三牧政雄也是日本人,杀死爹和叔的日本人,和他们不一样。
“以后做事,多拍着良心想想,我们是中国人啊!”四凤对弟弟语重心长,让他多做善事。
“记住了。”徐梦人要走,说,“姐,没别的事我回去了。”
“宪兵队有事?”
“没有。”
“没事不走了,晌午在我这儿吃饭。”四凤挽留道。
“我回去吃。”
“梦人,你最想见的人,马上过来。”四凤故意不说是谁。
徐梦人望着姐姐,见她笑盈盈,一下猜到是谁,说:“我妈!”
“是,她马上过来。”
“妈来了,妈来了!”徐梦人雀跃道。
到三江县宪兵队报到后,有两天空闲时间,他想回家,看看妈看看叔,还有大伯他们。思前想后他没出宪兵队大院,在屋子闷了两天。为顾虑,他没回家,谈了茶花贞子朋友,遭到家人的反对,最激烈的是二伯,他们对日本人恨吐血,当了宪兵队的翻译,还能让自己进门?
“妈!”徐梦人拱在母亲怀里,有一车的委屈话要倾诉,他忽然给人推了一下,见母亲惶然站在一旁,“怎么啦,妈?”
“那玩意……”二嫂直盯着徐梦人的腰部,方才她的手触碰到冰冷的铁器上,猛然推开他。
“妈,是支枪……妈你怕它?”徐梦人掏出佩戴的短枪给她看,“妈,就是一支枪嘛。”
“不不,赶紧收起来。”二嫂摆手,叨咕道,“我晕枪。”
“我放起来。”他说。
徐梦人放好枪,他奇怪她为什么如此怕枪。二嫂给枪吓破胆,是在八岁,警察枪掐折爹的手腕,她吓坏啦。
灯笼铺给一个大烟鬼一口一口抽黄了,田掌柜摇身成为田大泡,非金属炮,烟泡也!爹吃鸦片,有首民谣曰:
七茬八茬尽管抽,
九茬烟灰不进斗,
管他进斗不进斗,
抠到手,扔到口。穷富决定吸鸦片是否讲究,单从工具--烟枪上讲,有首民谣道:
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田大泡的烟枪杆可镂镀镶焊不起金银铜,用木杆制成,警察来抓他,竟举着木杆烟枪对着警察。
“拿枪对着警察,你袭警!”警察找到了开枪的理由,朝他射击打折大烟鬼的手腕。
爹流血的手腕阴影一样跟着她多年,怕枪,见到枪就晕就哆嗦,她无意触摸到徐梦人腰间的手枪,差不多吓坏啦。
“妈,你别怕,枪也没什么好怕的。”徐梦人安慰她,将手枪藏掖好,他问起佟大板儿,“妈,我叔好吧?”
二嫂说前不久给日本宪兵抓去白狼山做苦力,刚刚回家来,她说:“四凤找人要回来,他要去车行赶车,我没让他出门,怕再叫宪兵抓去怎么办。”
“不能了,有我没人抓他。”徐梦人说。这话不夸张,宪兵队翻译官的养父用不着去做苦力,说白一点没人敢小瞧。
宪兵队里有人,显然用不着担心家人被抓劳工什么的。二嫂想想也是,大板儿可以放心大胆地出去赶车。
“听四凤姐说,妈你来烟馆做事。”徐梦人说。
“做什么事,帮着忙活忙活,这么大的摊子她一个人咋忙活过来。”她说。
二嫂本着前来帮忙,其实四凤可不是这样安排的,烟馆业务两大部分,卖烟,政府专卖配置的鸦片送到这里销售;烟馆设二个房间,烟枪数杆,女招待数人,需要一个人来管理。四凤让二嫂管理这部分事务。
“走份。”四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