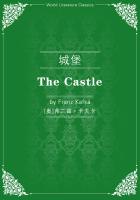我是在2000年8月29日午后3点离开白房子的。
我将在这块昔日的争议地区盘桓到晚上才离开。也就是说,我将从白房子沿着边界,穿过185团的六连、五连、四连、三连、二连、一连,同时,还要穿过边防军的另外两个边防站,即克孜乌营科边防站、阿赫吐拜克边防站。在这块前争议地区巡礼一周后,最后回哈巴河。
正值中亚细亚阳光灿烂的中午,我们的汽车在一片铺天盖地的金黄中行驶。阳光闪闪烁烁,在这金黄色的海洋上跳跃着,令人头晕目眩。
“这是祖国的土地一无可争议的祖国的土地。”
当我在这片金黄色的海洋上行走的时候,眼望窗外,我喃喃地对自己这样说。
我想起苏联的著名女诗人,被喻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那首名曰《祖国土》的诗。
她说:我赞美祖国的泥土,你是沃野,是乡间泥泞的道路,是旅人衣服上弹落的一丝微尘,是我们指甲缝里抠出的一丝垢甲。
现在由我来赞美,我的祖国的泥土吧!
它曾经差点失去,现在又重新获得。哦,这我们赖以立足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
这我们代代相袭的土地。
兵团的六连,是个渔业连,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依着一个椭圆形的沙包子,建起自己的村庄。村庄很小,只几十户人家。这些人渔汛时间打鱼,渔汛过了,便到大田里种地。他们住的村庄,一半是地窝子,一半是土坯房。我记忆中的那个扛着圆锹,穿着高腰雨靴,站在条田里浇水的1965年来的天津支边女青年,就是这个连队的。
紧靠六连的五连,村庄大一些,人丁兴旺一些。我记忆中,那个穿着一身变了颜色的将校呢,上衣肩膀上还有两个攀带的人,好像就是五连的连长。他是山东来的退伍军人。这地方以山东来的复转军人为主体,附近哈萨克牧民学的汉语,都是山东话。我曾在文章中写到的,那骑着从马车上卸下来的光背马,背着老式的冲锋枪,带着唐·吉诃德式的无畏,迎着界河对面开来的坦克的,好像就是这五连的人。
紧靠五连的,是四连了。四连紧靠着185团团部。
其实在185团团部周围,还驻扎着一些兵团村庄。以前我不知道,以为它们是团部的一部分,这次才知道,武装值班连、修理连,还有八连等等,都在这里,从而令这里成为一座边境小城,这小城就以“185”命名。
当年我骑马从这里经过时,那个男人打仗去了,女人拖着孩子,坐在花格包楸上,准备撤退的人家,就是八连的。
这户人家在这块争议地区生活,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家的男人,就是1962年伊塔事件以后,匆匆赶往这块争议地区的一个。他们还住在原先的那个土坯房里,因此在这次行程中,我很容易找到了这户人家。我请记者小陈在这间土坯房前,为这四代兵团人拍上一张全家福。
沿途这些兵团村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惟一的变化是树木多了点,村庄掩映在绿阴中,再就是地窝子已经没有了,不论贫富,人们都住进了土坯房里。再一个变化就是,人们的衣着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比起外面飞速发展的世界,兵团人还很苦。为我开车的那个部队的志愿兵说,光看一看这些几十年如一日的土坯房,你就知道兵团人比起部队来,比起地方来,是变化最小、生活最苦的。
兵团人目前的尴尬处境,和他们曾经给予共和国的无私奉献,是不成比例的。
在八连这户陈姓人家的土坯房前,兵团作家老钱对我说:“你才在这里当了五年兵,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兵团人已经在这个地方守了四代人了。兵团人可怜,当兵的服役期满,最多再超期限服役上一两年就屁股一拍,走人了。可是兵团人没个走处,也没有个盼头,他得世世代代守在这里了!”
老钱说的是实情。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能说出一些重要的话,而且不避情面。这也是我十分喜欢这个兵团作家的原因。
每一个兵团人身上都有一种他们称之为“兵团情结”的东西。
这种“情结”我在乌鲁木齐一接触到兵团人时就开始领教,在北屯与老杜相逢时,立即就被他那“伟大的公民”一说感染,然而,最具有“兵团情绪”的人,还是这个老钱。
他是兵团的第二代。他出生在石河子。
只要一谈到“兵团”这两个字,他就眉飞色舞。他会滔滔不绝,从部队进疆开始,从荒原第一犁开始,从新疆一些大型企业是如何起步的开始,一直讲到今天。他对他是兵团孩子,他的出生地是石河子这一点尤为骄傲。
但是,老钱也有黯然神伤的事,这事就是兵团那一年从准军队序列中,划给农垦局,变成边境农场的事。
老钱说:“虽然后来又恢复过来了,但是,从此以后,好像大家商量好了一样,兵团人再不去过八一建军节了!”
我能理解老钱的感情,也能理解每一个兵团人的感情。
说点愉快的吧!
我们到达185团团部的时候,这里正在大兴土木。昔日破旧的土述房正被推土机隆隆推倒,本身就宽阔的路面现在被掘开,修得更宽。一座城市建设的第一步是挖埋地下管道设施,因此,这一块不大的地面,现在被挖得处处是壤沟,处处堆满新土。
我们的汽车绕了很久,走了很多冤枉路,最后才找到团部。
185团的宣传科长也在车上坐着。短短几天,他竟然也找不着路了,可见变化之大。
185团的政委对我们说,国家要搞一个“边境美容”工程,改变边境一线团场目前的这种破败景象。以185团而论,国家计划每年投资两千二百万,连续投资十年,总资金两亿二,将这里建成一座边境小城。
一座座的兵团人当年修筑的小窝被推倒了。老杜在这里也很熟,他领着我在尘土飞扬中找了很久,才找了一些过去的房子,找到一个喀拉苏公园在中国版图上,以时拉克别克河为界河。在前苏联版图上,以喀拉苏自然沟为界河》这就是白房子争议地区形成的原因。现在随着白房子归属的确定,兵团人将喀拉苏自然沟填乎,并在上面建起公园,篮球场,找到当年的供销社。
篮球场叫我记起来了,当年我们骑马巡逻来到克站后,曾经把马拴在克站的马号里,徒步到这里,和185团打过一场篮球。
喀拉苏自然沟从185团的小城中间穿过。
兵团人真是伟大,早在几年前,他们就把这个惹是生非的小水沟用沙土填了,建成一个公园。这公园就叫喀拉苏公园。公园上的题名,正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聂副师长。他当时是这个团的团长。
“让这条水沟从地面上消失,让老毛子彻底断了想念!”兵团人这样对我说。
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就在185附近,靠近边界的地方。我们的汽车绕了好一阵,满眼狼藉,找不着去克站的路,于是只好作罢。
继而,我们继续沿着边界线向北,穿过兵团三连,兵团二连,最后,到达阿赫吐拜克边防站。
阿站在右手是连续起伏、冷峻高大的阿尔泰山,左手那是我们的来路,则是儿座像金字塔一样闪闪发光的沙丘。正前方,下个坡坎便是界河,界河对面,是哈萨克斯坦小城阿连谢夫卡。
阿站距白房子50公里。
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曾经提到过一个无头烈士纪念碑的事。首先,这事是真的,它曾经发生过。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一百年前的故事是如何钻人我的脑子中的,是饶舌的分区参谋讲述的吗?或者,是口口相传的老兵们告诉我的?抑或,是在我的沉沉的白房子的梦中,昨日的一幕如梦境般呈现?
我原先以为,这个无头烈士纪念碑在阿连谢夫卡边防站,这次,
翔实考证,才知道它是在白哈巴边防站。从白哈巴巡逻到阿赫吐拜克,到白房子,有遥远的路程,况且还要翻越几乎无法逾越的阿尔泰山,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看来,我是把几起边境事件放在一起说了。
不过这个无头烈士纪念碑是确确实实地存在。
下了阿赫吐拜克的了望台,我们再去眼镜山。
眼镜山的那个地方,在兵团一连。这个兵团村庄紧靠着一座大沙山,那沙山光禿秃的山坡上,长着两棵落地叶。这落地叶像人的两只眼睛,所谓的眼镜山,就是因此得来。
兵团人说,当年边境局势紧张的时候,这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昼夜间一眨不眨,如今边境局势缓和了,这两只眼睛一个睁着,一个闭着,正如俗语所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哈萨克族传奇人物塞力克的墓地,在比利斯河西岸。
我早在十六医院的时候,就得知这位故人业已故世的消息。忧伤的我,那时候就叮嘱自己,此次白房子之行中,一定要去拜谒他的墓地。
在这一片草原,塞力克是一个传奇。
那一年的夏天,我正在边防站的菜地里干活。远远地,从比利斯方向,颤巍巍地走过来一人一骑。那人,高高的个头,宽肩膀,长脸,穿着一件黑色的灯心绒上衣,腰间扎一根宽皮带。那马,是一匹焦黄颜色的小马,大走马,在骑手的胯下,它像一只兔子一样弱小。
那人骑着马颤巍巍地走过来了,像一座移动的铁塔。
“铁塔”在菜地铃铛剌扎的围墙外面停住了。骑手头顶的三耳皮帽不再闪动。骑手骑在马上,一手扶着马鞍,拱起腰,招呼道:
“加克斯(1)吗?”
“加克斯!”我回答说。
我不知道他是谁,只觉得他像传说中的草原四处游荡的勇士一样。说心里话,我有些害怕。
“你是内地来的巴郎子吗?我叫塞力克!白房子的人我都认识!”
(1)哈萨克语,你好。
来人见我有些狐疑,于是补充说。
接着,他问边防站的储医生在不在。
这句话叫我放心了。我明白了这人至少不是一个越境分子。
问话的那一刻,我手中正握着两个西红柿。那一年一个河南兵探家回来,带回来一种叫“北京梨”的西红柿种子,这西红柿长得像鸡蛋般大,圆圆的,一株上结红艳艳的一片。
于是我将西红柿晃了两晃,问他吃不吃。他摇摇头说不吃,他说这东西里面籽太多,吃了它以后,会生很多很多孩子的。虽然他这样说,我还是把西红柿扔过去了。我以为他的摇头只是一种推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哈萨克人从来不做作。
塞力克伸出大手,接住了西红柿,他凑到眼睛跟前看了看,又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最后,装进了他的上衣口袋里。
塞力克扬了扬手,告辞了。谁知,马儿走了两步,他又停住。他问我回不回边防站,说着指了指天上的太阳。我回答说我正准备回去,于是他说,捎上你吧。
那匹小黄马载着他,已经是勉为其难了,现在再加上一个我,能行吗?
塞力克笑着说:“能行!”
我关好栅栏门,走到马的跟前。
塞力克骑在马上,伸出两只手,卡住我的腰,轻轻一提,我便坐在他的马屁股上了。
马儿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一样,载着两个人,一路碎步向白房子走去。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塞力克的情形。
后来听边防站的副指导员说,塞力克是前哨公社反修大队的支书,从比利斯到白房子,这一块偌大的草原上,就这么一个牧业队,它的面积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县。副指导员还说,塞力克的妻子有胃病,所以他经常到边防站来,为妻子要几个药片。
而更多的关于塞力克的故事,是我听班上那个叫阿依同拜以的哈萨克说的。
这个战士的家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数百公里的锡伯渡,他也知道塞力克的故事,可见,塞力克确实是阿勒泰草原上的知名人物。
那年代许多事情都与人们的一种反苏情绪有关,塞力克的故事也是这样。
50年代末,苏联的世界摔跤冠军在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况下,巡回表演来到中国。并且在北京设下擂台,向中国人挑战。
那时中国大约还是有个专业的摔跤队吧。结果这些人在世界摔跤冠军的面前,根本不是对手,被冠军像老鹰捉小鸡一样,一一摔倒。
对中国人来说,这确是一件失面子的事。况且在那个时期,人们对摔絞这件事本身,赋予了摔跤以外的许多意义。
不甘示弱的中国官方,听说在遥远的阿勒泰草原上,有一位臂力过人的勇士,同时也是摔跤高手,于是用飞机将他接到了北京。
塞力克曾经向我描绘过那个世界冠军的情形。他说那家伙出场时,被一根铁链子拴着,嘴上像马一样勒着钗子。他披散着长头发,嘴里嗷傲地叫着,吐着白沫,在铁链子哗啦哗啦的牵引中,被送到台上来。
塞力克说,他当时吓坏了,他感觉到那家伙分明不是一个人,而是个哈熊。
钗子取开,牵引铁链子的人往旁边一闪,世界冠军便咆哮着向塞力克扑来。
塞力克心想,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了,怕也没用,于是就迎上去,架住那家伙的膀子。
塞力克那时候大约也就是二十四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几个来回下来,塞力克心里有了点底。他发现这个像野兽一样的人终归还是个人,他的招数有不少破绽,他的实力也并不像他的外表那么可怕。他那嗷嗷乱叫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战,吓唬对手的伎俩。
于是塞力克开始反击。
那家伙见摔不倒塞力克,急躁起来。
塞力克化解了他的一次进攻,趁他重心移动,双脚不稳的时候,使一个巧力,将那家伙平平展展地摔倒在擂台上。
那家伙不服,说并不是被塞力克摔倒的,而是他自己絆倒的,提出再摔。
塞力克已经心里有底,也就不再推辞,于是抖起精神,使出本事,将这个世界冠军连掼三跤。
事情发生在第三跤的时候。
当塞力克将世界冠军摔倒,自己的身子也失去平衡,随着世界冠军一起倒下的时候,那个卑鄙的家伙,在倒地以后,用胳肘拐子,狠狠地朝塞力克的腰间顶了一下。
塞力克当时只觉得腰间一阵麻木。
胜利的喜悦令他忘记了腰间的疼痛。只是回到下榻的地方,松池下来以后,腰间越来越疼,一检查,才发现三根肋骨断了。
塞力克养好伤,便留在北京,担任摔跤教练兼队员。
虽然他不是世界冠军,但是因为世界冠军败在他的手上,所以大家都称他世界冠军。
北京的生活不习惯,于是塞力克偷偷地坐火车跑了回来,重新回到这一块草原。
塞力克对我说:“没有奶茶,没有抓肉,没有草原,没有马,我受不了!”
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也就没人管他了。他躲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继续做他的草原王。而上级后来也就顺便给了他一个职务,这就是反修大队的支书。
哈巴河县武装部每年冬天组织的军民联防指挥部进驻南湾的斗争,塞力克他们那个牧业队好像也参加过。其实,在菜地里见过他以前,我想起了,我在南湾巡逻时也见过他的,只是当时冰天雪地,头上有苏联的直升机驱赶羊群,我的心情很紧张,没有记住他。
塞力克的妻子我也见过。她脸色很白,显得十分高贵。高高的颧骨上停着两朵病态的红晕。黑油油的长发将脸颊遮住。她从来不说话,见了人只害羞地一笑,算是招呼。她好像经常胃疼,老是一手捧心,一副病西施的样子。但是只要从边防站拿几片白色药片,一吃就好了。再就是,她的马骑得漂亮极了。她骑在马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再背一个小孩,马儿如飞地从草地上驶过去,肚皮贴着草塞力克的马也是一匹好马。
另看这马又小又瘦,却很有力气,又有耐力,而且聪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