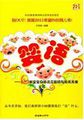没过多久,南城门口传来喧哗,士兵们各种呼喊,更有一个焦急的军官声在斥责。
不一时,城洞里火光大亮,火光掩映下,士兵整齐的列队,朝城内小跑。队伍中每隔三二人就举有火把。此时一整夜的大雨终于放晴,连淅沥沥的小雨都不见了,士兵们踩着大雨的泥泞冲向旅店。
元栎看在眼里着急在心头,呆呆看着,一直到这些人走到旅店门口方才醒悟过来。这下玩大啦,整个城都出动了,不快点找藏身之处,哪里还有命活。
心跳恰在此时应景似的加速跳动,元栎摸着胸口:大哥找到地再跳啦,这会儿不要动啦。
守城士兵刚到旅店门口,就有士兵上前禀报,双方比划,然后抬出数具尸体,军官大手一挥,然后就有两三组士兵分东、西、北各自持火把而行,他们开始搜查了。
元栎又返身折回小巷,又不敢进巷口,生怕引起这些狗叫。思索一下,躲在巷口终究是不对,搜查之时这里必定是重写照顾对象。
元栎急得跺脚,好像士兵们马上就要到这里一样。他突然想到要去文庙,文庙里好藏人。仔细张望一下,旅店门口的士兵都进屋里,像是在安慰住客。
元栎脱下床鞋拎在手里,一只手按住身后的斗笠,为减少声音。猫着腰,小跑着路过旅店门口。他恰如一条夜猫,没有发出点滴不应该的声音。
凭着直觉,他跑到城中最大的院子前,果然这院子就是文庙。元栎毫不犹豫,纵身扒住墙头,稍一用力就翻入院墙。
院子里静极了,这时候也应该没有人在。大门口通向大殿的砖石路上摆着一个青铜大鼎,相毕平日里也香火极盛。外面有些许人声,正殿青砖大瓦,大门紧闭。
元栎贴在门口听声,说话的人声也离这里很远,雨后的院子充斥潮湿的气息。循着青砖路向前走,绕过大鼎,大殿正门关的紧,元栎推不开。
绕过大殿,后面什么也没有,空空荡。想是只有一个正殿。有人打着火把从后门走过。
突然有一个人声高叫道:“你们几个快去找钥匙,打开文庙看看,还有土地庙,别让贼藏在这里。”
怕什么就来什么,还没坐下来休息,人家就又找上门了,跑啊!元栎抢先跑回前门,扒上墙头,所幸外面还没人。
又冲到大路上,所幸路上没见官兵,倒是文庙后面的路口边,有三五个火把,这些兵待在那里休息,搜寻点时间自己还先就累了。这样的兵有什么战斗力。
元栎心下正不知如何去处,偏偏看到城门口。泗州城本就不大,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到边的。此时门口已经没有士兵了,本来门洞里面夜里还有三四个士兵,刚刚一发都去旅店,这时候门洞那边恰是一个人都没有。
“正合我意!”元栎心道:“都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就去那城门口。”
门洞里,本就没有点灯,漆黑一片,元栎左右张望,暂时还没有,士兵朝这个方向。恐怕他们恰巧知道城门口贼人是万万不敢去的。
他们哪里会知道,元栎偏偏冒这个大险。一步三回头,旅馆里面正是热闹呢,仵作才来正在检查死因。知州赶到,就在怒骂士兵,几乎已到唾沫横飞的地步。而在他身边的士兵个个大气不敢出。宋朝重文轻武的气氛可见一斑。
元栎来回几趟,众人丝毫不觉,等他面躲进门洞里边。官军搜查力度加大,好似被知州查出昨天收幽州人贿赂,知州大怒,几乎打发所有士兵出来,整个里鸡飞狗跳,全城的狗都叫起来。
一片狗叫声中,元栎突然注意到门口东边的这家人并没有狗叫。那小巷甚是偏僻,离南城门口一百步的距离,元栎沿着城墙走,到这家人的正门口,有意无意的,轻拍铜环,小院里仍然没有反应。
元栎心下大喜,这家人恐怕没有养狗。于是后退两步,纵身一跃翻上墙头,仍然没有狗叫,元栎放心许多。
他并没有进入院子,而是趴在这家的房顶。茅草屋顶还是很湿,但也顾不上许多。方才趴下,门前就有人举着火把穿过,火把一直往里面走,走得很深,只剩下两个点。
这会儿才半夜,元栎睡意上来,也不管后背湿透,合上眼便睡。不过因为背部冰凉元栎不一会便醒来,此时外面的动静已经没有了。正不知道那些幽州人去哪里了。
一夜不能合眼,到第一只公鸡开始打鸣,启明星闪现,乌云已经飘走了。元栎的马尚且在旅店里,恐怕他的房间杀人,官府正等着他去呢,只好不管它。
等到城门洞开的时候,元栎径直走出去,这时候对进城的人盘查很严,出城的人却并不严。
听着旁边有人议论昨夜的事情,元栎侧耳倾听,其中有一人悄声道:“听说昨天晚上有辽国的奸细在张家店里面杀人,那王伍长,早先受过他几两银子放他们入城,结果晚上就起来血案。听说昨晚杨知州大怒,恐怕要砍他脑袋。”
另一个人又道:“这王伍头,平日里,咱们进城百般刁难,谁家给银子就见钱眼开,早知道他会有今天。”
元栎微微一笑拉上斗笠,徒步出城,走了大半日,才又回到那药铺。
跟浪里白条细说这件事,里城里人说那是辽国人,这是个重要线索。
浪里白条道:“你这一趟倒是有惊无险,即是辽国人,城中说不定有什么收获。小姻的病咱们也要找个好点医生,咱们不如此时再去。”
元栎于是在这小镇上买一辆小马车,将小姻安置好,她此刻仍神志不清。浪里白条体格健朗,此时已经能坐起身来。
元栎便赶着牛车晃晃悠悠的,又用了几乎大半日的时间,等到晚上才又到泗州城,这回守城门的果然不是之前那个王伍头。
门口贴出告示,说昨晚有辽国奸细在城里动刀兵,要求大家见到辽人余党之后立即报官。别的一无所说!
士兵们见元栎带着病号并不刁难他,直接放他入城,元栎顾不上那些辽国人,首先去找药铺。
路人就指了最好的一家药铺,这医生早年在汴京城做事,等到晚年就迁居泗州据说医术高明,然而他看小姻还是得不出结论。
他要来元栎之前带的药方,看完之后,他道:“这药方着实没错,不过我再开一幅别的。”说着他又道:“你们大老远的来这里恐怕没处住吧,今夜就权且暂住我家,等药煮好之后,也可以及时送服。”元栎二人自然千恩万谢。
安顿好小姻服药之后,仍然是没有知觉,不过好似高烧已退,面色转正常,皮肤也并不发烫。
第二日,元栎大早出门去打听昨夜黑衣人的下落,听得茶馆里面,众人谈论。昨夜想必发生火并,其中有好汉独自杀了七八个辽国奸细,只不知那好汉下落,他的马还在旅店里,官府正在寻找。找到之后重重有赏,
元栎心里嗤笑,恐怕是找到之后要将自己拿来问罪,自己私藏违禁兵器,官府怎么会放过他。又听人说之所以认定是辽国人是因为身上发现了玉佩,玉佩上都是契丹文。
元栎暗自心想:这伙人真是辽国人,恐怕也是北方汉人。要不然我怎么汉化会说的那么流利。
当下回去告诉浪里白条,浪里白条跟元栎商议,小姻终究是女孩儿,一路上照顾多有不便,叫元栎去街上买一个丫鬟回来。
元栎情知是这个道理,便去到集市上,找到人芽子,只花五两银子便买了一个小丫鬟,元栎看着小丫头长得甚是水灵。楚楚可怜的样子便也不讨价还价,直接领走。
这小姑娘叫杏子,是本地人,既然被卖出来则各有各的心酸,元栎当下也不提,便带她一起去买一些妇女的衣裳、换洗用品,又回到药铺。
医生本在给人开药,见元栎回来,三下五除二便写了一副药方送给来人,叫他去那边拿药。然后拉过元栎,边走边道:“你来、你来我、跟你讲!”
走到后院,元栎着急问:“大夫有什么事?”医生道:“我观察她天,也不知为什么药力不行?恐怕我医术不佳。”说着他拿出一封信交给元栎:“我师傅在汴京城,专治疑难杂症,你去汴京问问我师傅,性命攸关之事,你还是多问问人好。”
这医生倒是很会做事,元栎接过信,千恩万谢,然后去跟浪里白条商议。
浪里白条权衡利弊,此刻动身去扬州也帮不上忙,倒不如就先去汴京将小姻伤病治好。当下便修书一封,交给这边的客商,要他们将此书送到自己手下人。
此时浪里白条从身边摸出一张银票交给元栎,叫他去城中兑换银两,元栎一看,银票足足一百两,来此间数日元栎也知道银两的贵重,一百两可不是小数目,浪里白条笑道:“银票就给你了。一路之上多有花费,此次出行我身上也不过只这一张,你就拿着用吧。”
元栎收下不提,随便去城中买了一辆大车马车专门给小姻用。而浪里白条虽然力气不强,却已经可以驾马车,叫杏子跟小姻在车内,元栎自己买一匹马。
四人一行,便沿着官道,取汴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