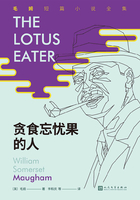那女人姓杨,是个寡妇,从十七岁便开始守寡,来时才二十多岁。她待熙岱不错,对他也有那么一点心思,可熙岱在杏花的事情上伤透了心,说什么也不愿再娶女人了。他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许多年,直到杨寡妇让翠儿的护兵枪杀
香莲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情景实在是太凄惨了。几千两银子给洗劫一空,杏花在惨遭轮奸后,悬梁自尽,可怜的哥哥经历了这场横祸,也变得精神恍惚起来。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李宜龙也现出很意外的样子,在院子里踱着步。他瞅了眼在一旁垂泪的夫人,安慰着:“香莲,别难过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也许都是命。这样吧,干脆把他先接过来住些日子。他也算暂时有个着落。”
“不,我不离开这里,杏花是死在这里的,我也要死在这儿。”熙岱拄起拐杖,朝前走了两步。
“笑话,你在这里可怎么活呀。”宜龙看一眼香莲说。
香莲此时的心思没放在这儿。她琢磨着这事发生得蹊跷,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问:“宜龙,你看这事是不是有点怪?”
“咳,事情明摆着的嘛,人家是看上熙岱的哪点银子了。”
“可熙岱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的银子?”
宜龙见事情瞒不住了,便说:“香莲,你当时快生孩子了,所以我也没跟你商量,就做了主,借给你哥一万两银子。我原想能成全他,可谁知这反倒招来了祸事,真想不到啊。”
香莲脸色大变:“你怎么能这样!熙岱他一向是挣一个花仨的手,你这不是坑他吗?”
熙岱火了,冲香莲说:“你不要埋怨了,这钱我以后还你好了。”
“哥,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说宜龙这样做不合适,至于钱不钱的,我根本就没想。”
“算了吧,我看透了,你还是心疼你的那点银子,心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哥哥。”他依旧气恼地说,“现在好了,杏花没了,银子也没了,我又一贫如洗了,守着这个空宅还有什么意思,明天我就把它卖了顶帐。”他越说越激动,忍不住拿起拐杖使劲敲了两下桌子。
香莲虽说气得不行,可一看熙岱的样子,怕他再生出什么意外来,便不再说什么了。熙岱仍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还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任凭大家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幸亏梁云贵在场,凭他三寸不烂之舌,才将熙岱又接回李府,腾出一间屋子安顿下来。
熙岱在精神上已经彻底垮了。晚上,他常常做恶梦。杏花的影子总浮现在眼前。他忘不了那惨烈的一幕,自己的妻子给剥光衣服任人蹂躏,而他却眼睁睁地瞅着,无能为力。这还叫什么男人!
在安葬杏花的墓地上,他痛哭失声,跪在杏花的坟前喊:“杏花,我不该娶了你,是我害了你呀!”
香莲也哭得泪人似的。她恨自己出于私利,将杏花推给哥哥,以至造成了这种结局,不管怎么样,熙岱还苛且活着,杏花却屈辱地死去了。李宜龙面无表情地站在他们的身后,而心情却异常复杂。他意识到闵宅归到自己的名下已指日可待了。但是,这也许会让他从此背上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他不信基督,但他信因果报应。自那天从葬礼上回来,他害了一场重病,在床上一躺就是十几天。
吴渔闻讯赶来探视他,还以为是为了辞官的事,便安慰说:“我已将辞呈报给朝廷了,恐怕用不了多久便会批复回来。”
李宜龙苦笑着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这生生死死,恩恩怨怨,要到哪一天才能了啊。”
吴渔给他的话搞糊涂了,也弄不明白他究竟指的是什么。但见他神情抑郁,满嘴都烧起了水泡,像是遇到了什么想不开的事。他有心打探一下,可宜龙缄口不语,也只好作罢。他草草地安慰他几句,便乘上官轿回府了。
闵香莲抱着雨霖送走了知州大人,又回到丈夫跟前,关切地问:“感觉好些了吗?要不要让柳眉再给你煮碗参汤补养补养。”
他摇摇头说:“我这是急火攻心,等过了这一阵子,就会好的。”
“急火攻心?”她奇怪地说,“难道就为熙岱和杏花的事?”
他点点头:“我只是觉得我对不起熙岱他们俩,一时疏忽,搞得他们家破人亡了。”
香莲也心情沉重地说:“这也怪我当时就不该鼓动杏花去。唉,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
“是啊,当时熙岱要是不走就好了,哪能出这等事。”宜龙瞅了眼香莲,话里有话地说。
“先前我是撵过他,可后来还是熙岱他自己要走的嘛,我有什么错。”香莲以为他在责怪她,争辩说。
“事已至此,咱们相互埋怨是没有用的。”他振振有辞地说,“要紧的是我们该给熙岱以后的生计考虑考虑了。”
“还有什么考虑的,我哥都成废人了,只有靠我们养活了。”
“可那所宅子怎么办?”他从床上坐起来,关切地问。
“好啊,你还惦记那宅子。你就死了那份心思吧。”她变了脸。
“看看,你又误会了不是,我可是完全为熙岱着想。”
“嗬,看你说得多动听。现在我倒要听听你的高论。”
“香莲,你也不想想,熙岱混得这样惨,还不都是住了这座宅子的缘故。一年前被人打断了腿,现在又送了老婆的命,按风水先生的说法,这叫凶宅祸宅。除了宅子更名换姓,风水才能转回来。”
“是吗?”香莲将信将疑地说。
“千真万确,我是亲耳听人家讲的,不信你去问梁云贵。”
香莲找了梁云贵。他说的也和丈夫的话如出一辙。她有点相信了,便说:“那就让熙岱把房子卖掉吧,也好破破邪气。”
熙岱这边也对宅子伤透了心,死活也不愿住进去了。于是,香莲才最后下了卖闵宅的决心,可心情也很不好受,毕竟是百年的家业啊。她托人打听了好几个买主,人家不是嫌这宅子晦气,便是嫌价高。好不容易有个上心者,刚谈好价格,可第二天不知为啥又反悔了,死活也不肯要,把个香莲气得够戗。
这时,梁云贵凑了上来献策说:“夫人,我看这宅院九九归一,还得你和老爷买下来。这样做,一来成全了熙岱,二来还可以把你们现有的房子给了他,他也好有个安身之处。”
香莲想想也是这个理儿,就答应下来。闵宅最后核定一万六千两银子,除去原先熙岱借的一万两,李宜龙答应再付六千两银子,但要寄存在香莲处,以防再生出什么祸事来。
前年夏天,当我领着尹莉莉站在这座大宅的院子里向她陈述这段故事时,她深深地为杏花的悲剧结局而难过。她非要我领她去见见杏花自尽的那间屋子。我将她带入那间挂满尘埃和蜘蛛网的房子,只见房梁的朱漆大都已剥落,那张雕着龙凤的婚床早已不知去了何处。可据有人说那张床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给黄毛手下的人抬到院子里烧掉了。
我记得尹莉莉那天穿了条牛仔裤,上身是黑色的低领T恤衫,双背带的皮包也是黑色的。她望着我,用手撩了一下长发,说:“诗剑,这屋子的确够瘆人的,让人总感到带有一点血腥气似的。”
“是吗?”我故作惊讶状:“这里应该开辟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教育像你这样没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
“去你的。”她挥起那柔弱无力的拳头,在我背上捶了一下说,“我要是把你姥爷干得臭事跟我妈一学,她就更不会让我跟你处了。”
“那太好了,我还正愁找不到机会换个女朋友呢。你要是做了,一定人会使许多女孩子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我大声开着玩笑。
尹莉莉也不生气,还继续挖苦说:“别自我感觉良好了。谁不知道你,把你姥爷的那点风流基因都继承了,看见人家漂亮的女孩子冲你笑一下,就以为人家对你有意思了。你也不自己偷偷照照镜子,除了我,还有谁能看得上你。”
“哎,你可不要随意贩卖血统论呀,我可告诉你,我妈妈姐妹几个,生下的孩子日后可大都是作风正派的好人呢。”
“除了你之外,我都相信。”她依旧笑着气我。我说不过她,就伸手去捂她的嘴。她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好啦,别闹了,咱们讲和吧。我请你吃冰淇淋。”
“真的?”尹莉莉一听吃,兴致就来了,拉着我就往外走。
“等等,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急忙说。
“没关系,我等会儿给你续这个故事,准与你讲的不差分毫。”
“胡扯!我讲的可都是真事,绝没演绎的成分。”我表白说。
我们俩坐进一家高雅的冷饮店里。这间冷饮店不大,墙角放着卧式空调,吹出了咝咝冷风。店中摆放着六套酸枝木雕的有清代风格的小桌与座椅。八角形藻井的中央悬吊着精致的彩色宫灯。一位身着深紫色旗袍,凤髻盘云,珠光钗影的服务小姐款款而至,端上了两份冰淇淋,嫣然一笑,道了声“请”字就走开了。
“够档次。”莉莉环顾左右,满意地点点头,“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它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不像刚才见的古宅,给人一种压抑感。对了,这个冷饮店叫什么名字来的?”她用木匙放入嘴里一口冰淇淋,微笑着问我。
“哎呀,进门时我也没注意。小姐,这个店名是——”我冲那位不远处的服务小姐问道。
“先生,这儿的店名是‘冰清苑冷饮店’。”
“嗬,名字挺新鲜的。”我饶有兴趣地说,“不过缺少了点情趣。”
“先生错了,”那小姐说,“凡到这儿来消费的,大都是情侣,我们起这个名字,就是祝愿他们情真意切,地久天长。”
我和莉莉相视一笑,有点无话可说了。我们刚刚从古宅走出,又走入了一家冰清苑冷饮店,这也许是个巧合。可我们的话题还是没离开那座古宅。
尹莉莉说:“哎,你姥爷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那座大宅了,你对这事的看法如何?”
“我不是历史学家,无从把握这事情的是非曲直。”
“耍滑头。”她讥笑我,“一个省作协的专业作家,如果连点起码的正义感都没有,那就还不如回家躺着去。”
“行啊,只要你能养得起我,我也甘愿做个闵熙岱的。”
“你别提他好不好,我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窝囊。”她一把捂住了耳朵。
“好,我遵命。”我忍俊不禁,“那就让我给你讲讲日后那古宅的命运好了。”
“得,你还是让我来讲吧。”
“你怎么倒反客为主了。你真的要续这个故事?”我有点不相信的样子。
“事情明摆着的,你姥爷在这件事上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既欺骗了你舅姥爷熙岱,又愚弄了你姥姥。”
“你有什么根据?”
“这还用说吗?当初,李宜龙让梁云贵引闵熙岱上钩,借给他一万两银子,便埋下了伏笔,又将杏花许给他,原指望两人不和,李宜龙好从中渔利,不料杏花待熙岱不错,用善良的心感化了熙岱,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李宜龙将大宅收归己有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便打了坏主意,让梁云贵雇人闯进闵家,抢走了他们借的银子,想逼他俩走投无路卖掉宅子。谁料,来人见到杏花长得漂亮,便动了邪念,不但抢了银子,还强奸了杏花,以至杏花寻了短见。”
我惊得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怎么真的编起故事来了,谁能证明是我姥爷雇人抢了熙岱的银子,奸了杏花的?”
“我是推理推出来的。”她认真地说。
“你整个一中国的福尔摩斯呀,可惜论据不足。”我认真地说。
先前,我也这样推想过,可妈妈告诉我,姥爷和姥姥对此事一向守口如瓶,忌讳颇深。阴阳脸究竟是谁派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不过解放初,有人在沈阳的一个公审大会上见过他。他以抢动杀人罪给押赴刑场。他那时已成了一个干巴老头子,居然入室抢动,还杀了一个九岁的男孩。但我觉得阴阳脸不该是我姥爷支使去的,他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手段来得到这座古宅的。
“诗剑,咱们别争论这件事了。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不过我倒是挺可怜闵熙岱这个人,他活得挺凄惨的。”
“是啊,生活对他有些不公平。他实际是一个时代造就的畸形儿,坑过别人,可更多还是被人坑,最终还是不明不白死去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
“大概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吧。”我想了想说:“我姥爷辞官搬进那座大宅后,就把自己原先住的房子给了熙岱,还雇了个女佣伺侯他。那女人姓杨,是个寡妇,从十七岁便开始守寡,来时才二十多岁。她待熙岱不错,对他也有那么一点心思,可熙岱在杏花的事情上伤透了心,说什么也不愿再娶女人了。他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许多年,直到杨寡妇让翠儿的护兵枪杀。”
那晚,我和莉莉在冰清苑冷饮店坐了好久,中间又要了点心,边吃边说,把晚上去听音乐会的事儿都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