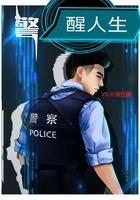我一个人,朝着剧团的方向。那时家家屋前都晾腊肉,不小心就有油滴到头上,街道已经在改良,到处是修葺的迹象,一个新建的大市场把大路分成两半,剧院被日益瘦身,压缩在大路的末端。不远处应该就是大河,往常这里可以听到水流的声音,如今隔远了,全是打桩声。河的对岸是杨岭,河的旁边有学校、农村,沿河的无人区就是鬼屋,那里成就了我和毛毛的初恋往事,没有多久,所以的一切都将和往事一样面目全非。剧院外贴的是颇有骟动性和诱惑力的录像广告。拥挤了、骚动了、人们生活的老城开始变了模样,个个都忙于新旧交替,那时,谁也没想到老城的好处,等他们熟知的东西一件一件消失时,他们才会蓦然惊醒。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小道走,越往里走越阴凉。
可以听见剧团里有小孩子在跳皮筋,奶声奶气地喊:“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在家里数星星,马兰开花开什么花,他妈拉个屁,星星全是我家嘀。”听得我稀里糊涂,我从车上跳下来,问:“你们刚才说什么?”
“嗯……是他妈拉个屁,星星全是我家嘀。”一个小屁孩两只捧着自己的小脸蛋,扭扭捏捏,一本正红地回答我。
谁教的?太有特点了。我心想。然后说:“以后改掉吧。不好听。”
“阿姨,那改成什么呢?”这小屁孩十分认真而执着。
“他妈拉个屁不好,改……西西拉西西吧?阿姨还没想好呢,阿……阿姨?不是阿姨,是姐姐,回头想好了告诉你们。乖。”我推着车往剧团里的白楼走去。
“西西拉西西,就是拉屎屎啦!!你是笨猪猪!一个大笨猪猪!”那几个小屁孩子在身后笑我。我冲他们吐了吐舌头。
我抬头往三楼张望,黑呼呼的一屋,好像没有人存在的迹像,我回头问小屁孩:“宝贝,姐姐问一下,这栋楼住人吗?”
“住。”
“好像没人啊。”
“没人?那我们从哪里来的。”一个小屁孩问。我听这话环顾四周,的确这四周除了这栋白楼和剧院就只剩下芡草丛生了,如果白楼不住人,那些小孩子在平地里看起来就有些突兀了,可若大的庭院,只有几个跳皮筋的孩子,似乎凭生许多怪异。两棵大树并肩立在白楼的一侧,几乎要钻墙而出,那里有间窗户抹了大片红色涂料,乍看像一张褪了色的戏剧脸谱。我听到孩子们还在说:“嘻嘻,笨猪猪阿姨。”我笑笑不介意,一群小屁孩嘛。
我准备往楼上走,身后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是第一个叫我笨猪猪的孩子,摘下了口罩,露出很漂亮的小脸:“笨猪阿姨,你要去那个红屋子吗?”
“不,是姐姐。是啊。是不是住着一个好看的小哥哥。”
“不是,那里刚死了一个老画师伯伯。”
“啊?”
“阿姨你怕了?我们都不怕。老画师伯伯是个好人,他带了个徒弟,也会给我们糖吃。”
“是姐姐!姐姐!他的好徒弟住哪?”我搞不懂他们为啥老叫我阿姨。
“他一直看着你呢?呶,在那边。”小屁孩指着另一边,我看到了毛毛露在窗户口的那张清秀的脸。他似乎知道我要来,我抬头望着他,很小的一张脸,太远了,看不见,却能想像那种若有若无的、似在非在的眼神。
白楼一楼的楼道处处是垃圾,我印象中它们自我小时候起就以这种姿态存在,从未消停,人一走过,飞起绿肥的大头苍蝇,洋洋自得的晃动过度发育的身体。总归是疏于管理的垃极,只怕剧院的经营也好不到哪去。采光不好的走廊和一些蒙尘的房间,像个阴森的所在,说哪里有鬼魂只怕也有人信。二楼翻出杂碎的道具,一个坐立的白色女人的腊像悲凄的从中露出半边脸,黑眼珠直瞪瞪地盯着我,一转身又碰上木偶戏大头墩子,咧着血色的大嘴巴冲我笑,退一步又差点从楼梯滚下来,原来是一堆彩色的玻璃碎片,草,顶家常的去处搞得人鬼同途似得。我从梯间乱七八糟的道具中匆匆忙忙扭着身体上了三楼,一下子被一大床小碎花床单挡住了去路,这晒得正是好地方,正对着楼道最通亮的窗口,我茫茫然不知所措,张望着,这时,就从被风吹得起起伏伏的小碎花床单中央看到了毛毛,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落下心来,急急往毛毛那边走去。
“哈!哈哈!”一个屁孩从侧身的房间跳了出来,差点把我撞倒。
“小贝,你吓倒人家了,快撒完,撒完回来。这位姑娘真对不起,吓着你了。还不快撒,就等你洗手吃饭了。”
那个叫小贝的屁孩跑到走道对着一个超大的痰盂“嗞,嗞”的一边撒尿一边回头睨着我,我也边走边看着他,结果一头撞到了一张正在凉晒的大幅剧照木框上,那画,除了一对丰满白皙的乳房半隐在浴巾之中外,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摸着头自嘲地笑了,毛毛也在那头瞅着我笑。然后就听到楼外一大串鞭炮的声音响彻整片天空。
“过年了呢?”
“是。”毛毛只是说了声“是”,连“你来了?”这么简单的问候也没有。我蛮沮丧,不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姑且认了,哎,看到毛毛,这一刻真是怨也无力,爱也无力。我想,我这次来,只怕这一刻他也会明白我了——呵呵,也许真实的情况是:他早就明白我,是我不明白他而已。
但他却说:“你来做什么?”
啊?!把我问倒了。“我……我,不,你从没想过我会来找你吗?”我盯着他的眼睛。
“不是,不敢肯定你是不是来找我,也许,你……还有其他人要找,这里又不是只住了我一个。”他说的句句在理。
“我就是找!你!”
“那么,请进。屋子里乱,我在工作。”
“噢,工作好啊,工作赚钱好啊。”我嘟嚷着跟着他进了屋。走进去,就很自然地深吸了口气。屋里一角整齐地叠着洁白的画纸画布,地面和床都很干净,不,是屋里亮堂堂,所有东西摆放的秩序井然,连一件蒙尘的东西也没有,没用完的颜料也拧上了盖,窗边是若大的画架和一张小竹椅,常青籐倒挂在横梁处,可以马上想到“相忘于江湖”的画面,就缺莺莺鸟叫了。
我倚着窗户,能望到大片田野,暮霭色已经围拱了过来,大地的线条显得暖色很多,这地方像是故地重游一般美好。我笑了。
“你还跟以前一样。”毛毛说。
“什么?噢,你想说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傻傻地?”老实说,我并不想说话,我只想享受毛毛在身边的感觉,我在这样的想象中度过了我的大学一年级——这点我也没有意料到。更老实说,我想象中的见面,是快速相拥、快速寻找彼此嘴唇和身体的每一部分的情景。我仔细地打量毛毛,他似乎没有这种念头,我只好故作沉静地说:“你高了,而且壮了。”
“你也更……唉,不说。”毛毛欲言又止。
我随处翻翻。外面又响起了一大串鞭炮声,但估计是便宜货,打了半截没声了,于是那群小屁孩围着大叫大嚷。
我看见楼道口最通亮的那处小碎花床单处走来一个身影,是个女人,妇女,小心地往这边来了,她身后跟着一条黑狗。毛毛一喊:卡卡,卡卡。她就摇头摆尾的来了。
“找你的吗?”我问毛毛,我指的是那女人。
毛毛承认了,还告诉我不回我家过年了。
“为什么!”这声音在屋子里大的吓人,我赶紧捂住嘴,低着嗓子又问一遍:“为什么?我专门……”
“没什么。我有客人来,那是我剧团里师傅的朋友,她是来吊丧的,从上海来的。”
“噢?他是上海人吗?”
提到这个师傅,毛毛一丝不苟的脸终于挂起了笑,像海洋一样明亮,不过,这明亮瞬间即逝。
很快,进来了一个妇女,那个妇女上了年纪,但皱纹不太多,白净净的,一抬头看见我一脸疑惑,毛毛赶忙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说朋友,谁都往恋爱关系去想,她一听愈发打量我,她像是这里的主人,满脸堆笑,堆笑之后,就摸狗毛,狗很安静,只是感觉它跟人时间长了,长得也有点人样,两只弹珠似的眼睛居然闪着狡黠的光,在屋里,我很不习惯这双狗眼,像不同类的便衣密探。
“嗯。”毛毛没有反驳,抓住我胳膊拉到他的身边,我脸色一下翻红了。
“她来找你吃年夜饭吧?”
“不不,我不去,我跟你一起吃。”
我看到她手上拎了一只肥鸭和两块猪肉,于是说:“不,我只是来看看毛毛,他今天跟你过年三十呢。”
“哪里哟,我今天也有地方去啊,我这里有个老大大的朋友,我今天要去他们家过的,人家就在下面等我噻。”
我往楼下望了望:“啊!我爸!”呵,我爸插着手靠着自行车立在下面。
“噢哟,凑一起去了,我那个老大大的朋友就是你们家啊,哎呀!这下好了,我还说带些东西来让毛毛自己过年,不好意思带毛毛去,这下好啰,一起去,一起去。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她满口上海腔,钻到耳朵怪舒服的。
毛毛出门时拴好了狗,然后拉着我的手,这样子也怪舒服的。他很自然,我不自然。从三楼下来的时候,我远远地瞅着韩老师的房间,半米阳光透过几欲穿墙的大杨树打在红玻璃上,在风和叶之间晃动着,乍看有些惊鸿,倒凭生无限愁怅!韩老师是个思考力和想象力都万分强大的男人,却常常有种自我反刍的苦寒感,也是清瘦清瘦的一个人,我看和毛毛差不多都是难以随俗的那种人吧,无法或此或彼的,自己的沼泽地便要自己才挨得过去。
他却没有走过他的沼泽。他应该不到五十岁,算是早逝,那么也许没有后代吧——这事考究起来颇有些周折,我也到后来才想明白,细想起来倒在情理之中。
这个没有任何审美趣味的小县城和令人乏味的人群凭地留了一位唯美的画家,也颇令人费解,许是人世的一种匹配和筛选吧,比如被昏晦的时代打败落荒而逃的是俗人,剩下那些执着笃定的就是在世尤物了。
这些尤物却往往过早谢世。草,真不应该。
关于韩老师的回想,足足让我上溯到中学时期,那时正兴汪国真的朦胧诗,画画方面,也正值意象派画家找到“空气”——它原来也是可以画出来的——这就是意像和氛围之类的东西。一堂课上,韩老师拿出一张他自己刚画的意象画——灰色基调、几只血色的手印,他问我们想到了什么,我们说:“恐惧。”他笑了,他说:“是记忆。”
记忆?他的记忆中存在的血色手印?想着想着这些,我的脚步到了二楼,我下意识往毛毛身上凑,身边经过的那些道具和肮脏的墙壁没有一样是让人看了清爽和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