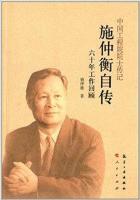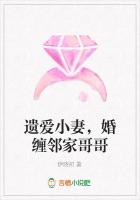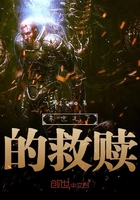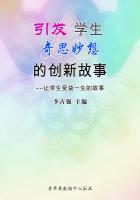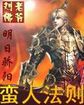甲午战败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1895年3月),中日经历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宗藩朝鲜沦于日本之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宝岛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准许外国侵略者对华资本输出……甲午战争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俄、法、英、美、德诸国紧步日本后尘,纷纷向清廷提出领土要求,攫取在华利益,抢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清王朝何以走到这一步?谁应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过去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考虑的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妥协、投降和卖国,其代表人物下是李鸿章,上是慈禧。
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甲午战败的责任、特别是慈禧的责任呢?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慈禧已归政五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准备她的六十大寿。按说战争胜负与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所共知,慈禧不但与这场战争有关,而且发挥了较大甚至极大的影响。
的确,五年前光绪亲政后仅一个月,即亲自扈从慈禧驻跸改称“颐和园”的清漪园,后来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又顶着朝野压力,按慈禧旨意将训练海军的钱挪用兴修颐和园。与当年同治修园修三海的意图一样,他们企图以梦幻般迷人的湖光山色稍稍转移慈禧对朝政的兴趣,使之乐不思“蜀”。但他们,特别是奕譞,错了。如前文所述,作为光绪亲政的交换条件,奕譞屈从于慈禧淫威,将慈禧终身对朝政的把持和最终裁决权写入了“归政事宜”条款。这些条款束缚着光绪的手脚,使之空有“亲政”之名,却不能“乾纲独断”,说到底还是个傀儡皇帝。倒是慈禧有了进退自如的余地,大权绝不放手,棘手之事则以早已归政为名让光绪顶着。为此,奕譞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郁郁死去。长期处于特定环境下而不谙世事的光绪一个人面对复杂沉重与外国交战的政局,却要每日去颐和园向“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时时贯注于紫禁城”的慈禧请安。因为凡朝中大事,“帝与大臣皆知,必须秉白而后行”。
评说甲午战争中慈禧的作用,一般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的问题;一是和战问题。
在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问题上,人们普遍以为,慈禧为了个人的享乐不顾国家安危。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慈禧竟然拿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甲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辗转扣克,到工者实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
人们指出,北洋海军有大小战舰25艘,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然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时速23海里的吉野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发展之迅速,足令欧美震惊,其世界排名从末位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早已在清朝海军之上了。对这一点,北洋海军将领无不忧心如焚。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虽是旧式水师出身,但十六年大洋上的磨炼,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不无了解(他曾数度前往欧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也多为留洋深造、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精通外语、理论、实战的世界级一流海军将领,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这些人大多不是如后来人在想象、影视中描写、丑化的颟顸官僚,而是一批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都是或战死、或自尽殉国的。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深知在大洋上作战,5分钟打1炮与1分钟打5炮,时速15海里与时速23海里的区别。慢船慢炮对快艇快炮,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打败了,无法逃避;打胜了,无法追击。然丁汝昌、刘步蟾等,却实际为以慈禧为首的腐朽的清朝统治集团枉背了贪生怕死、无知无用的骂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鄙夷和讥笑的对象。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清朝海军竟然“未购一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日双方之形势已是箭在弦上,户部却征得海军衙门同意,正式宣布,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吧。朝鲜局势吃紧时,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20尊替代各主要舰艇的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暂且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海军官兵积愤。
那么,为修颐和园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言人人殊,难究其详。据说将清漪园改建成颐和园的初期预算竟为白银一万万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而实际估计达一千万至三千万两。具体项目,人们举出,李鸿章与奕譞以所谓“建军祝寿”,在颐和园万寿山修建工程中挖“昆明湖”,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共计二百六十余万两,存于天津洋行生息。“本银专用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其余息银、捐输二款,另款存储,专备颐和园工程之需。李鸿章与奕譞强调,今日颐和园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师操各处”,就是慈禧七十大寿之年,皇帝身率臣民祝寿胪欢之地。这“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兹得诸臣急公济用,相助为理,不惟海防足恃,腾出闲杂各款专顾钦工,亦不敢有误盛典”。当时持反对意见的官员屠守仁、吴兆恭、林绍年等,或革职永不叙用;或交吏部严加议处;或外调出京。下页为相关两表:
另外,醇亲王奕譞还倡导百官“捐俸”四分之一效忠太后等。然近年来,清史专家王道成等教授认为,慈禧太后并没有挪用那么多的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对海军建设影响不大。
首先,光绪九年(1883年)清廷并未为海军筹款三千万两,终光绪一朝也未曾有过这样的事;光绪元年(1874年)规定北洋、南洋海军每年各四百万两的经费,从来也未全部兑现过。有时“仅及原议拨四分之一”,有时“大半无着,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即便全部挪用,也不足人们印象之数。
其次,颐和园为海军衙门承修,经费也为海军衙门筹措,但并不等于海军经费全部或大部均用于修建颐和园。从史料上看,修建颐和园的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从海军军费中拨给。据总理海军事务的奕譞、奕劻等的奏折,如海军经费每年果能全数拨给,则可勉强支撑,腾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费用大约在每年二十万两左右,但这是他们的设想,有无实行,目前没有史料证明。二、海军巨款息银。即上述李鸿章与奕譞以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实是“筹银”)、存天津洋行生息的银两。时两广认筹银一百万两;两江认筹银七十万两;湖广认筹银四十万两;四川认筹银二十万两;江西认筹银十万两;直隶认筹银二十万两等,称“海军巨款”。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至十八年三月解往天津存入洋行生息。至甲午战前,这笔“海军巨款”本金一直未动,息金数额及颐和园如何动用史料未载,按上表累计本银一百多万两,息银三十多万两,可供参阅。三、光绪十五年后的“新海防捐”垫款。所谓垫款是要由上述“海军巨款息金”归还的。“新海防捐”每年约收一百八十万两左右,为颐和园垫了多少,后来还了没有,不得而知。从现在保留的颐和园算房56项工程(占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二)工费料费三百一十六万六千余两估算,颐和园工程修建经费大约在五六百万两白银。
再次,颐和园修建经费所花费的这五六百万两白银,是光绪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86年—1895年)间陆续支出的。而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奠定规模,大小舰船25艘全部于光绪二年至十四年(1876年—1888年)间购置。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没有添置舰船、装备海军,并不等于就是为了修颐和园。当时清廷财政困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深刻,李鸿章等是以湘、淮军起家,代表地方势力进入上层的实力派,不能不受到多方猜忌。他曾大发慈禧的牢骚:“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实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云云。慈禧限制北洋海军发展另有深意,不能简单归结为修造颐和园。
但是,慈禧个人的生活享乐,确实对甲午战争的进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这就是她的六十庆典。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寿。按中国传统,六十为一个甲子,非寻常生日可比。故此慈禧非常重视,两年前即成立了“庆典处”,专门负责庆典事宜。除了准备在颐和园举行盛大典礼而大兴土木之外,还准备仿照乾隆为皇太后祝寿的方法,在从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所经跸路分设60处景点,建造各种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每处用银四万两等。另江南、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特造彩绸十万匹,粤海关监督采办足金一万两供庆典之用。慈禧六十庆典成了当时清朝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连发动战争的日本侵略者都看到,“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庆典加紧筹备之时,中日战争爆发。而当有人提出撙节庆典费用以供战费所需时,慈禧怒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必令彼终身不欢!后清军接连失利,黄海之战北洋水师严重受挫,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慈禧不得不停办颐和园受贺事宜,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六十岁生日。但仍奢华已极,九月二十五日全国各地开始呈进万寿贡物,十月初一庆典正式开始,十七日结束,其中唱戏三天,前后将近一个月,共用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当时户部给前线的战争筹款却只有二百五十万两,不足庆典一半。史家叹道,如果当时没有慈禧六旬庆典,全国上下全力对日作战,战争结局或许全然不同。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慈禧有如下一段强词夺理的台词:
“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观众听着刺耳,知道“其实这都是编剧的话”。但,“好家伙,按这逻辑,硬是把挥霍浪费、奢侈摆阔的陋习上升到了爱国爱民、为国争光的高度”。他们联系现在的社会现象——一些地方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上级领导到某地检查工作,当地领导要到县界、市界迎接,而前一地方的领导则要送到县界、市界,往往还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有一市长访美,有关部门隆重送行不说,还特地要求美国方面安排少女献花,夹道欢迎。甚至一个乡长调任,也要组织几十辆汽车、几百人的送行队伍,理由是“工作需要”、“争光”;不这样做,“没面子,没威信,外人瞧不起,不好开展工作”等——从《走向共和》里慈禧的逻辑找到了根据和根源。
十年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又过七十大寿。章太炎作了一副对联,如下: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明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在和战问题上,人们以光绪为主战派;以李鸿章为主和派;认为慈禧起初主战,后来转而支持李鸿章主和。
光绪主战,十分鲜明。就在清廷筹款、造园,为慈禧六旬庆典举国奔忙时,甲午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役打响了。早在明治维新时日本侵略者就已制定了首先征服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侵占中国的战略方针。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本以为时机到来,以清韩宗藩关系为由怂恿清朝出兵朝鲜:“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并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清廷得到日本保证,应朝鲜要求出兵牙山。日本则以保护使馆及侨民为由派大量军队从仁川登陆,占领朝鲜京城汉城。东学党起事平息后,清廷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日本不予理睬,并不断挑衅、制造事端,战争一触即发。对此,光绪主张坚决回击。他给李鸿章的上谕道:“现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庸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击沉了清朝增援牙山的运兵船“高升号”。二十七日又向牙山的清军发动猛攻。七月初一,清廷向日本正式宣战。同一天,日本对清廷宣战。然而清朝主持前方战事的李鸿章采取保存淮军实力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俄、英等国的调停上。光绪则明确表示,“不宜借助他邦”,要以本国军力战胜日本。但他没有实际经验,不了解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所指定的作战方案含有不少空想成分,加之清军武备废弛,指挥失当,结果“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然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日军攻陷旅顺,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迫不及待要求议和,不惜割地赔款时,光绪仍表现了鲜明的主战态度,对作战不力、贻误大局的李鸿章严加惩处,“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告诫他“旅顺既为敌据,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可往来无忌………敌兵扑犯,必乘我空隙之处,威海左右附近数十里内,犹为吃紧,着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巡逻,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