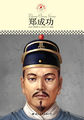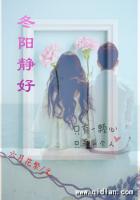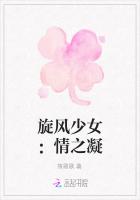慈禧开始亦主战。这与她一贯的思想和做法是一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到惨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决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即将出发的时候,时为懿贵妃的慈禧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触怒了咸丰,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后奕訢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曾劝咸丰废约再战,因咸丰病危作罢。此次战争初期,慈禧与光绪一样估计不足。光绪事事均请示慈禧,慈禧的态度主战无疑——光绪对诸大臣说:“朝廷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也主战”。中外舆论也认为,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在慈禧看来,蕞尔岛国小寇不堪一击,不待时日便可一举荡平。然随着战场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慈禧由主战转向主和。这倒不完全是战争教训了慈禧,使她变得实际了一些;也不完全是担心战火将波及清朝龙兴之地盛京。促使她转向主和的决定因素有二,一是旷日持久的战事,势必影响她的六十庆典活动,一是帝党的形成。其中第二个因素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甲午年中日开战前后,围绕着“主战”,光绪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整顿军机处;一是筹措巨额战费。如前述,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与奕譞合作发动“甲申易枢”,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平庸的礼亲王世铎及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等人。面临战争,这个班子明显运转不灵,难担重任。光绪果断任命主战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务,军机处重要事宜都须与翁同龢、李鸿藻协商。战争爆发后更直接授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后又鼓动词臣上书,吁请十年前被罢黜的奕訢重新出山,使奕訢得以“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在内廷行走”,尽管他已耗尽当年与慈禧抗争的锐气,“久之乃竟不足恃”。而汪鸣銮、志锐、文廷式、李盛铎等锋芒毕露的台馆之臣开始聚集在光绪麾下。他们还对慈禧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等发起猛烈攻讦。指斥孙毓汶在“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独“怏怏不乐”,说“皇上为少年喜事者”;指斥徐用仪性情柔猾,与孙毓汶狼狈为奸,要求将二人立予罢斥,逐出军机。在筹措巨额战费的过程中,光绪一度停了颐和园工程。他周围的所谓“帝党”,仰其旨意提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为此娱目骋怀,似与哀惧之意相背,将何以申警将士,振发庸愚?”要求将“所有点缀景物,一切繁仪,概行停止”,“停办点景,移充军费”。在慈禧看来,改组军机处,那是夺取她控制朝政的大权;停建颐和园,那是藐视她的存在,触犯皇太后至高无上的尊严。
八月,平壤之战,清军失利,左宝贵等将领壮烈牺牲,统帅叶志超一夜狂逃三百里,仓皇渡过鸭绿江退回中国境内;黄海之战,中日战平,邓世昌等壮烈殉国,中方损失4艘战舰,李鸿章抛出所谓“保船制敌”的方针,命北洋水师全队避入威海卫港内,不准出港与日军交战。慈禧终于站到台前,公然干预光绪的执政了。
她先发懿旨,表示今年庆典仍在皇宫举行。而后连续召集重臣会议,提出议和,派翁同龢赴津要求李鸿章设法媾和。每次会议,光绪支持的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与慈禧支持的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等均发生激烈争执。慈禧索性抛开光绪,通过奕訢、李鸿章两条线加紧开展调停、议和活动。与之同时,她痛下狠手,教训光绪、整饬后宫、打击帝党。于是发生了前述珍妃一案。十二月,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本求和,翌年(1895年)正月初抵达日本。时日军正在准备进攻威海,决定彻底消灭北洋海军、给京津造成直接威胁后再谈,以进行最大限度的勒索,遂照会清廷,以张荫桓非全权特使、官秩稍低为由不予接待。慈禧当即议和的愿望没有实现。十八日,日军攻陷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朝派出李鸿章乞和。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在日签署的《马关条约》文本送到北京,须由光绪“用宝”(签押)后,再送往山东烟台与日本换约。这是从未有过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赔偿军费二万万两;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日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等。消息传来,举国震动,“章奏条陈,流涕谏阻,市肆行人,聚谈偶语,咸惴惴惧和议即成,臧获仆隶,皆裂眦切齿”。外省封疆大吏钦差大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棠、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嵩、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以及陕甘总督、陕西巡抚、署理山西巡抚、广东巡抚、盛京将军、吉林将军、署理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等大员纷纷致电、上奏坚决反对;京官据不完全统计,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大员10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50余人(次),没有奏事权的低级官员达575人(次)之多;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上书反对签约,都察院一天即转递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7省举人公呈8批,签名者311人,“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一时间,“拒和迁都,毁约再战”的呼声震撼朝野、震撼人心。二十九日,光绪如常召见军机大臣。孙毓汶将文本呈给光绪,称:无论如何应在今日批准。光绪说:条约要割台湾。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称:前线屡战屡败,如不签约,倭人将犯京师,奈何?光绪大怒:此约关系重大,汝欲逼朕签约不成?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不料,慈禧称病闭门不见,在这个时候又做出“已归政”的架势,冠冕堂皇地说:“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光绪“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四月八日,光绪最终颁谕批准《马关条约》。回到读书的毓庆宫后,光绪与师傅翁同龢“战栗哽咽,相顾挥涕”,痛不欲生。十天以后,光绪下令大小官员一律到内阁观看他的一篇朱谕。这是他对战败的交代。他字字血泪地说,嗣后“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勿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他只说要增强军事力量,他没有说和约的签订是因为慈禧已“意有所归”。
戊戌政变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生成。这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等,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仕宦家庭,以理学传家。光绪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戊戌变法前后,他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并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其后思想日趋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一岁成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后师从康有为,先后领导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共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并著《变法通议》,倡导变法,时人将之与康有为并称“康梁”。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变为狂热的保皇党徒,以立宪派领袖自居,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论战。不久从维护帝制转向拥护袁世凯。而袁世凯称帝,他又策动蔡锷倒袁。在护国战争中,他作为进步党领袖,以康有为“复辟帝制”,同其公开决裂。
康有为熟谙西学,洞察外情,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尚属一介布衣时即曾伏阙上书,发出危机存亡的警告。他甚至预见到,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六七年后中日必将一战,战则中方必败、必致辱国丧权。他的预言在六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变成了现实。当年康有为的上书到了翁同龢手中,但翁同龢胆小没有上达光绪。甲午战争失败后,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进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子,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用一天两夜,赶写万言书即《第二次上清帝书》,力言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举子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者数百人,据说签字的有一千几百人,虽经主和派派人到各省会馆恐吓举子撤销签名,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而保留签名,遂联名交都察院代呈,史称“公车上书”。而呈递都察院的当天,光绪已在《马关条约》上盖了玉玺,都察院拒收了那份万言书。举子们的上书只在坊间刊刻流传,未能径达光绪御览。光绪看到的是康有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递上的所谓《上清帝第三书》。整个奏折长一丈多,共一万多言,书中有: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为未迟。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尚可振衰起弊,救民救国。“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整理;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强大,孰轻孰重可以辨之者。”“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书中详陈变法图强的方略,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严惩主和派与战败者,破格起用新人,变法图强,练新军、选新将、用精械,筑铁路、开矿山、建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革官制等。这些闻所未闻的精辟论说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了光绪的目光,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痛创后的光绪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存记,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时时展阅。后光绪在朝臣章奏中发现了不少类似章奏,遂命军机处将康有为等九个条陈发到各地督抚将军处讨论。并下谕道:“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疾,力行实政为先。迭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这已是变法改良的先声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之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俄、英、法、日亦虎视眈眈,伺机瓜分中国。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心头。康有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指出:“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上,省括即发,海内惊慌,乱民蠢动”,中国“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切。这封上书也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燮为此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法的意见,并诏令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等书,且可上奏言事。康有为遂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12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治。光绪谕令王大臣会议,王大臣请得慈禧“尽管驳议”的旨意,逐条驳回。康有为于是转而鼓动群众性的变法运动。他怂勇御吏李盛锋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政治性团体保国会,京师士大夫数百人参加。在此前后,并成立了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各会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益浓厚。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
光绪拟要实行的变法维新,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就其触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和传统的“祖制”而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个政治家,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种政治势力会有清醒的认识,会预先考虑到变法维新将会遇到怎样的局面,出现各种情况时应如何应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证方能付诸行动,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如没有把握就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但光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被慈禧造就出来的有严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轻书生。他的一切思想认识,包括仅有的一点自信都是从读书中得来——他读到《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新政记》等书,如获至宝,又“大购西人政书览之”,“考读西法新政之书,日昃不惶”,对中国的现实和官场则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准备不足,却急欲有所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亲信荣禄私下活动,打算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连,号召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后党逼光绪退位的举动,使光绪忍无可忍,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地付诸行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中有:“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试问近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宣布了变更旧法,博采西学,发愤为雄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