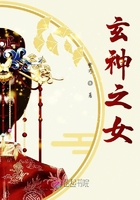这就是所谓的“族长们”了?实在是太可笑了,出云心想,大庭氏开会的时候那屋子里可满满当当都是人,各族族长的陪同还只能乖乖站到外面去等;反观这共工氏,稀稀拉拉就坐了三个,倒还不如大族长的家人多。
难道共工氏已经衰弱到无人来投靠了吗?
前方的伊歧勉强冲着出云和附宝慈爱地笑了笑,但转瞬间又皱起了眉头,附宝似乎见惯不怪了,拉着出云在孟春那边依次坐下,小乙领着狼站在孟春身后,对面的三个族长不约而同地抬起眼来盯着出云上下打量,瞥了她几眼,倒也没说什么。
各归各位后,一个族长翻着白眼不耐烦地说:“宗长大人有什么话快说吧,我还要赶着回去弄庄稼的事儿呢。”
初来乍到的出云被这种理直气壮的以下犯上给惊了,她早已听说过和见识过伊歧的无能软弱,却不料他无能软弱到这样的地步上。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耻辱,”她遗憾又愤怒地想,“我竟然有这样无能的父亲!”
帝鸿戏谑:“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我会去找一个大陶罐,一根麻绳,一把石刀。我用石刀先在目无尊上的人的脖颈上环绕一圈,再用麻绳把他们倒吊在树上,脑袋套进陶罐里,让他们的血不断地流进去,然后淹死他们。”
帝鸿赞赏地笑了:“看了伟大的出云并不是一个仁慈的长母。”
“开什么玩笑,”出云对于这个赞赏颇为受用,“巍峨浩大的大庭氏可不是靠着仁慈屹立到现在的。”
看看曾几何时不可一世到连上子女娲都头疼的共工氏吧,靠着一颗仁慈的心,堕落到几乎快要消亡。
伊歧脾气好到不可思议,居然还可以耐着性子与下属商量:“再等一等吧,还有好多人还没到呢。”
另一个族长气呼呼地哼哼:“有什么好等的?他们都在为自己部落里战死的男丁举行葬礼,来不了了。这些年来各部落被逼送出了多少个男人,连族长们的儿子都通通送到了大庭氏的战场上,我们听说打了胜仗,欢欢喜喜地等着他们回家来,结果呢?昨天一个都没回来,现在各族里连几个像样男人都没有了,难道要派个女人来参加会盟?”
大庭氏遗孤的身份此刻真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出云十分懂事地低头沉默,尽量只把自己当一个装饰品。
伊歧面有难色:“这都是因为战争……”
“大庭氏跟赫胥氏的战争,管我们什么事儿?”首先发言的那位跟着发起了牢骚,“现在人没几个了,例行的供品却要更多,今年虫灾泛滥,成片成片的蝗虫跟乌云似的罩在田野上,庄稼都没了,我还以为把我们叫过来是要举行祭天消灾的仪式,结果就这么傻坐着,有什么用呢?!”
熊泉抬头向天道:“那蝗虫就是上子对我们祭祀太少的惩罚。”
附宝柔柔弱弱地说:“可是我们的祭品实在不够呀。”
出云忍不住开腔:“晚上在田坎上多搞几堆火就好了呀。”
一整屋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瞪了她一眼,孟春的那个尤其凌厉。其实出云出口就后悔了,毕竟满屋子都是一群满脑子只想靠上天保佑来过日子的男人,他们哪里懂得自力更生人定胜天的道理呢?
只有对面中间那个一直闷着不说话的族长这会儿抬头盯了出云一眼,他没说话,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闪烁着意义不明的光,满额头的褶子又深又多。
伊歧满头雾水:“什么供品?我们不是已经取消上供了吗?”
一直默不作声的孟春轻轻开了口:“不是给我们的,是给尊卢氏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看也没看父亲,语气满是对伊歧的愤懑。
“什么?”伊歧惊异道,“为什么要给尊卢氏?”
“因为我们参加了战争!因为赫胥氏要求我们为战争提供更多的男人和粮食!可我们哪儿有那么多的男人给他们?我们连十岁的男孩都送到战场上去了!我们伟大的上级部落赫胥氏就让我们用粮食去代替,我哀求遍了所有的部落,只有好心的尊卢氏愿意借给我们粮食。”孟春像被点着的雷火,狂躁而激烈地向伊歧吼叫。
“好心?”族长们哼声冷笑,“说尊卢氏好心,就像说老虎温柔一样。尊卢氏借粮的条件是我们向他纳供,夏冬两季都要纳,每次都是当初借粮的量,一直到当初借粮的十倍为止。”
看来这场战争还真是规模不小,不管是赫胥氏、尊卢氏还是共工氏,几乎都是倾尽所有。反观她们大庭氏,以一敌百还打得轻松自如,生产生活什么的一点儿都没受影响,想来若不是那场浩大的地震和海啸,就是大庭氏不使劲去打他们,也能把赫胥氏引领下的整个父系部落群给拖垮。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呢?”伊歧地问孟春,急切的语气中似乎有些责怪的意思。
族长们挤眉弄眼地讥笑:“她不仅答应了这个,还答应嫁给尊卢氏巫觋的儿子呢。”
孟春怒目而视:“若不是我嫁给熊泉,你们现在已经被关在赫胥氏的奴隶窝里,被割掉舌头没日没夜地干活儿了!”
族长们白眼翻到一边去,似乎对孟春如此伟大的自我牺牲并不领情:“那是你们共工氏的战争,本就与我们没关系,却把我们拖累得半死不活。”
出云一双眼睛贼溜溜地在几个人身上晃来晃去,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他们好像在内讧。”她兴奋难耐,忍不住要跟帝鸿讨论讨论。
帝鸿与她心有灵犀:“内讧就好,怕的就是他们团结一致。”
“没错,”出云开开心心地说,“最好斗个你死我活,这样我回空桑的机会就更多了。”
伊歧受惊不小,看看孟春,又看看熊泉,瞠目结舌:“我以为……以为你们是互相爱慕上了……尊卢氏的人说你们见面后自己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