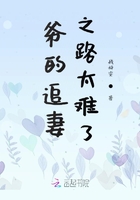構成歐洲文明的混合體是個不穩定的組合。雖然它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整個中古世紀,一千年左右,但組成元素之間並不調和。時至西元一四○○年,這個混合體開始分崩離析,它的分裂首先始於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常被描述為古希臘羅馬學術的發現或再發現。不過,這並不是說這些智識成就曾經遺失而今重新被找回,雖然當時確有若干新的發現問世。它的改變在於不再使用古代知識來支持基督教會的神學,而是有許多學者,主要是在教會體系之外,嚮往希臘和羅馬在創造這些知識時的世界樣貌而意圖擬造。他們希望像古代藝術家那樣創作藝術,希望建造出類似他們的建築、跟他們一樣讀寫拉丁文、所思所想俱與他們相同。他們想回到過去那個非基督宗教的世界──但這樣的世界已被教會藏匿起來,因為教會只把這些知識利用於遂行自己的目的上。
這也是一個比較「入世」的世界。古典時代之前的人對死後的生命其實沒有那麼看重,對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為關注更多,他們對人的力量和能耐歡喜擁抱,不會滿腦子想的盡是人的邪惡墮落。文藝復興學者現在進入了一個思想奔放的世界。怎樣生活最好、想些什麼最好,古代哲學家和道德家早就百花齊放,在觀點上百家爭鳴,但他們的辯證和推論並沒有被傳承下來,因為基督教會已經為人民的思想緊緊裹上了束縛衣。
文藝復興的古典主張
不過,文藝復興學者並沒有直接攻擊基督宗教。他們的個人態度或有不同,但大致上對基督宗教採取的觀點頗類似於古人的宗教觀,那就是:宗教是個基本的存在,大體而言是件好事或者說有存在的必要,只是世界上還有更多的事情值得關注。宗教不該箝制生活和思想的一切,而這正是教會一貫的目的。這樣的箝制一旦被打破,歐洲的思想反而變得比過去更大膽開闊、天馬行空。
隨著文藝復興來到,歐洲社會開啟了它漫長的世俗化過程。在世俗的世界裡,宗教可以存在,但是屬於私人事務,或是一群人受到某些信念所吸引的結社團體──就像我們今天的世界。宗教不能左右社會,不能強制每個人遵守規定和儀式,也不能宰制思想。
文藝復興的結果是,身處於某種文化和傳統的人,靠著思想讓自己邁入另一種文化和傳統。一旦跨過這條分界線,你就永遠不一樣了。任何東西都不再是不變的。歐洲的思想家們震撼於文藝復興時期所帶來的衝擊,而這並不是它最後一次發生。
最開始把希臘和羅馬年代稱為古典時代的,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古典在此處意謂著經典、最優,例如我們說經典的接球、經典的演出,是種無法超越的精采。他們相信,古人在文學、藝術、哲學和科學方面的成就一直無人超越,未來也無可超越。至於他們自己,能夠庶幾近之也就不錯了。如此這般,歐洲這個組合體就因為「文藝復興」的這個訊息──古典的東西是無與倫比的──受到了干擾。
西方人現在計算年代的方法是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準上,這不啻是代表:這個文明的本質是個混合體。制定西元年份是從基督誕生的那年起算,這表示西方人依然承認自己是基督宗教文明的一部分。AD是拉丁文 Anno Domini的縮寫,意思是救世主出世之年(事實上耶穌並非誕生於西元元年;生於西元前六或前四年更為可能。)不過,我們把時代劃分為幾個紀元──古典、中古、近代,就跟基督宗教毫無關係了。這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觀點,意指古典世界已臻於完美的顛峰,之後人類逐漸偏離了正道,就此跟寶貴的遺產失卻了聯繫。這段「暫停」期間就是所謂的中世紀,也就是基督教會在智識和社會生活上達到全面操控的時期。因此,古典時期、中世紀和近代的區分,和基督宗教是不相干的。
行動像天使,悟性像神明
有三件雕塑作品可以顯示古典時期、中世紀和近代這三個進程的轉折(見下頁)。第一件是一尊古希臘雕像,留存至今的希臘原始雕像屈指可數;我們今天看到的通常是羅馬人的複製品,品質很難和真跡相比。這尊雕像出自普拉克希特利斯(Praxiteles)之手,雕的是赫米斯(Hermes)握抱著嬰兒酒神戴奧尼索司(Dionysus)。人體是完美的,這個觀念是希臘的發明之一。一如藝術歷史學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言,裸體像和裸露的身體是有分別的。裸體像本身展現的是豐富的力與美,它是一種恰到好處的狀態;裸露的身體就只是沒穿衣服而已,而且因為沒穿衣服而顯得自曝其短。
當然,大部分的男體看起來並不像那尊雕像;希臘人的目的不是要展現哪個人的軀體,他們的用心是從人體中找到完美,並且利用數學算出至為賞心悅目的比例和線條。
第二件雕塑作品呈現出中世紀的人體觀。這是德國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堂大門上的人物畫,它刻劃的情景,是亞當和夏娃吃下了上帝告誡他們不能吃的水果。亞當在責怪夏娃,夏娃在責怪毒蛇,兩人都為自己的赤身露體感到羞愧,拿手遮遮掩掩。
這明顯不是裸體作品,它們是基督教義的具體展現,表示身體是邪惡的,是罪惡的根源。
第三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作品,他將自己投射為希臘古人,重拾他們對裸體的概念。他所雕刻的大衛像是公認的完美人類形貌;人類是尊貴、高尚和美的化身──一如哈姆雷特所形容:「行動多麼像天使!悟性多麼像神明!」
從裸體作品到罪惡的赤身露體再回歸裸體作品,可以代表古典到中世紀再到近代的意涵演變,而這正是文藝復興對它本身的理解。
耶穌早就警告過……
文藝復興是中世紀世界的第一個重大衝擊,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是第二個,這回是對基督教會的直接攻擊。宗教改革的目的,是要基督教會回復到尚未羅馬化之前的樣貌。我們說過,基督教會因為跟著羅馬帝國一起成長,各種特性深得羅馬真傳;在羅馬帝國滅亡後,教會的教宗依然屹立,地位儼然君王一般,而各教區的主教和大主教,也猶如古羅馬帝國的行政百官,轄下更有不計其數的地方神父教士。這個聖職體制不單有自己的法律、刑罰和監獄,還有自訂的稅收制度。
教宗和主教團掌理著整個教會,教義也由他們制訂。教會可以給你救贖,可是必須透過它所掌握的東西來運行。你要得救,非得靠神父和主教不可。你必須領聖餐、參與彌撒,還需要神父替你變魔術,把麵包和酒變成耶穌基督的血和肉。你需要神父聽你懺悔,賜你寬恕,教你如何贖罪。神父可能要你唸百遍千遍的聖母瑪利亞或指示你去朝聖,或者如果犯行重大,會要你到聖壇之前乖乖接受鞭笞。如果你是有錢人卻快死了,他可能會斬釘截鐵地告訴你,除非你把大筆財富留給教會,否則你進不了天堂。
在中世紀,大部分的神父、主教和大主教加入教會,並不是因為宗教情懷或特別虔誠;他們加入教會,是因為它是當時最龐大也最有錢的組織。領聖職就跟今天你去當公務員、進大公司、進政壇或進大學沒有兩樣,可能是為了一份穩定的差事、有興趣的工作或高薪,也可能是為了吃香喝辣、施展權力。在教會裡,你有得是機會撈油水、發橫財,還能替親戚朋友謀職找事,讓他們雞犬升天。
可是,這個巧取豪奪、富有又腐敗的組織,卻也是耶穌教誨以及早期基督徒言行紀錄的保存者。耶穌和他的門徒出身卑微,如今教宗和主教們卻高居於廟堂之上。耶穌早就警告過擁有財富的危險,而早期基督徒聚會都是在自家或別的信徒家裡。《聖經》上對這些都有明文記載,因此,教會保存的聖典文獻若是落入了反對基督宗教的批評者之手,很可能會變成引爆的炸藥。
那麼,教會是靠什麼手法,可以避開這種破壞性的批判這麼久?
馬丁路德之時勢英雄
由於《聖經》是以拉丁文書寫,極少人能夠閱讀。教會說,它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解讀《聖經》的權責單位。任何人要是利用《聖經》去批評教會的訓示或作為,就會被當成異教徒綁在木樁上燒死;換句話說,你要是非信徒,不但會害了自己,對基督宗教也會造成威脅。可是,到了十六世紀,有個「異教徒」卻逃過了一劫,他的名字是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是個修士,對自己的宗教非常認真。他對自己的救贖充滿煎熬:「我,一個滿身罪惡的人,必須怎麼做才可能得救?」一天,他讀到《聖經》中保祿寫給羅馬教會的書信,頓時豁然開朗。保祿說:「你只要相信耶穌基督就能得救。」馬丁路德從這句話裡做出推論:「你根本不必做任何事就能得救,尤其不必對神父的指示言聽計從。你只要相信上帝、抱持信仰就行了。」
「光是信就能得救」,是路德教派的中心教義。只要相信基督,你就能得到救贖。當然,作為信徒,你會樂於去做讓上帝高興的事,一如教會所說,要行善積德,去做一些耶穌說我們該做的工。可是,行善積德本身並不能幫助你得救。
這是新教和天主教教義的基本分野。羅馬天主教強調,行善積德是得救的一個過程;朝聖、施捨錢財給窮人,都有助於你的最終目的──與上帝同在。但馬丁路德說不是這樣的;就憑我們,渾身罪惡又腐敗的我們,哪有可能做出什麼讓上帝高興的事情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崇信上帝,而只要我們崇信祂,上帝就會讓我們得救,這是祂做過的應許。
這算是一種反求諸己的宗教;馬丁路德說,羅馬教廷花了幾世紀建立的一個龐大機制,根本毫無必要,但羅馬教廷對這個觀點並沒有虛心受教,教宗駁斥了馬丁路德對教會的批評以及他對救贖的新見地,而馬丁路德也強烈譴責教宗作為回覆。
「這人以為他是誰啊?他告訴我們,他是耶穌基督在世間的代表,但他其實是耶穌的敵人,是個反基督之道而行的人。他過著奢華的生活,頭戴著三重皇冠,你來到他面前必須親吻他的腳趾頭,要行動還得僕人高舉過肩,而我們從《聖經》上知道,耶穌基督都是靠著兩條腿行走四方。」
《聖經》,是馬丁路德據以批評教會的關鍵。如果《聖經》上沒寫的,教會就沒有理由去堅持或執行哪個訓令。《聖經》是唯一的權威。和羅馬教廷決裂後,馬丁路德第一件事就是把《聖經》翻譯成德語,使得人人都能閱讀、成為自己得救的主人。
宗教改革運動,是以《聖經》的訓示和教誨為據,對羅馬教廷進行改革的運動。它希望重塑早年的教會生活。宗教改革所帶來的訊息是:基督宗教並不是羅馬人的宗教。
由於異教徒必須受火刑燒死,馬丁路德是如何逃過這個劫數的呢?有好幾個原因。第一,拜印刷術發明之賜。馬丁路德對教會的批評和譴責立刻被印成文字,傳遍了整個歐洲。馬丁路德開始抨擊教會之時,印刷術還是個新發明,問世不過五十年;教宗要打壓馬丁路德的計畫還沒成形,他的大名已是人盡皆知,每個人都在拜讀他的批評文章。在過去,也曾有許多異教徒在一國之內帶領著一小撮跟隨者,但馬丁路德不一樣,他很快就擁有了大批隨眾,國內國外都有。
馬丁路德攻擊羅馬,日耳曼一些王侯見獵心喜,是他能倖免於難的另一個原因。當時的日耳曼民族並不是一個單一國家,它是一個由許多小國組成的邦聯。羅馬教廷在日耳曼的影響力要大過對英國、法國,這即是部分原因──英國和法國是統一的國家。在日耳曼,教會握有廣大的土地,有些地區甚至佔據泰半;剝削人民、聚斂錢財不說,各教區的主教也由教宗任命,這些王公貴族全無置喙餘地。若是跟著馬丁路德走,他們便可佔據教會土地,任命領地內的主教,對羅馬停止金錢捐輸,於是,這些王族成了馬丁路德的保護者,並在領土內廣建路德的新教教會。日耳曼民族有一半的土地都設有新教教會,路德派教義也從現在的德國北傳到了瑞典、丹麥和挪威。英國則是創立自有的新教品牌,稱為英國國教。
兩派人馬從相殘到相容
羅馬教廷的敵人很快就變得不止一個。新教教會的形式不一而足,因國家而異。它們在自己的國家裡自給自足,建立起一系列教會,天主教會則是個跨越多國的龐大組織。平民百姓在受到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者鼓勵而自己閱讀《聖經》後,不久也從中找到批評馬丁路德的理由。在宗教改革運動中,由於再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威去詮釋《聖經》、監督信仰,新教會不斷增設,也不斷被淘汰。
一百多年間,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就這樣互相攻伐,甚至不惜兵戎相見。兩方都認為對方大錯特錯,都不認為對方只是不同種類的基督宗教、甚至不只是非基督宗教而已,而是以反基督、真正教會的敵人視之,唯有另一方被消滅,真正的教會才能存續,這種認可殺人的教義引發了屠殺──與其讓天主教徒或新教教徒去傳揚一種完全牴觸上帝的訓示,而使得祂在世間的教會受到傷害,不如把對方給殺了來得好。不過,在互相殘殺、誰也沒勝過誰的百餘年後,兩方終於達成長期的休兵協議,包容的觀念也逐漸成形。
首先,雙方同意某些國家可以信奉新教、某些可以信奉天主教,接著──這是一大躍進,同一國裡不同的基督教派也可和平共處,雖然一開始,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對這個可能性都不敢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