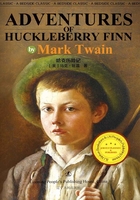也许,刚才不过是幻觉?不得已,我起了身,走进客厅,果然不见人。走到阳台上,却听到玲玲“咯咯”的笑声,只见她正跟楼下边的小孩子逗得欢,一条小辫还让个小孩抓散了,散了个满脸,满脖子弯的。这丫头,成心是想气我,不时抬起头,冲着我笑一阵,又低头逗小孩去了!这回,轮到我去找她了。我下了楼,到了她的身边,她把小孩塞到我怀里,拔腿又要走,我只好叫住她:“玲玲!”“有什么事呀?”她象个陌生人一样地问。我却怔住了,不知怎么说好。“没什么事哇,那我上街玩玩去。”“不不,有事。”我只好说。“什么事?”“给你讲件平反中的事,我想你会感兴趣的。”“听多了,没什么兴趣。”“这个特殊,听完了再发表意见吧。”玲玲这才站住了:“那我就听听。”其实,我能有什么话,不过是想拖住她。一转念,还是讲起一件刚处理完的事来。就在一个百货店,小百货店,一天午睡时分,钱柜里少了四十多块钱,晚上盘底,售货员急了,忙告诉领导。查来查去,查不出钱来,更不知去向。
反映到上级,正好,七七年双打运动,抓到了典型,于是,双打工作队穷追猛打,终于促使这个售货员交代了一千多元的贪污案子,送到了牢里法办。可在牢里,那售货员遇上了一位小偷,小偷有闲没事,讲起他一次用竹子吊钱的事,他把大头钉扎在竹尖上,趁午睡时分,从柜台外伸进去,扎了两次,一次扎了一张十元一张五元和几毛钱,一次扎了两张十元和一张五元,总共四十多元。售货员一问,正是自己的店里,便诉说起自己怎样因四十余元掉失而成了个千字号的贪污犯。
小偷听了,也算是良心发现吧,立即向公安部门交代了这一起案子--对于他来说,四十多元,只算是起小案子。售货员便立即打了申诉报告。公安部门还算认真,说,就算是千字号,还不一定够得上判刑案件,何况有出入,所以,便把那售货员释放了。但是,单位领导却一直不给这售货员安排工作,说他已被开除工职,不能回来了。原因是公安局抓去过。为什么被抓?他们说不管,再说,出来时工作队也撤了。就这样,那位售货员,一分钱也不曾挪用过,却一直在外面告状,整整两年光景,直到最近才解决。当时,我训斥了那位单位领导一顿:“小偷都良心发现了,整整两年过去,可你们连小偷都不如!还当什么共产党的干部!”我还没说完,玲玲却打断了我的话:“爸爸,你有什么资格训人家?”“怎么?我训的不对么?”
“可是,你还记得么?耶枚骂过你们,说你们比她,一个堕落过的女人都不如,是么?”“……”“你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白你自己,爸爸,对不对?你默认了。我承认,落实政策,中间的阻力很大,而你几乎是被他们包围起来了,在他们看来,你平反得太多了,是一风吹!当然,他们正面不敢这么说,而是捧你,说你把所有该平反的都办了,弦外之音是说,不该平反的你就不用去管。是么?而你也津津乐道。为什么群众把这类事看淡了,失望了,唤不起热情来,甚至对有名的大人物平反也无所谓,这也是一个原因,也许还是一个次要的原因。”“玲玲,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呻吟了。“谁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也不说自己高明。当日,我闹着要去长征,也是一样,拼命洗刷自己,好向他们表白自己是革命的,厉大夫,小石也是这么怜悯我。可我洗刷得掉当日的屈辱么?洗刷不去的;直到今天,不洗,它却自然去掉了--这可以解释厉大夫今天并不乞求于平反而醉心于事业的原因。可那时的洗刷,却耗费了我多少时间和精神,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可悲!可你呢?爸爸,你挨整的关头,不也是这样么?并没超出我当日那号小学生的水平,你为了表白自己,在宣布你是‘内奸’‘叛徒’‘走资派’,作出开除党籍等处理的大会上,你不也挣扎着,不让人家堵你的嘴,叫什么‘革命路线’、什么‘万岁’!就象宋江被毒死,还怕坏了名节,伤了皇帝,要害死自己当日一道聚义的好汉一样。你的‘万岁’无非是叫人不要怀疑你的忠诚罢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以为,那样,正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
玲玲的话太放肆了,我有点儿气愤。莫非后一代会这样审判我们这老一辈的革命者么?这太可怕了!我心里说。玲玲从我怀里抱过那位小孩,说:“裁判我不做。你不是我的教父,我也不是你的法官。我不需要一个教父,你也不需要一个法官。”她沉吟了很久,眼里熠熠闪光,却又叹了一口长气--就像她当日神经失常时叹气一样,令我心惊肉跳,一会儿他又说:“爸爸,我不是来请你的。你也有眼睛,也有耳朵,可以看什么,不看什么,也可以听什么,不听什么……我们这一代,是在近廿年的挫折、创伤与浩劫中长大起来的,我们只看到这么些,我们自己周围的一切,并不曾有过天堂般的幸福、田园诗般的美妙,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结论来看世界的,也许过去有过美满与幸福,但我们没见到。不过,我知道,当你投身于革命,并不出自于对某一个人的好感,而是为的整个民族的命运,当时,民族危亡正迫在眉睫。
而你们憧憬的未来,也许是很简单的满足,也许是出自于朦胧的设想……但解放以后,尤其是五七年之后,你们在自己的已奋斗出来的天地里干了些什么?我不想多说了,你们挨整,我们一起受难,整个民族一起受难,可是,你可想到,当你说起什么忠诚、气节、原则、主义时,我们的结论却是,对于你们,最大的悲剧却在于:你们已经够‘左’的了,可把你们还当作右的整了下去……你们曾伤害过人民,可你们最终还是同人民一道负伤……”我默默无言,也许,站在另一代的位置上,是这么看的。
我说:“玲玲,你得让我想想。”“不是想想,而是实践出真知,得下去……”“去找厉大夫么?”“当然不一定是他,而是整个群众、人民,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爸爸,我倒想起一件事,在‘文革’最黑暗、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
至今并不曾解决。”“呵!”我的心被刺痛了。确实,那时候,当父亲的,是感到绝望了,对上头绝望,对国家的前途绝望,尽管当时在家里,没人来罗嗦什么,可我比在干校、在监狱里时还要绝望。可是,玲玲呢?除开对肆虐的‘四人帮’一伙表示愤慨后,却从血泊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民的觉醒,说这是一次预习,一次前哨战!“是呵,爸爸,我们的分歧一点不曾消除。当日,你为什么绝望,是因为你只看到上头,看到上面那套班子不行,你仅仅寄希望于上层。可我们,却是一直寄希望于人民的!今天,你尽管完全又恢复了希望,而且,平反冤狱的工作,不能说没有起色,但你不过完全是按上头的意志办事。但你并不了解,这上头的意志,当今,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于是,我们的分歧的根本点又出来了,你为什么不更多倾听人民的呼声?我了解厉大夫,也基本上了解你……他是完全献身于事业的,我记得他讲过,在狱中,一位老作家常给他讲‘凤凰涅’的故事,说凤凰是怎样投生于烈火而获得永生,却不知道你……”“我是应该同他面谈一下……”
“咯咯!”玲玲欢快地笑了,“这还差不多!”可笑声一消失,玲玲也不见了!“玲玲!玲玲!你在哪里?”没有回答。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说:她在你要去的苍海山区!她在那里等着你!弄到头,原来是幻梦一场,我还好好地躺在藤椅上--思念过切,郁积成梦了!我的反省成了后一代的诘问……我该怎么去作出回答呢?“作为当年的‘小芥兰头’,今天的厉咏时大夫,你可曾知道,当日对你说‘新社会只会把鬼变成人,也决不会把人制造成鬼’的人,他的确还活着,活到了今天,可是,他自己也成了鬼,也曾把人制造成了鬼……而他为了避免变成鬼,甚至连过去是知识分子的出身也一度加以否定,极力把自己从知识分子中划出去,装模作样,冒充什么工农干部。工农对于知识分子也许是一种进步的资格,但是,历史却绝不会这么写:愚昧对于文明是一大进步。
“这一切,又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难道岁月会耍魔术?”--在整个案子结束之后,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不知我自己是否能解答得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来年机构调整,我是该下去了。但是,在最后述职之际,不应当留下更多的遗憾。--于是,郑明丰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住宅,第二天,便叫了部小车,一直开到西南省有色金属公司的矿区去了。他要去见女儿玲玲,要去见小石。更要去见一同坐过两次牢的“小芥兰头”--厉咏时大夫。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攸之故也!--屈原《离骚》小车穿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口,重重迭迭的山崖在公路前似屏障一般不断地闪开--往事也有如这山崖,在郑明丰眼前不断地迭影出来。岁月过滤掉了所有的杂质,记忆这才变成明净的流水--但对于郑明丰来说,它迄今未澄清得了……
郑明丰终于见到了厉咏时,可这是怎样的一次见面呵!刚刚松了绑,两个手胀痛、发麻、痛彻心脾,就被人往里一推,正好撞在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角上,胸肋似被折断,几乎要昏过去了……昏昏沉沉中,仿佛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快给他一口水喝吧……”这多似廿年前,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难友们在他提审回来后,总端来一小盅子的水,特别是一位叫“小芥兰头”的小乞丐,总爱说:“快……快……”他缓缓地张开眼,仍是那么一个昏暗的牢房,人都辨认不清楚,一个个又白又黄,活似阎罗殿里熬尽了油、熬干了筋的小鬼,眼眶凹进去的,眼珠子凸出来的,颧骨耸起来的,下巴削尖了的,耳朵似风干的皮搭着的……奇形怪状,难以一一描绘。突然,他看到了一张枯干的脸。
眼一花,那张脸模糊了,似乎恢复到孩提时代的模样,额头很宽很大,凸出来,活象个芥兰头,眼眶子却凹了进去,眼珠子特别黑,特别灵活,他不由自主惊叫一声:“啊--是……”后面一句话,他没吐出来,把嘴唇紧紧咬住了,而且偏过了脸……而那张脸,也呈现出了惊愕的神情,简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惊异,还感到意外,眼珠子似乎钉住了,眼皮半天也没眨。郑明丰那久经风霜而变得发黑削瘦的脸,尤其是因长期折磨而不曾修过须发留下的一部大胡子,顿时让他明白了很多,很多……尤其是明白了,专案组为什么要让他证明一个死人是叛徒的问题……要给死人写变节材料,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事情,这也许只有在中国,在六十年代末端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这偏偏是真的!这人几乎要扑到郑明丰的身上,可是,倾刻间,他又马上变得麻木不仁,缓缓地转过了身子,忍受着最剧烈的痛苦,不再端详郑明丰的面容了……一切,仿佛又都在片刻中变得陌生,或者不曾经历过--为什么要经历过呢?不发生不更好么?
他,就是厉咏时,厉大夫!仅仅是由于积习,他厉咏时反对任何违背政策的作法,可他还在“执政”时,人们却以为这是头头们得讲政策而表现出来的高姿态。可他也反对派别间无休止的报复行为和武斗。他被一些人斥为右倾,也深得大多数人的心。
连耶枚亦认为他做得得体、有气量和风度。处处都有着对他的倾慕和体谅。惊涛骇浪的岁月里他过来了,公司革委会成立,他是文教部门的代表,居然当了委员,而且是少有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名委员。自然,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他的声誉又上了一个峰巅。过去的声誉仅是业务上的,现在却是社会上的。繁重的社会工作,使他几乎无暇于专业的深造,而那时风气也惟有政治红极一时。但他在百忙中坚持了自己的专业,没有荒废,并准备在安定下来后,再更上一层楼。他并没把常委的职务当作功禄晋升的一个台阶。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之所以“造反”也有专业上的感情所导致的。而耶枚呢?更陶醉于“委员夫人”的称呼上,愈发对他百依百顺了。但是,当他把专业上的情感和道义带到了社会上,带到了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之中时,他却注定要为这个职业病而倒霉和摔跤的。
此时,公司的一把手是上头派来的,二把手是个永久牌的左派干部,不说,读者也知道这是谁;三把手是个群众组织头头,就是那个孙头头,他们自然是配合默契,永远是一致而又一致的。革委会成立之后,无非是斗、批、改。干部的处理问题就摆上了议事日程。那时的风气,老的第一书记总归是不行了的,二书记也岌岌可危。谁也不会有异议,谁也不敢有异议。那时,厉咏时对老郑的看法是犹豫的,因为他运动中被贴的大字报最多,问题弄得很复杂。他自己对一些错误并不讳言。但是,在讨论他的专案的会议上,厉咏时还是本着对专业的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听取了专案组长的系统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