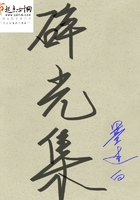哎,他这个小舅子,有时候还真是个活宝!
滕曼洗了把脸,又在眼部周围扑了点粉,只是眼睛的红肿总是一时半会儿消不掉的。
两人一下楼,就被围观,其实,说是围观也未免有些夸张,拢共就那几个人,除却他们俩,倒有三双眼睛往一块的招呼。
盯得他们极不自在。
滕曼不好意思的低着头,吸吸鼻子,瓮声瓮气的,“看什么呀,不是说吃饭么?”
“呀,小曼,你这额头怎么了,肿这么大一包!”安玉素顿时心疼的跟什剜了她一块肉似的,赶紧跑到滕曼跟前想要仔细看看,这一看可是把她给吓坏了。
“哎呦,怪不得一直低着头的,不肯抬起来,瞧瞧,眼睛都哭肿了,很疼吧?怎么弄得这是?”
滕曼不好意思的左躲右闪,温景之脸色随之一僵,正要开口,却被滕冀打断:“妈,我刚才和姐不是闹着玩儿吗,不小心给我撞得!”
话音刚落,他便很有自知之明的举起手臂,拦住安玉素晃过来的手,却还是被撸了一下后脑勺。
“妈,您怎么还打我头呐,我这都快要娶媳妇儿的人了,像什么样子嘛!”滕冀一脸的委屈,可怜兮兮的抚着后脑勺,暗地里却对着那夫妻俩挤眉弄眼。
腾远山也乐呵起来,“该!个不成器的小子!”
温景之很是感谢着小舅子的深明大义,见岳父这样埋汰他,自然是要护着一把的。
“爸,您别这么说,滕冀在他们那圈子的评价挺高,前两天我还挺行昀说,飞玦如今都缺他不可了呢!况且他还小,正是前途无限的年纪。”其实,这也是大实话,不过就是做个顺水人情。
腾远山心里自然也是高兴的,不过嘴上总是不依不饶,“他哪天要能跟你似的,就不用我和他妈这样操心了!”
“我哪儿要你和妈操心了,还以为我跟姐似的呐!”
滕曼气得直咬牙,偏又中间隔了一个温景之,不好对他直接下手。
安玉素一听他说到滕曼,立马就护了过来,“你姐才不要我们操心呢,她有你姐夫,你呢,赶紧的给我带个媳妇儿回来!”
“这还哪儿跟哪儿啊,我这不是引火烧身么我……”
滕冀的脾气好,耐受,抵抗力也是杠杠的,很是无所谓的耸耸肩。
有这样一个活宝的调剂,一顿饭到也吃的笑料百出,高潮迭起。
晚间,温景之照例陪着腾远山下棋,这老丈人也就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了,他可不得每次来了便献殷勤么!
滕冀他是没有那个耐心的,看了十分钟不到,被翁婿两人嫌了不下5次。
第一,他当真不是什么君子,做不到观棋不语。
第二,这只货根本就不会下棋,还喜欢两边乱指挥,简直是在捣乱!
安玉素在厨房剥石榴,滕曼则烹了上好的大红袍给两人端了过去。
她很自然的在温景之的身边坐下,安静的看着自己丈夫一步一步陷入父亲的包围圈。
这下她不淡定了,在男人举棋不定的时候,抢过他手中的棋子,替他走了一步,结果么,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腾远山不悦的大摇其头,“你说你们姐弟两个,棋品,懂不懂?”这棋赢得,真叫一个扫兴!
“我也不是什么君子呀,要棋品干什么,再说,爸,您都已经赢了,这有点儿得瑟了啊!”要嫌弃她,怎么着也该是温景之啊。
“怎么跟爸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温景之笑着揉她的发顶,顺手将她带进自个儿的怀里,将她抱在胸前。
滕曼自然是忸捏一番,这男人,也不分个人前人后的,丢人!实则,心里头也是欢喜的。
“再来一盘儿吧,爸,这回曼曼她保管不再多嘴,也不多手,是吧,老婆。”
滕曼很是无趣的撇撇嘴,正巧望见安玉素端着一瓷盘红澄澄的石榴过来。
“我吃石榴,才不愿意给你支招呢!”还敢嫌弃她,他自己的棋艺怕也比她好不到哪儿去,就这两下子,还是前阵子死乞白赖跟她求来的呢。
当初还被她笑话来着,老婆都娶到手了,还要回过头去讨好岳父大人,这是什么逻辑?笨!
可人温景之只是笑笑,并没有因为她的耻笑而懈怠,终于经过滕曼一段时间的调教之后,学了点皮毛,每次来滕家,总算也能对付个一两招。
不过腾远山滕大师说了:“景之呀挺有天分的,要是能长期经受他的熏陶和培养,指不定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呢!”
滕曼当时就笑抽了,“哎呦,可拉倒吧!人现在是正军级,那什么大师,他稀罕么?”
温景之当时是怎么回答来着?
那怎么能一样?论棋艺,我这才是刚入门阶段,能得到爸的肯定,是莫大的荣幸……以至于滕冀后来都表示,姐夫那天的表现,用名词来形容,那就是‘狗腿’;用动词来形容,那就是‘拍马’,冠冕堂皇了说是‘尊敬长辈’,不要脸的说是给你根杆儿,还真敢往上爬!其实,后来,温景之给总结了下,顺便道出了实情:其实,这个,在战术上称之为全面性渗透,占据你方心腹地带……
总之,就是一句话,将腾远山同志彻底拿下!从此奠定下不可动摇的翁婿加棋友加师徒的复杂革命情谊……
等他们下完棋,时间已经不早,滕曼都快要在温景之的怀中睡过去,这样,小夫妻两个自然是被安玉素留下。
许是最近都没有睡过一回的好觉,滕曼今晚特累,温景之将她抱回了房,草草的洗了个澡,便倒在床上挺尸。